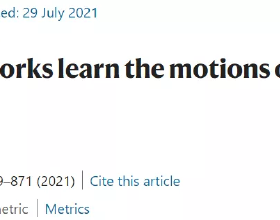父親見到我,急急忙忙的,先跟我說道:“村裡的春亭死了!才六十三,死了!”我心裡陡然一驚,腦海裡立時浮現出春亭的樣子來。
記憶中的春亭,中等偏上的個頭兒,短圓臉兒,厚嘴唇,方下巴,粗粗實實的,看著很壯氣,總是渾身冒勁的樣子。他好說笑,愛打鬧,有時說話挺衝,是個不帶拐彎兒的直性子人。第一次對他有深刻的印象,還是在我十三四歲的時候。
那年秋天,我和母親在村西十八畝地往外拉棒子秸。割倒不幾天的半乾不溼的,死沉死沉,加上又要來來回回過水渠,抱過幾捆子後,就累得吃不住勁了,只好幹一會兒歇一會兒。等到要裝車時,我們孃兒倆更犯難了,車子裝得支架巴虎的不說,更難的是煞車的繩子總也勒不緊。就這樣拉著走的話,車上的棒子秸很容易“唰”下來(坍塌的意思),弄不好還會側翻。我和母親圍著車子,唉聲嘆氣地乾著急。
正在這時,春亭拉著一車棒子秸正好路過,見狀停了下來,幫我們把上邊裝得歪了的理了理,然後開始煞車子。他把摟著棒子秸的繩子解開,重新捋了捋,把繩頭兒從車把下掏過去,遞給我,讓我用兩手拽緊,然後往下一鞘身子,雙膀猛地用勁,一提一放,再一提一放,繩子被拽得緊繃繃的。他的手頭很有勁兒,我能感覺到。春亭的手很快,來回那麼一弄,我還沒怎麼看清,他已經綁好了,動作看上去很簡單,也不費勁,卻十分妥帖、受用……
後來,我繼續上學,知道春亭娶了媳婦兒,過了一年生了個小閨女兒,也知道他當著瓦匠,成天忙得不行。我參加工作後,星期天、節假日斷不了回村子裡來,有時在街上能碰見他。每回碰見,他總是老遠就笑嘻 嘻地跟我打招呼:“峰峰迴來啦? 今幾個還走不?”說完就匆匆忙忙走開了。他為人豪爽、熱情,遇事愛講義氣,村子裡誰家過紅白事兒,只要跟他一招呼,他就放下自己的活計,趕過來幫忙兒,幹什麼都跑在人前頭。有時忙完他自己手上的活兒,就又去幫別人,見女人們人手兒緊張,用過的盤子、碗碟兒堆著洗涮不過來,他就趕過去,擼起袖子幫著一塊兒洗涮,別人笑他“裝娘們兒”,他也跟著開玩笑,一點兒也不惱。
總之是不閒待著,手不識閒兒。他也肯賣力氣,特別是遇上人家過白事兒的時候,總是去幫著打墓。打墓是有規矩和講究兒的,這個活兒一般人幹不了,又有的人心裡硌硬,不願意幹。沒聽見春亭抱怨過什麼,什麼時候說去打墓,說走就走,樂樂呵呵地扛上鐵鍁,再帶上盒兒煙……
再後來,我聽到他的訊息就漸漸少了,直到這次聽父親說他剛剛去世。
我問父親,春亭出殯那天去上名兒沒有。父親說:“上了 ,我給出了個白幛子。你娘那個(去世)時候,他家出的就是白幛子。這是傳換,咱算是還他家的。”白幛子就是一塊白布,短的是六尺,長的是一丈二。我沒問父親出的是多少,他有一個小本本兒,是我母親當年出殯時鄉親們上的名兒,一筆筆、誰誰家,是隨的錢,還是拿的幛子,都記得清清楚楚。鄉里鄉親的,遇見紅白喜事,即便平常的日子裡來往不多,也大都要照個面兒,或去幫兩三天忙,或去上個名兒,“隨" 一個“份子”,除非兩家人不對眼才不會走動。上名兒般講究對等,禮尚往來,誰不比誰高,誰也不壓過誰。歲月流轉,村裡人之間有來有往,彼此惦記著、維繫著,誰也不欠誰,也就沒有別的話說。這是鄉間的一種“禮數”吧。
自母親去世以後,我回村子裡的次數越來越少了。想來,我不見春亭,差不多已有七八年的時光。自然,以後也再不會見得著了。他曾給村子裡那麼多去世的人打過墓,不知道這回是村子裡的誰給他打的墓。
■文/改編自《走,到村子裡去》(樊秀峰 著 花山文藝出版社出版)
■圖片除圖書封面外均為配圖
■編輯/徐姍姍
■版權所有,未經許可不得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