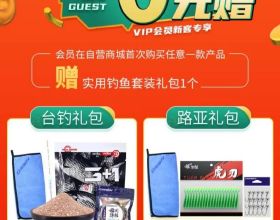白孝文是白嘉軒的長子。從孩童起到族長走過一段好孩子、好學生、好“莊稼”、好丈夫,好族長的歷程。
該到上學的年齡,白嘉軒給馬駒起了學名叫白孝文。白孝文先在本村的學堂跟徐先生初學,然後到白鹿書院去投朱先生門下深造。
辛亥革命後,孝文孝武受到上新式學堂的表妹的影響,也提出要進城唸書,白嘉軒說:“人家進城裡讓人家去。書院只要不關門,你們就跟你姑父好好唸書。”孝文孝武再不敢強求。
朱先生的白鹿書院因為學生都去城裡新興的學校唸書而關閉了。孝文和孝武回到了白鹿村。白嘉軒一陣歡喜之後便對兩個兒子說:“明日早起把舊衣裳換上,跟著你三伯到地裡務莊稼去。”
孝文是好樣的,穿著舊衣服每天三晌跟鹿三到地裡去學務莊稼,一身土一臉汗從不見叫苦叫累。
孝文結婚後因為貪戀床笫而受到父親白嘉軒的詰責時也是恭敬地回答:“我哪兒舉止失措,禮儀不規,爸你隨時指教。”
白嘉軒經過長期觀察和無數次對比認定,由孝文將來統領家事和繼任族長是合法而且是合適的。兩個孩子都是神態端莊,對一切人都彬彬有禮,不苟言笑,絕無放蕩不羈的舉止言語,明顯地有別於一般鄉村青年自由隨便的樣子。但孝文比孝武更機敏,外表上更持重,處事更顯練達。
白孝文的“發達”起自白氏祠堂的修復。在白嘉軒看來,當初砸碑鬧事的是鹿兆鵬黑娃等人,是他之下的一輩人了,他這邊也應該讓孝文出面而不值得自己親自跑前顛後。今天召集族人的鑼就是孝文在村子裡敲響的。於是白孝文第一次在全族老少面前露臉主持最隆重的的祭奠儀式,由此走上了族長的位置。
“白孝文已經被確立為白鹿兩姓族長的繼任人,他主持修復祠堂領誦鄉約族規懲罰田小娥私通的幾件大事樹立起威望,父親白嘉軒只是站在後臺為他撐腰仗膽。孝文出得門來從街巷裡端直走過去,那些在蔭涼下裸著胸膛給娃娃餵奶的女人,慌忙拉扯下衣襟捂住了奶子躲回屋去;那些在碾道里圍觀公狗母狗交配的小夥子,遠遠瞧見孝文走過來就立即散開……他比老族長文墨深奧看事看人更加尖銳,在族人中的威信威望如同剛剛出山的太陽。他的形象截然區別於鹿兆鵬,更不可與黑娃同日而語。
他的人生轉折起自白嘉軒對鹿子霖的羞辱和對田小娥的酷刑。鹿子霖和田小娥的私情被前去和田小娥“撩騷”的狗蛋發現,隨後遭到鹿子霖指使的團丁暴打。致使狗蛋與田小娥的醜事被張揚得村巷盡知。
雖然白嘉軒察覺出鹿子霖與田小娥有染,但並沒有讓鹿子霖出列示眾,而是依然讓他站在族人當中做一名“監刑”並受教育的看客。
鹿子霖心中有鬼,自然覺得這是對他的羞辱,所以他去看望受刑後重傷的田小娥才藉著田小娥對白嘉軒的怨恨說出:“你得想法子把他那個大公子的褲子抹下來。那樣嘛,就等於你尿到族長臉上”的主意。
“白孝文不摸牌九不擲骰子,連十分普及的‘糾方’‘狼吃娃’‘媳婦跳井’下棋等類鄉村遊戲也不染指,唯一的娛樂形式就是看戲。”結果,這看戲成了他淪陷的“井口”!
田小娥藉助“忙罷會”看麻子紅表演“春戲”的機會實施了鹿子霖策劃的報復:田小娥抓住了白孝文身體上的“反應”並用眼神“準確無誤明明白白地告示他:‘你要是敢吭聲我也就大喊大叫說你在女人身上耍騷!’”白孝文完全清楚那樣的後果不言而喻,聚集在臺下的男人們當即會把他錘成肉坨子,一個在臺下趁黑耍騷的瞎熊不會得到任何同情。
白孝文“惶恐無主,心在胸膛裡突突狂跳兩腿顫抖腦子裡一片昏黑”,結果被田小娥挾持到廢窯中,田小娥極盡威脅哄騙誘惑地將白孝文拉下水:田小娥“成功”地將自己交到白孝文的手中,而白孝文也發現了田小娥身上的“新鮮”。相比之下,白孝文覺得自己那個婆娘簡直就是一堆粗糙無味的豆腐渣了。
經鹿子霖的操作,白孝文和田小娥搞在一起的訊息終於透過冷先生傳到白嘉軒的耳中。白嘉軒去“捉姦”,聽到了兒子和田小娥在窯洞炕上的“呢喃”。白孝文在父親“氣昏死在窯洞門外雪地上的那一晚,”回到家中後羞悔難當,跑到馬號,站到鹿三的面前抬起低垂到胸膛的下巴說:“三叔,我要走呀!你日後給他說一句話就說我說了‘我不是人’……我做下丟臉事沒法子活人了!”
最終,孝文被“執行族規”當眾抽打,隨後又“按照家規”被分家。
在饑饉到來的日月中,孝文“硬著頭皮向父親提出借糧,白嘉軒拒絕了。”孝文又“硬著頭皮走進上房東屋……他哀告奶奶給父親說一句:借些糧。”白嘉軒聽到後從對面的西屋對著母親的東屋大聲說“你就甭開這個口。”白孝文再沒有說話就從奶奶的屋裡退出來回到前頭門房。
孝文向父親提出借糧傷臉以後就把兩畝水地賣掉了。白嘉軒得知這個訊息後氣得吃不下飯,他把孝文叫到院子裡,阻止孝文把水地賣給鹿子霖並許以雙倍價錢回購,被孝文報復性拒絕。結果“黑暗裡一聲嘯響,白孝文應聲一個趔趄跌倒在地,父親手中的柺杖抽擊到他的臉上,繼之又砸到他的大腿上。
白孝文卻感到一種報復性的舒暢,從地上晃晃悠悠爬起來走進屋去,咣噹一聲插上門閂,把父親和孝武冷晾在院子裡。”孝文又回到屋裡躺在自家炕上“一條腿架在另一條腿上,對著女人說:‘好咧好咧!從今往後再沒有誰來管我了。’”
白嘉軒這兩棍子不僅把白孝文打離了這個家,還把孝文打入了斷崖式的墮落。
白孝文在傷好後第一次走出街門就端直走進田小娥的窯洞,在這裡他第一次“得心應手”地在田小娥身上完成了自己想做的事。田小娥很是驚奇和好奇地問:“過去到底咋麼著是那個怪樣子?今日個咋麼著一下就行了好了?”,白孝文卻嘲笑說:“過去要臉就是那個怪樣子。而今不要臉了就是這個樣子,不要臉了就像個男人的樣子了!”
看著白孝文與田小娥的鬼混,孝文的媳婦也曾鼓起勇氣抗爭:“地賣下的銀元不論多少,不見你買一升一斗,你把錢弄了啥了?”白孝文眼睛一翻:“你倒兇了?你倒管起我來了?”媳婦說:“我兇啥哩我管你啥來?我眼看餓死了,還不能問你買不買糧?”白孝文冷著臉說:“不買。你要死就快點死。你不知道死的路途我指給你:要跳井往馬號院子去,要跳河跳崖出了村子往北走,要吊死繩子你知道在哪兒掛著……你不死我也睜眼不盯你。”
隨後有一夜,孝文媳婦找到田小娥的窯門口外頭,跳著罵著。孝文拉開窯門,一個耳光抽得媳婦跌翻在門檻上……還揪著媳婦的頭髮髻兒,兩個嘴巴抽得她再不吼叫撕罵了,迅即像拖死豬 似的拖回家去。孝文媳婦最終沒能逃出餓斃的命運,臉上留著一坨坨烏青紫黑的傷痕,那是孝文拳頭砸擊的結果。
白孝文在田小娥的引誘下抽上大煙。
飢餓比世界上任何災難都難以忍受,鴉片煙癮發作似乎比飢餓還要難熬,孝文跌入雙重渴望雙重痛快的深淵。八畝半水旱地和門房,全都經過小娥靈巧的手指捻搓成一個個煙泡兒塞進煙槍的小孔,化作青煙吸進喉嚨裡。
當孝文手中最後的一塊“銅板”化作青煙消散後,白孝文走上了乞討的路。
白孝文在神禾村遭到了頭一家財東李龜年鄙視;在賀家坊被賀耀祖拉到家裡當做“敗家子的師傅”警示全家;最後跌落在自家村子外面的大土壕裡差點被野狗當做死屍,又差點兒被鹿三當做臥道的餓殍。
在鹿三半是同情半是揶揄的提醒下,孝文打起了精神柱起來打狗棍子走進白鹿倉的舍飯場去搶舍飯時又受到鹿子霖的“展示性”的羞辱:鹿子霖把白孝文拉進白鹿倉的一間屋子裡“一抬頭就看見姑父朱先生坐在一張桌子旁邊啞然閉口垂下頭來。”
“屋子裡的人全都噓嘆起來。這裡坐的是臨時組成的白鹿倉賑濟會的成員,包括鹿子霖在內的九個保障所的鄉約,各管一項分工負責向原上饑民施捨飯食,總鄉約田福賢自任會長,他們構成了白鹿原上流社會。
大家瞅著鹿子霖拉進門來的白孝文,衣褲骯髒邋遢,頭髮裡鏽結著土屑灰末和草渣兒,臉頰和脖頸沾滿汙垢,眼角積結著的乾涸的眼屎上又湧出黃蠟蠟的新鮮眼屎,令人看著作嘔,挽卷著褲腳的小腿上,五花血膿散發著惡臭。從德高望重的白家門樓逃逸出來的這個不肖之徒,使在座的白鹿原上層人物觸目驚心感慨不已,爭相發出真切痛心惋惜憐憫的話。孝文不僅得不到絲毫溫暖和慰藉,反而更加窘迫,透徹地領受到墮落者的羞恥。”
鹿子霖為了擺脫自己買白孝文的地,拆白孝文的房的尷尬,他靈機一動地提醒田福賢舉薦白孝文去縣保安大隊去擔任那個“有文墨”的角色。田福賢爽快地答應並當時寫下舉薦信。白孝文接過田福賢寫的舉薦信,感激得流出淚來:“田叔子霖叔……”撲嗒一聲跪下了。孝文被田福賢抻起來。
到滋水縣保安大隊僅僅一個月,孝文身體復原了信心也恢復了,接受過十數天的軍事操練之後,他就被抽調到大隊部去做文秘書手,可望將來有輝煌的發展前途。
白孝文謀劃,第一次領餉之後,就去酬答指給他一條活路的恩人田福賢和鹿子霖,再把剩餘的錢留給小娥。當聽到鹿子霖說:“那個貨死了”的時候,白孝文直著眼問:“誰死了你說誰死了?”當白孝文確認是田小娥死了後失控地站起來:“你說她……餓死了?”鹿子霖按著他的肩膀讓他坐下來才說:“不像是餓死的,像是被人害死的,炕上有血……”(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