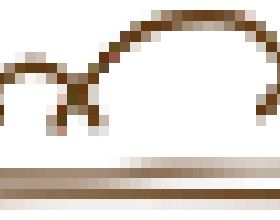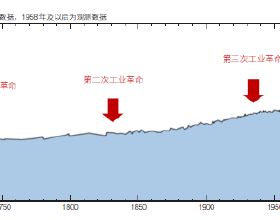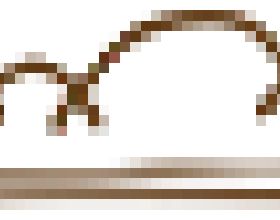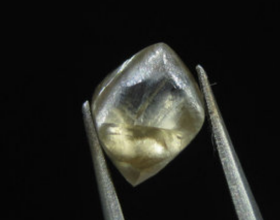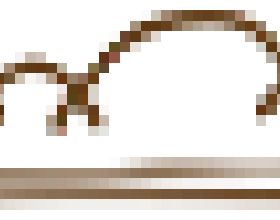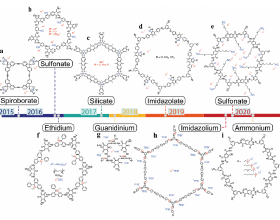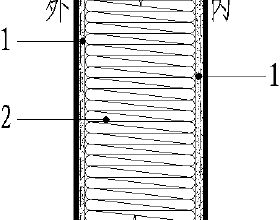周汝昌1940年秋考入燕京大學西語系,1941年秋走進顧隨宋詞選讀的課堂。年底,太平洋戰爭爆發,燕京大學旋被日寇封閉,師生被迫解散。也就是從那時起,顧隨與周汝昌開始了長近二十年的書信交往。周汝昌寄給顧隨的信函,早於上世紀六十年代損毀淨盡,而顧隨寫給周汝昌的部分手札卻幸運地儲存下來,現已收入中華書局新版的《顧隨致周汝昌書信集》。
通觀所見的這些通訊,起初更多是師生之間溝通訊息、傾吐心聲、唱和推敲,但從五十年代初開始,兩人的交流“忽然進入了一個奇蹟般的發展階段”,周汝昌說:“此階段中,先生因書札往還生出的許多討論主題,引發了先生的興致,其多年的積學深思之未宣者,卻以此際的興會與靈感所至,給我的信札竟然多次‘變成’了整篇的論學研文說藝的長篇論文……”(《懷念先師顧隨先生》,見《顧隨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文集》,河北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正是從這些有限的書札、文稿中,我們有幸得睹兩位大師圍繞《紅樓夢》的一段殊勝文緣。
一、《曹雪芹生卒年之新推定——懋齋詩鈔中之曹雪芹》的發表
1947年秋,周汝昌透過考試,重入燕京大學西語系繼續學業。課餘必到圖書館看書,興趣所及,常與其兄周祜昌通訊研討,不知不覺,話題轉到《紅樓夢》上。在《我和胡適之》(《歲華晴影——周汝昌隨筆》,東方出版中心1997年版)一文中,周汝昌回憶:“一次,祜昌把考察《紅》書的幾種重要書目開列給我,囑我留意,其中之一名曰《懋齋詩鈔》。這本書,是曹雪芹的好友敦敏的詩集子,胡適之已經訪得了敦誠的《四松堂集》,只是尋不到《懋》集,久抱遺撼。因祜昌提醒了我,於是就到圖書館去找尋——其實也不過是姑作一試之意罷了。誰料此書就在館中,卻多年無人過問,我則一索而得,當然十分高興。在這集子裡,很快發現了六首與雪芹直接有關的詩,重要無比!”

周汝昌(左)與同學上世紀40年代合影於燕京大學校門(今北大西門)
周汝昌隨即就此六首詩寫了篇文章,但也只與周祜昌作了交流,便擱置一旁了。
恰在此時,顧隨來了一封信,一語“煽燃”了這點險些熄滅的“星火”。信中說:“不悉足下之課忙至如何程度,能復抽暇為小文向各報投稿不?如能亦復大佳,既可以資練習,又可以與人多結文字緣。”(1947年10月23日)
周汝昌於是把手邊的兩篇文章交給顧隨,其中一篇便是研究《懋齋詩鈔》與曹雪芹的那一篇。顧隨把兩篇文章推薦給了趙萬里,趙時主編天津《民國日報》的“圖書”副刊版。12月2日,顧隨告訴周汝昌:“大作兩篇,其第二篇已交與趙萬里先生。今早晤及趙公,具說已寄出,將在《天津民國日報·圖書週刊》日內披露,希注意。”
12月5日,《曹雪芹生卒年之新推定——懋齋詩鈔中之曹雪芹》發表——這是周汝昌公開發表的第一篇作品。次年3月15日,顧隨致書謂:“大作‘論曹雪芹’一文登出之後,胡適之極推許,曾有一短札致兄,亦載《民國日報》圖書版。”
周汝昌自述:“此文內容,今日已成‘常識’,但在當時,卻是紅學停滯了二十五年以後的一個突然的新發現。胡適之見了此文,確很高興,就寫信給我。此信是由趙先生轉交的,而趙在轉交前又編髮在《圖書》上。”(《我和胡適之》)周汝昌與胡適的交往便始於此時,而其對紅學的深入研究也正是從這裡起步,並迅速迎來個人學術成就的巔峰。
二、《紅樓夢新證》出版的前前後後
周汝昌從胡適處借得甲戌本《脂硯齋重評石頭記》,閱罷,他“簡直驚呆了”,當即“萌發了一種極其強烈的志願:此生要盡一切努力將曹雪芹的這部奇書的本來面貌讓讀者都能看到,而再不能坐視篡亂嚴重毒酷的程高本永遠欺蔽世人”。胡適繼而又把“戚序大字本”借給周汝昌。不久,已迷蹤多年的“庚辰本”也被周汝昌搜得。“當時僅有的三真本匯齊”,周汝昌開始著手“實現恢復芹書真面的大願”(《我和胡適之》)。
1949年12月,《燕京學報》第三十七期發表了周汝昌的《真本石頭記之脂硯齋評》。文末寫道:“讀者於覽此拙文後,若能進而更事鑽研,匡其不逮,訂其未當,則舉世間《石頭記》的讀者,庶幾皆得賴以樹立正確的觀念,徹底瞭解作者的原意,不致將一部空前傑作汙衊得不人不鬼,此誠文藝之大幸,亦且拙著《證石頭記》一書之願心矣。”
這篇文章以及文末的這一段話,又引來了時在文化部工作,併兼上海棠棣出版社編輯的文懷沙的注意,主動幫助周汝昌安排《證石頭記》的出版事宜。1953年9月,被譽為“近代紅學研究的奠基之作”的《紅樓夢新證》由上海棠棣出版社出版發行。
顧隨初見此書時,心理上還經歷了一斷有趣的波折:1953年10月27日信中寫道:“我知道這部書是用了語體寫的,而我對於玉言之語體文還缺乏信心,萬一讀了幾頁後,因為詞句、風格之故,大動其肝火,可怎麼好?不意晚夕洗腳上床,枕上隨手取過來一看,啊,糟糕,放不下手了,實在好,實在好!再說一句不怕見怪的話,簡直好得出乎我意料之外!”“玉言風格之駿逸,文筆之犀利,其在此書,較之平時筆札,直是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對於把《紅樓夢》的批書人脂硯看做一位女性,並且認定她就是書中人物史湘雲這一重要考證成果,曾經有不少人表示譏嘲和反對,第一位完全給予肯定的,就是顧隨:“脂齋是枕霞公,鐵案如山,更無致疑之餘地。”他甚至斷言:“而今而後,《新證》將與脂評同為治紅學者所不能廢、不可廢之書。”(上信)
自此以後,直至1953年底,《新證》一直是顧隨寫信談論的主要話題。
1953年10月28日信中舉出《新證》的三點值得商榷之處:“《史料編年》過於求備,頗有‘貪多’之嫌,將來必有人焉出而指摘。……此其一。行文用語體,而興之所至,情不自禁,輒復夾以文言,述堂不在乎,亦恐有人以為口實。此其二。行文有時口風逼人,鋒芒過露,此處不復能一一舉例,切望玉言自加檢點。此其三。”
11月14日信中談到《新證》的修改問題時,顧隨又說:“如精力、時間、環境、條件俱能許可,必須大刀闊斧,收拾一下。殿最去留當以雪老為主,其他有關於曹家者不妨痛刪。”
1976年版《紅樓夢新證》,是在第一版基礎上的增訂,字數增加了一倍。對於顧隨提出的壓縮《史料編年》和有關曹家內容的建議,周汝昌有自己的看法,並在重排後記中作了說明。對於前者,周汝昌說:“這本書裡較為可存的,恐怕也就只這一章。因此,我從一九五七年即曾動手單就這部分進行過增訂修改,……這些年來陸續積累的資料,又有一定數量,蒐集非易,如不整理,散亡可惜。”對於後者,周汝昌說:“歷史是很難割斷來理解的。階級的行為也不是個人的而是集團的。透過曹家這個家族(以及其親戚朋友)的歷史,可以看到不少在一般歷史書裡看不到的時代面影,歷史情狀。這些對理解《紅樓夢》的社會背景,都不為無助。”
三、《說紅答玉言問》的撰寫
早在1952年病癒之後,顧隨便在信中與周汝昌展開了關於《紅樓夢》的長時間的討論。
在《顧隨致周汝昌書信集》中,最早談及《紅樓夢》的信是1953年4月11日的“第十八書”,其後接著還有5月底到6月初的“第廿書”,信中兩人研討的主要內容是榮寧二府和大觀園的真實所在。
稍早,1952年歲末,顧隨因“玉言來書問山翁”,“何以素於《紅樓》不著一字”,已有《說紅答玉言問》之作,分析《紅樓》中人物性格,不過只是個開端,尚不足六千字。究其原由,乃因顧隨1953年6月即到天津工作,“到津後,初是奠居未定,後是業務相逼,當然不能續寫。閣置既久,乃並初命筆時之腹稿亦拋到爪哇國裡去了”(1953年10月29日信)。從已有內容和寫作計劃來看,與《新證》專事考據不同,顧隨的《說紅》重點是從藝術創作的角度討論小說中人物形象的塑造,用他自己的話說:“《說紅》亦只是分析《紅樓》中人物性格,尚未能專力批評雪老之文字也。”
《紅樓夢新證》的出版和成功,激發了顧隨完成《說紅》的熱情,1953年10月29日信中對周汝昌說:“已有玉言之《新證》,便不可不有述堂之《說紅》,既並駕而齊驅,亦相得而益彰。”又說:“《說紅》暗中摸索,頗有與《新證》互相符合處。雖不必即詡為‘大略相同’,私心亦時時竊喜也。”連完成的時間,顧隨都已經計劃好了:“此間明春便開小說講座,寫出,正是一舉兩得耳。”
然而,這份宏偉的計劃終於沒有如期完成。到了1954年的10月,一場聲勢浩大的批判俞平伯《紅樓夢研究》的運動開始,顧隨的《說紅》也便永遠地擱置下去了。
關於《說紅答玉言問》這份未完稿,還有一段坎坷的經歷:1966年“文革”開始,顧隨已經去世六年,但家中還是受到衝擊,先後被抄了兩次家,著作、手稿、書信、藏書等等被查抄殆盡。1967年的一天,河北大學中文系學生劉玉凱在存放抄家物資的小禮堂無意中翻到顧隨的幾種手稿,悄悄帶回自己的宿舍,除了閱讀,還時常拿出來臨摹。1978年秋,已留校任教的劉玉凱到顧隨六女顧之京家,把自己儲存的顧隨手稿全部送還,倖免遭劫的其中就有這份《說紅答玉言問》。顧之京拿到這份手稿,立即給周汝昌寫信,報告情況,幾天之後又親到北京把手稿送交給他。周汝昌當時激動得半晌無言,淚眼婆娑。(劉玉凱《說說我收藏顧隨先生手稿的情況》,見《顧隨研究》,南開大學出版社2011 年版;周汝昌《羨季師的“紅學”——〈說紅答玉言問〉始末小記》,見《顧隨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文集》)。
根據珍貴手稿整理,
生動展現古典學問的魅力,
還原一代學術大師心路歷程。
《顧隨致周汝昌書信集》
趙林濤、顧之京 校注
簡體橫排
32開 精裝
978-7-101-15516-7
78.00元
顧隨致周汝昌書信集
¥50.7
購買
內容簡介
這是現代學者、書法家顧隨(1897—1960)在1942至1960年間寫給弟子周汝昌(1918—2012)的書信集,共126通(另附致他人信兩通)。
顧隨,字羨季,筆名苦水,別號駝庵,河北清河人,曾執教於燕京大學、輔仁大學、天津師範學院等高校,精研詩詞、書法、佛學。他曾在信中對友人說:“有周玉言者,燕大外文系畢業,於中文亦極有根柢,詩詞散文俱好,是我最得意學生。”(1952年8月28日致盧季韶書)著名紅學家周汝昌(1918—2012)則不無自豪地稱:“我是與先生‘通訊受業’歷史最久的一個特例。”(《懷念先師顧隨先生——在顧隨先生逝世30週年紀念會上的報告》
顧隨與弟子周汝昌的通訊始自1942年初燕京大學封校之後,一直持續至1960年顧隨去世之前,書信中儲存了大量學術討論、詩詞唱和的內容,在古典文學研究、現代學術史研究以及現代學人日常生活研究等方面都有著重要的價值。這些書信起初更多是師弟子間生活、內心的傾吐、詩詞的唱和與探討,但從五十年代初開始,兩人的交流“忽然進入了一個奇蹟般的發展階段”,周汝昌說:“此階段中,先生因書札往還生出的許多討論主題,引發了先生的興致,其多年的積學覃思之未宣者,卻以此際的興會與靈感所至,給我的信札竟然多次‘變成’了整篇的論學研文說藝的長篇論文……”每當談及老師和他這段特殊的文字緣,周汝昌都會對這批彌足珍貴的學術和文化財富大加歎賞。
書信原件長期保存於周汝昌家,直到2002年開始,才陸續整理披露於世。2010年,顧之京、趙林濤整理校注的《顧隨致周汝昌書》出版,後收入《顧隨全集》(2014年初版,2017年修訂版)。其後,周家又發現顧隨致周汝昌手札近三十通,兩萬餘字。《顧隨致周汝昌書信集》除了增補上述新發現的未刊書信之外,對舊版文字釋讀與編年上的訛誤進行了校訂,並進一步對書信中的一些內容作了註釋。
作者簡介
顧之京,顧隨先生第六女,河北大學文學院教授。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潛心於父親遺著的蒐集與整理工作,先後出版《顧隨文集》《駝庵詩話》《顧隨詩詞講記》《顧隨全集》等數十種,著有《女兒眼中的父親——大師顧隨》《苦水詞人——顧隨詞集詞作解析》《我的父親顧隨》等。
趙林濤,文學博士,河北大學教授。長期從事顧隨研究,主持國家社科基金專案1項、河北省社科基金專案3項,整理出版《顧隨全集》《駝庵學記》等10餘部,著有《顧隨與現代學人》《顧隨和他的弟子》,發表論文《“顧學”研究範疇》《新見顧隨自注本〈濡露詞〉研究》等20餘篇。
(統籌:陸藜;編輯:白昕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