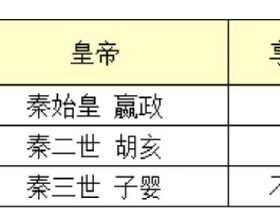父親的扁擔
■張 雄
在我入伍後的這幾十年,父親把我穿軍裝的照片一排排整齊地粘在老家客廳裡。生前,他逢人便說,他兒子有出息。但我覺得,這“出息”的源頭,幾乎是父親用扁擔“挑”出來的。
父親有一根扁擔,已經磨得鋥光瓦亮,靜靜地立在老宅的牆角。它是父親的老夥計,跟了父親很多年。
我們小時候,父親常常挑著這根扁擔去趕集,賣菌子、苞谷,換了錢買油鹽醬醋,偶爾也會買一小塊肉,帶回來給我們改善伙食。
一次,父親趕集帶回來兩隻豬仔,並對我們兄妹幾個說,你們要念書、要吃肉,就全靠這兩隻豬仔了,要照顧好它們。自此,我們兄妹幾個每次出去玩之前,一定會把豬草先打好,把豬仔餵飽。那時,因為家裡孩子多,我經常吃不飽飯,晚上總能夢見吃肉。醒來一看,枕頭上流了好多口水。父親笑著說:將來好好唸書,才能經常吃上白米飯和肉。吃肉和唸書有什麼關係?還沒上學的我,對父親的話似懂非懂,但牢牢記在了心裡。
我們幾個孩子相繼上學,家裡負擔越來越重。每次開學前,父親坐在火塘前一抽菸就是半宿。後來,父親心一橫,去了私人煤窯挖煤掙錢。
那時,他每天要揹著幾百斤重的煤,在坑道里爬許多個來回。有一次,他差點遭遇事故。我們知道後,死活不讓父親再去,以退學相要挾,父親這才結束挖煤。
我13歲那年,去離家很遠的鎮上寄宿讀書。出發前那晚,父親在火塘前一坐又是半宿。我睡意矇矓中聽見父親對母親小聲地說:“娃娃有出息了,咱們再苦再累也得咬牙挺著,不能耽誤娃的前程……”
送我去學校報到那天,父親還是挑著那根扁擔,一頭裝著我的被褥,另一頭裝著苞谷、臘肉、菌子醃的辣醬,像是把半個家底都給我帶上了。一路上,時不時有拖拉機路過。我看父親滿頭是汗,想攔一輛拖拉機帶我們一段。可這一伸手就是3塊錢,父親搖了搖頭,手一拍扁擔,說:“我有老夥計呢,累了咱就慢慢走,坐那個做啥!”到了學校,父親把東西放下,說了句“我回了,你好好的”,便頭也不回地走了。
高考結束,我考上了省外一所重點大學。母親去集上扯花布給我做了新被褥,採菌子給我做了一大罐辣醬。父親挑起他的扁擔,裝上行李,再次送我出門。
一路上,父親沒怎麼說話。到了站臺上,我跟父親揮了揮手。父親站在不遠處,腳邊立著他那根扁擔,喊了聲:“你好好的!”那一刻,我的眼淚掉了下來。火車緩緩開動,站臺上的父親,許久未動。他和他的扁擔,變得越來越小。
畢業前夕,在得知海軍某部來我們學校招人時,父親鼓勵我參軍,希望我能多為國家做貢獻。遵循父親的意願,我選擇到部隊工作,並最終如願。
父親去世後,他的扁擔孤獨地立在老宅的牆角。送父親遺像回老宅的那些天,我每天都把扁擔擦得鋥亮,摸摸它,彷彿還能感受到父親的體溫。抬頭看看父親的遺像,他的雙眼慈祥地看著我。我知道他有許多話想對我說。我也深知,唯有走好軍旅路,才是對父親最好的告慰。
(本文刊於《解放軍報》2021年12月26日05版,內容略有刪改)
解放軍報微信釋出
播音:郝澄波
編輯:霍雨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