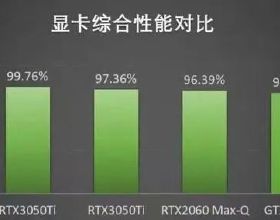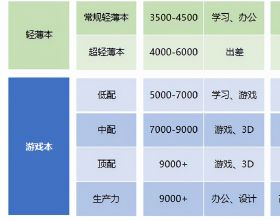當前,數字技術的強勢滲透正引發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等領域的深刻變革,逐漸成為多元主體關係重塑和社會治理結構最佳化的新型驅動力,這也為鄉村振興中的“治理有效”提供了技術性的方法論。為助力鄉村振興、推動鄉村治理數字化,國家相繼出臺了《數字鄉村發展戰略綱要》《關於開展國家數字鄉村試點工作的通知》等重要檔案,加速推動了鄉村數字化治理程序,基層治理體系的現代化水平在技術賦能下得以顯著提升。
鄉村數字治理的客觀複雜性
一是鄉村治理主體具備差異性。改革開放40多年來,拘囿於經濟社會發展和鄉村社會結構變遷,農村社會成員呈現多元分化,農民從均質性較強的群體分化成鄉賢、中堅農民、留守群體等具備明顯異質性的群體,在身份、角色多元化的同時,農民的能力和需求亦呈現出差別化和分層化。資訊科技作為高新科技的產物,具備較強的排他性,在為部分農村社會成員增權賦能的同時,也容易將一些群體排除在技術“高牆”之外。這不僅沒能實現良好的技術賦能,反而對資訊弱勢群體形成了相對剝奪。在村民的資訊可及能力存在一定差異的情況下,無差別地推進單一、同質的數字治理模式,無疑會誘發技術賦能的不均衡和鄉村數字治理的低效能。
此外,村幹部作為鄉村治理主體的重要構成,在數字治理實踐中承擔了更為複雜的資料錄入、公告發布、任務攤派等工作。與選調的大學生村官相比,相當一部分村莊老幹部在複雜的數字系統面前有捉襟見肘的尷尬,而各地政府雖然強調透過能力培訓實現人機匹配,但也鮮有在供給側針對此類村幹部的培訓。一個現實情況就是,村幹部往往學不會、學不精,也不願意學,這使得村幹部一定程度上成為鄉村數字治理的中間性梗阻。因此,各級政府在推進鄉村數字治理過程中,應重視治理主體的差異性,大力推進供給側改革,著力回應資訊弱勢群體的利益訴求,進行差異化供給。
二是鄉村的異質性資源稟賦。我國幅員遼闊、地理與文化環境複雜多樣,各村莊之間由於獨特的歷史文化和地理環境呈現出顯著的異質性。自然資源、社會資源以及區位條件等要素的差異使得不同村莊具備迥異的行為邏輯和發展樣態。同時,隨著工業化與城鎮化程序快速推進,區域間的村莊分化和農戶分層日益凸顯。不同村莊的治理事務、政策需求和發展路徑呈現複雜多元的態勢,相同的政策輸入可能輸出相異的政策效果,鄉村的異質性客觀上決定了鄉村數字治理路徑的多樣性和複雜性。目前來看,地方政府在推進鄉村數字治理過程中,傾向於將全域內各類村莊視為同質性的整體,強調數字治理的“一體化”和“整體性”。各級各部門為推進條線上的工作,自上而下地推行同質化的“App”“公眾號”,從而引發供需錯配和資源損耗,並有可能陷入“網際網路+形式主義”的誤區。
三是鄉村公共事務的複雜性。隨著鄉土社會公共事務的動態複雜性加劇,政府主導公共產品供給的科層邏輯難以適應公共管理情境變化的問題愈發凸顯。目前來看,儘管整體性治理、協同治理是各地政府推進鄉村數字治理過程中一以貫之的理念,但其落腳點更多在於破除政府執行體系的條塊分割、資訊孤島和“九龍治水”等結構性困境,強調政府內部的橫向整合和協商互動,對社會組織和企業等外部主體在某種程度上缺乏足夠的關注。在先行實踐中,數字化公共產品仍然是高度集中的科層制供給,政府往往是村民獲取數字公共服務的唯一“選項”,既難以滿足複雜公共事務的治理需求,也降低了公共服務供給質量和村民的獲得感。這就要求各地政府在推進鄉村數字治理實踐過程中,加快吸納社會和市場力量嵌入,著力構建多元共治的鄉村數字治理格局。
鄉村數字治理的供給側轉變
治理主體的差異性、鄉村資源稟賦的異質性以及鄉村公共事務的複雜性,客觀上要求鄉村數字治理要在供給側出好“多選題”。實現數字治理技術“親村莊”與“親社會”的友好型轉變,以善政與善治為鄉村治理目標,需要堅持如下數字治理的路徑。
首先是堅持使用者本位與差異化供給相結合。資訊科技具備一定的准入門檻,當前鄉村數字治理實踐中的同質化供給對數字化時代的弱勢群體形成了“技術擠出”現象,村民資訊可及能力的差異決定了鄉村數字治理要堅持以使用者為中心,針對需求側的能力差異,在供給側對弱勢群體進行兜底性照顧和差異化供給。以人民網的“無障礙服務”為例,為滿足不同受眾的瀏覽需求,人民網為老人、盲人和弱勢群體提供“老人版”“盲人版”“大字幕影音”以及“無障礙搜尋”等多樣版本,以實現各類群體的無障礙閱讀。鑑於此,各地政府應推動數字治理理念從技術本位向用戶本位轉變,將服務重心下沉至基層,著力挖掘和回應數字治理情境下不同群體的個性化需求,以提供多元化的數字治理模式,不斷提升電子政務和數字服務的可及性。推動鄉村數字治理的核心是憑藉技術的增權賦能提升村民的幸福感、獲得感,絕不能以對弱勢群體的剝奪和擠出為代價。
其次是堅持因地制宜與精準化供給相結合。發揮數字治理在鄉村振興中的支撐和引領作用,要始終立足於國情與鄉情,各級政府應充分摸清轄區村莊在人口結構、產業形態和服務需求等層面的顯著性差異,如傳統農業型村莊傾向於透過數字平臺獲得育苗育秧、機耕機收、糧食收購等服務,城郊村則更希望獲取房產租售、區域規劃和就業創業等資訊。鑑於此,政府應立足鄉村實際,分類推進鄉村數字治理實踐,形成更具針對性和可操作性的數字治理模式。政府要改變傳統的自上而下的推動方式,在提供基礎架構的基礎上,透過行政賦權推動“點單”職能下放,允許各村在政府的宏觀政策框架內結合自身特色和重點發展領域對數字服務進行集合性規劃,建立個性化的服務門戶和入口,為區域內使用者提供更為精準、優質的數字化服務,不斷提升鄉村治理效能。
最後是堅持協同共治與多主體供給相結合。鄉村數字治理應擺脫傳統科層制的權威架構,構建多元主體共治格局。政府應秉承協同共治理念,以更為包容的姿態制度化地吸納集體經濟組織、社會團隊和企業等多元主體參與。政府不僅是數字治理平臺的建構者,還應扮演好促進多主體協同的助推者、多主體共同生產的合作者。一方面,政府應更為開放地創設多元互動的協商治理平臺,既注重打破政府內部的“資訊孤島”和“數字鴻溝”,實現政府機構的協同高效,也向政府之外的企業和組織提供適配的介面和通道。另一方面,推動政務平臺與其他數字平臺的互嵌,實現資源和功能的雙重整合。網際網路平臺有大量的使用者資料和優勢資源,政府可以透過平臺整合建立政府與網際網路平臺企業的資料共享機制,並藉助其他平臺的服務功能回應群眾的多元化訴求,以更好地形成“黨政主導、群眾參與、社會協同”的鄉村數字治理格局。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一般專案“社會質量視角下鄉村治理與鄉村振興研究”(18BGL171)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南京農業大學公共管理學院)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張新文 杜永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