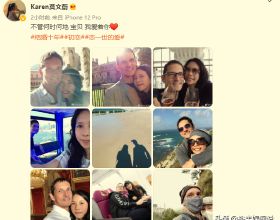縱觀歷史,以科學的名義進行了許多邪惡的實驗。我們都知道瘋狂科學家的刻板印象,通常是流行文化中的惡棍。然而在現實生活中,雖然科學經常拯救生命,但有時科學家會為了取得成果而犯下可怕的罪行。
有些是道德錯誤,是人們確信自己在做正確的事而做出的錯誤判斷。其他時候,他們是純粹的邪惡。以下是人類歷史上最糟糕的九個實驗。
分離三胞胎
在 1960 年代和 1970 年代,由 Peter Neubauer 領導的臨床心理學家進行了一項秘密實驗,他們將雙胞胎和三胞胎彼此分開,並將它們作為單胞胎收養。據說該實驗部分由美國國家心理健康研究所資助,當三個相同的三胞胎兄弟在 1980 年意外找到對方時,他們才被曝光。他們不知道他們有兄弟姐妹。
三胞胎之一的大衛凱爾曼對這個實驗感到憤怒:“我們一起被剝奪了 20 年的時間,”凱爾曼在奧蘭多哨兵報的文章中說。據《洛杉磯時報》報道,他的兄弟愛德華·加蘭德於 1995 年在新澤西州楓木的家中自殺身亡。
據新聞報道,負責這項研究的兒童精神科醫生——彼得·紐鮑爾和維奧拉·伯納德——沒有表現出任何悔意,甚至說他們認為自己在為孩子們做些好事,將他們分開,這樣他們就可以發展自己的個性,根據奎萊特的說法,伯納德說至於紐鮑爾從他的秘密“邪惡”實驗中學到了什麼,這是任何人的猜測,因為這項有爭議的研究結果被儲存在耶魯大學的檔案中,直到 2066 年才能解封,NPR 在 2007 年報道紐鮑爾在 1996 年出版的《自然的指紋:人格的新遺傳學》一書中發表了他的一些發現,主要是關於他的兒子。根據今日心理學,截至 2021 年,Viola Bernard 博士的一些論文已在哥倫比亞大學公開。
導演蒂姆·沃德爾在電影《三個相同的陌生人》中記錄了三胞胎的生活”,在 2018 年聖丹斯電影節上首次亮相。
納粹醫學實驗
也許有史以來最臭名昭著的邪惡實驗是大屠殺期間奧斯威辛集中營的黨衛軍醫生約瑟夫·門格勒(Josef Mengele)進行的那些實驗。門格勒在即將到來的火車上尋找雙胞胎進行實驗,希望能證明他關於雅利安人種族至上的理論。許多人在此過程中死亡。據美國大屠殺紀念博物館稱,他還收集了他死去的“病人”的眼睛。
納粹使用囚犯來測試傳染病和化學戰的治療方法。根據猶太虛擬圖書館的說法,其他人被迫進入冷凍溫度和低壓室進行航空實驗 無數囚犯接受了實驗性絕育手術。根據大屠殺博物館收集的口述歷史,一名婦女露絲·埃利亞斯(Ruth Elias)用繩子綁住了她的乳房,這樣黨衛軍的醫生就可以看到她的孩子餓了多長時間,她最終給孩子注射了致命劑量的嗎啡,以防止其遭受更長時間的痛苦。
一些應對這些暴行負責的醫生後來被作為戰犯審判,但門格勒逃到了南美。據《衛報》報道,他於 1979 年死於巴西,死於心臟病發作,他的最後幾年孤獨而沮喪。
日本731部隊
在整個 1930 年代和 1940 年代,日本皇軍主要在中國對平民進行生物戰和醫學檢測。根據1995 年《紐約時報》的報道,歷史學家謝爾登 H 哈里斯估計,在 731 單元的首席醫師石井四郎將軍的帶領下,這些殘酷實驗的死亡人數未知,但可能有多達 20 萬人死亡。
研究了許多疾病,以確定它們在戰爭中的潛在用途。根據蒙大拿大學羅伯特 KD 彼得森博士的一篇論文,其中包括鼠疫、炭疽、痢疾、傷寒、副傷寒和霍亂。 發生了許多暴行,包括用霍亂和傷寒感染水井,以及在中國城市傳播瘟疫肆虐的跳蚤。
根據彼得森的說法,這些跳蚤被扔在粘土炸彈中,這些炸彈被扔在 200-300 米的高度,沒有留下任何痕跡。囚犯在寒冷的天氣中行進,然後進行試驗以確定凍傷的最佳治療方法。
該單位的前成員告訴媒體,囚犯被注射毒氣,被置於壓力室直到他們的眼睛彈出,甚至在活著和有意識的情況下被解剖。據《泰晤士報》報道,戰後,美國政府幫助對這些實驗保密,作為使日本成為冷戰盟友的計劃的一部分。
據《衛報》報道,直到 1990 年代後期,日本才首次承認該部隊的存在,直到 2018 年,該部隊數千名成員的姓名才被披露。
“怪物研究”
1939 年,愛荷華大學的言語病理學家開始證明他們的理論,即口吃是孩子對說話的焦慮引起的一種習得行為。不幸的是,他們選擇這樣做的方式是試圖透過告訴孤兒他們註定在未來開始口吃來誘導他們口吃。
研究人員在俄亥俄州士兵和水手孤兒之家與孩子們坐下來,告訴他們他們有口吃的跡象,不應該說話,除非他們能確定自己說得對。這個實驗並沒有引起口吃,但它確實讓以前正常的孩子感到焦慮、孤僻和沉默。
根據 2003 年《紐約時報》的一篇文章,未來的愛荷華病理學學生將這項研究稱為“怪物研究”在研究上。三個倖存的孩子和另外三個人的遺產最終起訴了愛荷華州和大學。2007 年,愛荷華州以總計 925,000 美元的價格和解。
伯克和黑爾謀殺案
直到 1830 年代,解剖學家唯一合法可用的解剖屍體是被處決的兇手。被處決的兇手相對罕見,許多解剖學家開始從盜墓者那裡購買屍體 - 或者自己進行搶劫。“身體搶奪作為一種‘專業’職業直到 18 世紀末才真正開始形成”,《搶奪者:挖掘英國復活者不為人知的故事》一書的作者蘇西·倫諾克斯(Suzie Lennox)講述歷史的一切在一次採訪中,“在此之前,學生和解剖學家會在墓地進行自己的突襲,儘可能地獲取屍體”。
愛丁堡寄宿公寓的老闆威廉·黑爾和他的朋友威廉·伯克找到了一種方法,可以將新鮮的屍體送到愛丁堡的解剖臺上,而不會真正偷走一具屍體。根據瑪麗·羅奇 (Mary Roach) 的“僵硬:人類屍體的好奇生活”,從 1827 年到 1828 年,這兩個人在寄宿公寓裡扼殺了十幾名房客,並將他們的屍體賣給瞭解剖學家羅伯特·諾克斯。羅奇寫道,諾克斯顯然沒有注意到(或不在乎)他的最新供應商帶給他的屍體可疑地新鮮。
伯克後來因其罪行被絞死,此案促使英國政府放鬆對解剖的限制。愛丁堡解剖博物館館長麥克洛姆·麥卡勒姆(Maclolm McCallum)在接受採訪時告訴 All About History:“這起醜聞導致了 1832 年的《解剖法》,這使得更多的屍體可以合法地供學校使用。” “如果你死在收容所或醫院,並且沒有親屬或手段來支付你的葬禮費用,你的屍體將被送到學校進行解剖。至關重要的是,提供屍體的機構只將它們提供給相關的解剖學校與教學醫院”。
奴隸的外科實驗
“婦科之父”詹姆斯·馬裡恩·西姆斯(James Marion Sims)對奴隸的實驗繼續引起爭議(圖片來源:Getty/Hulton 檔案館)
據《大西洋月刊》報道,現代婦科之父 J. Marion Sims 透過對奴隸婦女進行實驗性手術(有時每人進行幾次手術)而聲名鵲起 直到今天,西姆斯仍然是一個有爭議的人物,因為他在女性身上治療的疾病,膀胱陰道瘻,造成了可怕的痛苦。患有瘻管(陰道和膀胱之間的撕裂)的婦女失禁並且經常被社會拒絕。
西姆斯在沒有麻醉的情況下進行了手術,部分原因是最近才發現麻醉,部分原因是西姆斯認為手術“不足以證明麻煩是正當的”,正如他在NPR的演講中所說的那樣。
如果西姆斯的病人完全可以自由選擇,他們是否會同意接受手術,爭論仍然很激烈。儘管如此,阿拉巴馬大學社會工作教授 Durrenda Ojanuga在 1993 年的醫學倫理學雜誌上寫道,西姆斯“操縱奴隸制的社會制度來進行人體實驗,這在任何標準上都是不可接受的。” 據《衛報》報道,2018 年,為了應對持續的爭議,一座模擬人生的雕像被拆除。
瓜地馬拉梅毒研究
許多人錯誤地認為,政府故意讓塔斯基吉參與者感染梅毒,事實並非如此。但根據韋爾斯利學院的說法,Susan Reverby 教授的工作最近揭露了美國公共衛生服務研究人員所做的事情。Reverby 發現,在 1946 年至 1948 年間,美國和瓜地馬拉政府共同發起了一項研究,該研究涉及故意使 1,500 名瓜地馬拉男性、女性和兒童感染梅毒。
該研究旨在測試化學物質以防止疾病傳播。根據邁克爾· A·羅德里格斯的說法在 2013 年的一篇論文中;“這些實驗不是在無菌的臨床環境中進行的,其中導致性病的細菌以針刺疫苗或口服藥丸的形式進行管理。研究人員系統地反覆侵犯極度脆弱的個體,其中一些人處於最悲傷和最絕望的境地Reverby 發現,那些得梅毒的人接受了青黴素治療,但她發現的記錄表明參與者沒有跟進或知情同意。據《衛報》報道,2010 年 10 月 1 日,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 (Hilary Clinton) 和衛生與公眾服務部部長凱瑟琳·塞貝柳斯 (Kathleen Sebelius) 發表聯合宣告,為這些實驗道歉。
塔斯基吉研究
美國最著名的醫學倫理失誤持續了40年。1932 年,根據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的資料,美國公共衛生服務部發起了一項關於未經治療的梅毒對黑人男性健康影響的研究。
研究人員追蹤了阿拉巴馬州 399 名黑人男性的疾病進展,還研究了 201 名健康男性,告訴他們他們正在接受“壞血”治療。事實上,這些人從未得到足夠的治療,即使在 1947 年青黴素成為治療梅毒的首選藥物時也是如此。根據官方塔斯基吉的說法,直到 1972 年的一篇報紙文章將這項研究暴露在公眾面前,官方才將其關閉。
斯坦福監獄實驗
菲利普·津巴多 (Phillip Zimbardo) 備受爭議的斯坦福監獄實驗繼續引起人們的興趣(圖片來源:蓋蒂/赫斯特報紙)
1971年,現任斯坦福大學心理學名譽教授的菲利普津巴多,著手測試“人性的本質”,以回答諸如“當你把好人置於邪惡境地時會發生什麼?”之類的問題。他如何回答他的人性問題曾經而且被許多人認為是不道德的。他設立了監獄,並付錢讓大學生扮演看守和囚犯,他們似乎不可避免地變成了虐待的看守和歇斯底里的囚犯。為期兩週的實驗在僅僅六天後就被關閉了,因為事情很快就變得混亂了。據泰晤士高等教育報道,津巴多說:“僅僅幾天,我們的警衛就變得虐待狂,我們的囚犯變得沮喪並表現出極度壓力的跡象。”根據斯坦福監獄實驗,獄警幾乎從一開始就對囚犯進行了惡劣的對待,剝光他們的衣服,用除蝨劑噴灑他們的身體,並通常騷擾和恐嚇他們,以此羞辱他們。
事實證明,根據Medium 上的一份報告新聞出版物,2018 年 6 月,看守自己並沒有變得咄咄逼人——津巴多鼓勵了虐待行為——一些囚犯假裝情緒崩潰。例如,志願者囚犯道格拉斯·科爾皮 (Douglas Korpi) 說,他假裝崩潰是為了提前獲釋,這樣他就可以準備考試了。
即便如此,根據美國心理學會的說法,斯坦福監獄實驗一直是心理學家甚至歷史學家理解即使是健康的人在某些情況下也會變得如此邪惡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