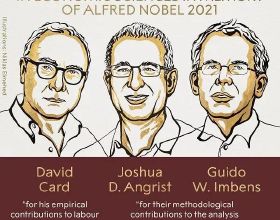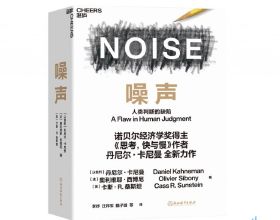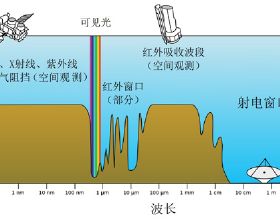盛夏熾熱的陽光裡,空氣中仍然瀰漫著揮之不去的死屍惡臭,秦淮河畔的六朝煙雨,雕樑畫棟的千年帝都,在炮火硝煙中化作了一片狼藉。
同治三年(1864)六月廿五日,距離吉字營攻破太平天國的都城天京,剛剛過去十日,坐鎮安慶大本營的湘軍主帥曾國藩乘船抵達江寧下關碼頭。
站在天京城的廢墟之上,審視著這座滿目瘡痍、哀鴻遍野的巨大城市,五十四歲的湘軍主帥卻無法抑制內心的陣陣喜悅,墨絰從戎至今,塵滿面鬢如霜,血染征衣十餘載,如今終是功成名就。
很快,克復天京的報功奏摺就擺在了紫禁城的御案之上,只是其中的某些內容,卻讓兩宮皇太后在興奮之餘又難免有些失望,甚至對奏摺所指的真實性都產生了懷疑。
歷年以來,中外紛傳洪逆之富,金銀如海,百貨充盈……然克復老巢,而全無貨財,實出微臣意計之外,亦為從來罕聞之事。
是的,根據曾國藩的奏報,太平天國定都十一年的煌煌天京城,洪秀全傾盡所有營造的“人間小天堂”,卻是座一無所有的空城。
那麼,1864年被攻破前夕的天京城,是否如傳聞所言,蘊藏了鉅額的財富,而在這場最終的決戰之後,曾氏兄弟又到底獲得了多少好處?
帶著這些疑問,讓我們一起走進今天的文章。
非議因何而起
天京城破,與清朝分庭抗禮十餘年的太平天國運動宣告失敗,湘軍這一堪比清初平定“三藩之亂”的不世奇功,為曾國藩和曾國荃等人帶來了巨大的聲望和榮耀。
但因為“髮匪老巢”的鉅額“賊髒”去向不明、交代不清,也讓曾氏兄弟在戰爭結束之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裡,都深陷在巨大的輿論漩渦之中。
尤其是吉字營主帥曾國荃,身為前敵總指揮,直接指揮和參與了天京戰役的全過程,戰後一度傳言其“獲資數千萬”。
流言雖無真憑實據,但也絕非捕風捉影,之所以會產生這樣的非議,主要是基於以下三點原因:
首先是不合邏輯
按照歷史記載和實戰經驗,一座城池尤其是一個國家的都城被攻破時,多少都會留存一定數量的金銀財物。
1127年靖康之變時,東京汴梁告破,金國人劫掠的北宋府庫和禁宮珍寶不算,光是兩次兵臨城下,強迫徽、欽二宗交納的戰爭賠償款就高達黃金一百三十七萬八千兩,白銀一千二百四十萬兩,帛一千一百零四萬匹。
1644年李自成攻破明朝首都,闖王在北京城內也強制性“募捐”了超過七千七百萬兩白銀的軍費。
太平天國雖然不能和宋、明兩朝相比,但作為一個統轄當時中國最富庶區域、存續時間又長達十一年的割據政權,若真如曾國藩所言,其都城之內全無資財,實在令人難以想象。
其次,曾國荃對天京採取的是長圍久困的鐵桶戰術,幾乎在城破前一年,也就是1863年秋天時,天京就已經完全斷絕了與外界的交通聯絡,基本上不存在大批次向外轉移財物的可能。
戰役的全過程只有湘軍參與,戰後整個天京城又幾乎遭到了毀滅性的破壞,包括天王府、忠王府等可能存在鉅額財富的地點,均被付之一炬。
這種事前秘不示人、事後死無對證的做法,如何能使人主滿意、如何能令朝臣不生疑,又更如何能堵得住天下悠悠之口?
最後,曾國荃做不到如胞兄曾國藩那般近乎刻薄式的清廉自守。
所謂財不外露,但曾國荃不僅在戰後一擲千金,遣專人到北京求購箋紙,弄得京城沸然,更在湖南老家大興土木,一副陡然而富還深怕旁人無從知曉的做派
甚至其侄女曾紀芬都親口承認,九叔“每克一名城、奏一凱捷,必請假回家一次,頗以求田問舍自晦”。
而這樣的行事作風,也讓人們對他貪墨之事的指控,有了合理的想象空間。
太平天國神秘的“聖庫”
當然,對曾國荃貪贓枉法的猜測,首先要建立在天京城確實存在數額驚人的財富這一基本前提之上。
正如前文所述,天京被圍日久,其中所藏金銀多少,外界很難得知,關於金陵城中“金銀如海、百貨充盈”的傳聞,多半也只是根據過往經驗而得出的一種推斷。
但有一點毋庸置疑,即太平天國從1850年金田團營開始,便採取了財產歸公、生活必需品平均分配的“聖庫”制度。
太平天國官方也對聖庫的管理,有過明確的規定。咸豐元年,洪秀全曾專門下詔:凡一切殺妖取城,所得金寶、綢帛、寶物等項,不得私藏,盡繳歸天朝聖庫,逆者議罪。
如果嚴格按照這一制度執行,那麼太平天國在十幾年的戰爭中所得,以及治下億萬臣民繳納充公的財物,確實是一筆難以估算的財富。
但“聖庫”制度實際上僅僅存在了六年,在1856年天京事變爆發後,便遭到了嚴重破壞,業已名存實亡。
內亂結束之後,洪秀全大權獨攬,隨著石達開出走,其洪氏嫡系又全面把持了朝政。
權力不受監管,必然滋生腐敗,洪秀全並沒有將聖庫的錢財“取之於民用之於民”,而是隨意地支取用於大肆建造亭臺樓閣,和滿足自己的揮霍。
“聖庫”的性質已經由“公帑”變為“私藏”,天王洪秀全帶頭破壞了這一制度,太平軍中大小將領紛紛上行下效。
先是把戰爭中獲得的金銀財寶等硬通貨悉數截留,而將穀米牛羊等尋常之物繳納入聖庫。
太平天國連年征戰,聖庫既要應付戰爭的龐大消耗,又要維持天京的日常開支,真金白銀的收入在減少,而開支卻不斷增加,長期的入不敷出,必然導致國庫的逐漸乾涸。
李自成當年打進北京時,即使得國276年,家大業大的明朝,為應對農民起義和北方的女真入侵,其國庫存銀最後也不過只有37萬兩而已,以此類推,太平天國的聖庫又怎麼可能充盈?
天京被圍最困難的時候,忠王李秀成曾苦口婆心地勸告“合朝文武”,“切勿存留銀兩”,“概行要買米糧”。
也說明在當時的太平軍將領中,私藏銀錢已經是比較普遍的現象,而聖庫空虛,甚至連基本的糧食儲備也無法得到保障。
1863年9月,天京被圍日久,境況日趨艱難,同時李秀成的大本營蘇州又正遭受淮軍的圍攻,忠王懇請離京赴援,但洪秀全卻以“國庫無存銀米”為由,要其“助餉銀十萬”,方能放行。
試想如果不是“聖庫”已捉襟見肘、無以為繼,洪秀全即便是再利令智昏,也斷然不會因為區區十萬兩白銀,而允許天京保衛戰的總指揮,在帝國生死存亡的最緊要關頭離開的。
所以,聖庫曾經“金銀如海”不假,但城破之時,“全無貨財”看來也是實情。
曾國藩並未道盡實情
當然,曾國藩在奏摺之中也並沒有完全說實話,聖庫枯竭不假,這只是反映出了太平天國這個政權,在國家層面的財務狀況。
而實際上整個天京城中,大小王府林立,軍民更有十萬之眾,這其中暗含了多少財富,湘軍又從中發了多少橫財,曾大人比誰都清楚,卻在奏摺中對此刻意的保持了沉默。
據曾國荃幕僚趙烈文事後在其《能靜居日記》中記載,“城破之日,全軍掠奪,無一人顧全大局”。
在天京城內“金銀如海,百貨充盈”的心理暗示之下,貪慾讓湘軍集體陷入了瘋狂,“見人即殺,見屋即燒,子女玉帛,掃數悉入於湘軍”。
地面之上被劫掠一空,眾人又開始挖地三尺,刨墳掘墓、破棺毀屍,為了儘可能地搜刮乾淨,可以說是無所不用其極。
天京城漸漸淪為焦土廢墟,而臨江的水西門卻熱鬧非常,大量搶奪而來的木材、器具,日夜不停地由城頭吊下,然後經由停泊在岸邊的船隻,溯江而上,源源不斷地運回湖南。
以上見聞,均出自《能靜居日記》,作為曾國荃的高階幕僚,趙烈文親歷了天京陷落的全過程,其真實性不用懷疑。
湘軍入城,並不是一種正常的政權更迭和城防交接,而是對南京這座千年古都從上至下,由內而外的洗劫。
所以無論太平天國的國庫是否空虛,湘軍上下,肯定都透過對天京的劫掠大發了一筆橫財。
當然,湘軍上下這種瘋狂的舉動,曾國藩兄弟不僅知道,而且是默許的,湘軍這種地方武裝,得不到中央的財政支援,軍費給養幾乎全靠自籌,因此,城破之後,大索三日,已經是其內部不成文的規定。
行文至此,有兩個問題大致可以得出答案,第一,天京城破之前,太平天國的中央財政系統已經崩潰,至少聖庫之中沒有傳言和想象中的鉅額財產。
第二,來自各王府宮殿中的奇珍異寶,以及百姓家中的民間財富,數量驚人,同時盡數為湘軍所得。
那麼,最後關鍵的問題來了,作為湘軍主帥的曾國藩和前敵總指揮的曾國荃,到底有沒有在天京戰役中獲得數量驚人的財富?
曾氏兄弟的不在場證明
曾國藩的嫌疑很好解除,因為從天京戰役打響,此人就一直坐鎮安慶大本營遙控指揮,直到天京城破的第十天,才抵達南京,此時金陵城已被洗劫殆盡,所以湘軍主帥有充分的“不在場證明”。
況且曾文正公時時以聖人的標準為言行準則,克己守禮,清廉奉公,在戰亂之中藉機貪贓枉法不太可能。
而曾國荃作為圍困天京的主力,吉字營的主帥,確實全程都在第一線指揮作戰,看似很難逃脫干係。
但城池何時告破,對於攻守雙方而言,顯然都是不確定的,恰好在城破當日,也就是1864年7月19日,曾國荃卻是在天京近郊的雨花臺湘軍大營。
關於曾國荃的形跡,《能靜居日記》中曾有專門說明,城破之時,趙烈文目睹湘軍燒殺搶掠,憤而奔赴雨花臺大營,請求吉字營主帥曾國荃出面主持大局,
但一來“大索三日”本就是湘軍破城之後的潛規則,二來曾國荃在這場決戰中,可謂殫精竭慮,陡然聞聽天京告破,精神和肉體鬆懈之後,疲憊因此根本就沒有理會趙烈文,倒頭便酣然入睡了。
而且曾國荃在給朝廷的第一封報功奏摺中,大致交代了攻破天京的相關情況,也正是因為“大勢粗定,遽回老營”而遭到了清廷的斥責。
直到三日之後,吉字營主帥才姍姍入城,此時,針對天京洗劫的高潮已過,連天王府都已經被曾國荃麾下悍將肖孚泗在劫掠之後放火付之一炬了。
所以,曾國荃在天京城破的第一時間,肯定沒有直接參與洗劫,至於其有沒有指使下屬參與,沒有明確的史料記載,無法妄加揣測。
但《能靜居日記》中曾反覆強調,“沅帥(曾國荃字沅甫)已實無所沾,但前後左右無一人對得住沅帥耳”,“沅帥坐左右之人累之耳!其實,子女玉帛,無所與也。”
身為湘軍一員,趙烈文能夠如實地記載湘軍入城後大肆搜刮搶掠、殺人放火的罪惡行徑,這個秉筆直書者的史德還是值得信任的。
但如果曾國荃是清白的,那其“獲資數千萬”的謠言因何而起,其戰後大興土木的資金又究竟從何而來呢?
用資料為曾國荃闢謠
認定曾國荃私吞太平天國鉅額財物的清末史料筆記,最具代表性的當屬李伯元的《南亭筆記》。
此書對曾國荃的貪墨行為,言之鑿鑿,有如目睹,其中就詳細描繪了湘軍主帥在天王府正殿之中獲得元代大頂燈四個、大如指頂的極品東珠一掛以及一個來自於圓明園的舊藏、堪稱稀世珍寶的“翡翠西瓜”,並進而推斷出“忠襄(曾國荃諡號)於此中獲資數千萬”。
此文一出,後世跟風者眾,加之曾國荃行事高調又毫不掩飾,因此其“老饕”之名不脛而走。
事實上《南亭筆記》只能算是野史演義一類的讀本,其史料的真實性也被後世學者詬病甚多。甚至其開篇第一句,“金陵既破,曾國荃入天王府”,就與事實真相有較大出入。
而關於曾國荃“獲資數千萬”是個怎樣的概念,這裡用幾組資料做一個簡單的對比:
嘉慶十九年,戶部庫存銀為1240萬兩;道光三十年,庫存800餘萬兩;咸豐元年,國庫尚有700多萬兩銀子,但因為要應付以太平天國為首的農民起義,到咸豐三年,大清的家底便只有區區169萬兩了。
實在很難想象,曾國荃透過一場戰爭的掠奪,可以收穫超過國庫十倍、甚至幾十倍的財富,這顯然是不合常理的。
那麼曾國荃在老家置辦田產、購買宅邸的資金究竟從何而來呢?
先看看曾國荃實際擁有的資產情況,其長孫媳杏文曾透露“忠襄身後,僅有田六千畝,長沙屋二所,湘鄉屋一所。
這些財產摺合成現銀,大概有上百萬兩,比照一般升斗小民,當然堪稱鉅富,但離富可敵國還相去甚遠。尤其是曾國荃還做了十幾年省部級的封疆大吏,攢下這點身家並非難事。
而田不過百頃,宅不過三處,也實在很難和傳言中貪墨太平天國數千萬資財產生的“老饕”產生聯絡。
曾國荃確實在湖南老家修建了氣勢恢宏、威風八面的“大夫第”,但實際上此宅並非始建於打下天京之後,也不是一次性投資,最初動工於1859年,此後陸續添磚加瓦,擴大改建,前後歷經八年才告竣工。
戰後曾氏兄弟功成名就、加官進爵,而曾國荃又是揮金如土、性格張揚之人,衣錦還鄉就更是理所當然的要大興土木來光耀門楣,但如此舉動也難免引起了他人的猜測和非議。
實際上曾國荃從軍多年,後來又位列封疆,有人做過統計,其出任湘軍統領六年,餉銀12萬餘兩,後又歷任巡撫、總督,俸祿更高達兩百餘萬,即使不算灰色收入,他的官俸足也以支撐他購置田產,建造房舍的費用。
至此,我們應該可以認定,打下天京,曾國荃並未曾參與過戰後的劫掠,也沒有從戰爭中獲得外界傳言的鉅額財產。
但至於其麾下將領是否在盆滿缽滿之餘對這個主帥有所報效、回饋,我想應該是有的,但這些意外之財,無論如何都不可能達到數千萬這個量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