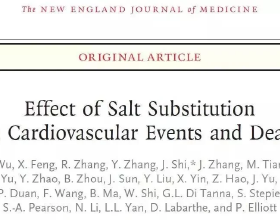北大教室中,一個戴著黑框眼鏡、身著長衫的中年男子正在為底下的學生們講課,他旁徵博引、引經據典,講至激動處乾脆連手中的講稿也扔下,手舞又足蹈,將一堂枯燥的歷史課講得生動有趣。
他就是我國著名的“國學大師”——錢穆,被文學界尊稱為“一代宗師”,和呂思勉、陳垣、陳寅恪並稱為“史學四大家”。
他的學生姚渠芳後來在《懷念在臺灣的錢穆老師》裡憶述:“錢師當年正在四十多歲壯年時期,講課聲音洪亮,結構性、邏輯性嚴謹,節節有獨到之處。”
與其他三位不同的是,錢穆並非正統學者,而是靠著自己的勤勉努力半路出家的“野路子”。
他生逢亂世,前半生家中累遭變故,動盪不斷,後半生則是長年索居,孤獨寂寞。
但在這種情況下,錢老卻從未自暴自棄,始終精神矍鑠、自強不息,在他的一生先後著書八十餘部,學術成果蜚聲中外各界。
在汗牛充棟的學術成果的平行面,是錢老強勁堅挺的體魄,他以數十年如一日的堅持和自律打破了錢家世代羸弱早夭、三世不壽的魔咒,享年九十五歲,擺脫命運的“劫數”,得以安享晚年,壽寢正終。
而種種人生的高光與奇遇無不與錢老頑強的生存意識和對命運的無情反抗有關,在他看似柔和平靜的外表下,藏著一顆堅定而不屈的靈魂。
01人生不壽大罪惡——“惜命”的生活家
錢穆此人,只要你稍微熟悉一點兒,就會知道這個行事怪異的大學者到底有多“惜命”。而錢老的惜命其實並非無跡可尋,這與他的整個家庭和早年的經歷都分不開關係。
上個世紀末,錢穆出生於江蘇無錫的一個五代同堂的大家族,父親是當地一個小有名氣的秀才。
按理說,這樣的一個大家族應該枝葉繁茂,成就斐然,是街坊鄰居人人豔羨的物件,但實際情況卻恰恰相反。
彼時的錢家彷彿被施了魔咒一般,家中的頂樑柱個個英年早逝,一條無形的生命之鏈似乎絞上了這個不幸的家庭。
錢穆的祖父年僅37歲就溘然長逝,緊接著父親錢承沛活到41歲時便撒手人寰,留下一大家孤兒寡母艱難地在亂世中求存。
儘管時局動盪,生活困窘,但是錢穆的母親依然堅信學習的重要性,將錢穆和哥哥錢摯送到學堂讀書,希望他們能有所成就、光宗耀祖。
在母親的辛苦操持和兄弟倆的不懈努力之下,窮困的痼疾一點點被清除,錢穆也在成年之後迎娶了自己的第一任妻子鄒氏。這個家庭似乎終於逐漸掙脫不停向下的螺旋,得以走上平坦的阡陌。
然而,這份得來不易的幸福卻再次被不幸的命運輕易奪走。妻子鄒氏在分娩時因難產離開了人世,隨後剛出世的兒子也似乎心有感召一般跟著母親離開了,沒能挺過來。
然而還不等錢穆收拾好不斷陷落的心緒,他的哥哥錢摯也因過度勞累而病逝,前往天國與父親團聚,年僅40歲。
親人接二連三離世,再加上自己也常年體弱多病,錢家“三世不壽”的說法無時無刻不令他恐懼不安,生活縹緲不定。他也因此常常感嘆:“人生不壽,乃一大罪惡。”
從這以後,錢穆開始思索起生命健康的重要意義,他想,倘若沒有強健的體魄和堅強的意志,就算空有一腔熱血也無濟於事,難以成就功業。
於是,在學習之餘,錢穆開始潛心研究起了獨屬於自己的長壽之道。
想要保持身體的健康,日常生活中的飲食和生活習慣就必須嚴格管理,有所歸依。
知道抽菸會損壞肺部運作,他就決然地戒掉,後來真的就一根沒再抽;自己有胃病,就嚴格控制自己的食慾,飲食清淡而節制。
旁邊的人也因此常常說錢穆此人:“能提得起,放得下,灑落自在,不為物累。”
此外,在錢穆的眾多實踐之中,打坐是他堅持得最久也是最為人們津津樂道的一項。
打坐是一種特殊的強體之法,在佛教中,它又被稱作“禪坐”或“禪定”。打坐者需要閉目盤膝,氣息均衡,腦子裡不想任何東西。
打坐的特點便是“靜”,講究一個“久靜則定,久動則疲”。
20歲的錢穆就開始學習打坐。
錢穆深知打坐對於精神和身體的好處,每天不論多忙,都會抽出時間來打坐。在這一會兒難得的平靜中驅散一天的疲憊,將精神力集中於自我,排除雜念,保持身心的自由與舒暢。
錢穆的妻子(第二任)對此回憶到:“整天在學校有應付不完的事,下班回家一進門,靜臥十幾分鍾,就又伏案用功。”
錢穆對此卻並不感到驚奇,覺得這些都是靜坐之功。可以說,錢穆對於打坐持之以恆的堅持使得他有著充沛的精力來從事學術活動和其他事務。
除了打坐,每天清晨的太極拳也是錢穆的必修課,這一項活動,他同樣是幾十年如一日地堅持。
有一次,一群地痞流氓來到錢穆執教的中學,大聲嚷嚷著,揚言要學生的財物,不給就要鬧事。錢穆得知後,專門在一片空地上打了一套太極拳。這群流氓見了,還以為校內有一位武功高手,嚇得落荒而逃。
在他九十多歲時的一天,錢穆同家人們一起觀看電視節目,播放的是某一次的體育賽事。
沒想到的是,錢穆卻對於這些“花拳繡腿”不屑一顧,他告訴家人中國傳統的五禽戲、太極拳比這些玩意兒要管用得多。
錢穆先生數十年如一日地堅持自己的健身之道,由內而外地關注自己的身體健康,虔誠而自在地生活,不僅生命的長度得以延伸,生命的厚度也同樣因此而厚重。
02勤學不輟成大家——矢志不渝的“楞”書生
如果說,強身是錢穆先生的第一層目的,那麼他的深層次目的就是治學,“惜命”的生活家的另一面卻是個勤學不輟的“楞”書生,這也是貫穿於錢老一生的底色。
錢穆自幼便跟著父親錢承沛學習文化知識,錢穆與書籍彷彿有著天然的聯結,在其他孩子還在牴觸讀書的時候,錢穆就開始纏著父親給他講《三國演義》的故事。
七歲那年,錢穆被送進了私塾唸書,也正是從這一天開始,錢穆就再也沒有放棄過讀書、治學。
後來父親去世,家中的頂樑柱轟然倒塌,雖然母親依然堅持送她去學校唸書,但也只是短短一年,學校就因為社會動盪而停辦。
因此,事實上錢穆真正接受正統教育的時間不足十年,也無怪乎後來的有些批評家稱他為“野路子”。
從學校離開之後,錢穆的身份從學生轉變成了老師。1912年春,年僅十八歲的錢穆被親戚推薦,前往小學任教,後來又轉到鴻模學校任教,開啟了他的教書生涯。
可即便做了老師,錢穆對於學識的渴望依然熱烈如初。小學四年,中學八年,“雖居窮鄉,未嘗敢一日廢學”。
數十年中,錢穆一邊吸收著知識,一邊傳授著知識。
他每天早上上班之前讀經典古籍之類難讀難懂的書,中午讀一些閒書趣書,廣泛涉獵,晚上睡前也開始研讀史書。
就這樣,日復一日的苦學使得錢穆紮下了深厚的學術素養。也正是在這期間,錢穆寫就了《論語文解》,成為了他出版的第一部著作。
多年來累積的深厚的學術素養和知識儲備很快就為錢穆帶來了人生的第一位伯樂——顧頡剛。
1929年,著名的歷史學家顧頡剛來到蘇州講學,而恰好錢穆當時剛剛跳槽到蘇州中學教授國文,兩人在學校安排的宴席中一見如故,一拍即合。
錢穆欽佩於顧頡的學識,於是將自己寫成的《先秦諸子系年》交給顧頡,希望他能過過目,提提意見。
顧頡剛欣然答應了錢穆的請求,剛剛看完開頭幾頁,顧頡剛就對行文間顯露出的驚人學識大為震撼,連連感嘆道:“錢穆不宜在中學教國文,宜去大學中教歷史”。
顧頡剛回去以後依然無時無刻不在惦記著錢穆,希望自己能夠提供一些幫助,讓這個難得的學者不至於被埋沒。
同年冬天,顧頡剛邀請錢穆為《燕京學報》寫一篇文章,錢穆得知了這個訊息後當然是義不容辭,馬上動筆。
在對《新學偽經考》充分地研究的基礎上,錢穆寫出了一篇《劉向歆父子年譜》,梳理了各家各派師承家法和經世論學的焦點,直擊今古文經長期以來的諸多紛爭。
文章一經刊出,錢穆霎時間成為了當時整個學界的“名人”,人們紛紛開始好奇這是從哪裡突然冒出來了一個絕世天才。
顧頡剛也連忙趁此機會,推薦錢穆擔任北大歷史系的副教授。
對於這一突如其來的驚喜,錢穆卻表現得非常平靜,因為他心裡清楚,這是他多年來辛苦耕耘的結果,他有實力也有底氣站上這個中國最高學府的講臺。
03閒雲野鶴覓歸處——靜心寡慾的“士大夫”
初入大學的錢穆意氣風發,揮斥方遒,迫不及待地想要在北大的三尺講臺上大展拳腳,奉獻出自己畢生所學。
但很快,錢穆就意識到了自己與這所高等的、前沿的學府的格格不入。
事實上,儘管後來錢穆大力倡導中西文化的結合,但在當時的他的身上仍然保留著很大一部分“舊”的元素,在他的內心深處,他依然認同自己是個“鄉土學人”,因而與大學乃至都市生活不相稱。
他自己也曾多次坦率承認:“餘性頑固,不能適應新環境,此固餘之所短”“餘性迂而執,不能應付現代之交際場合”。
錢穆也因此有意無意地將自己退到“主流派”的邊緣,但是這並不意味著他退縮了,相反,他想要另闢一條路重新徵服屬於他的戰場。
他依然如往日一般,潛心研究自己的學問,而對於交際名譽等看得很輕。
後來,抗日戰爭爆發,北京大學與清華大學和南開大學重組成西南聯合大學西遷至雲南昆明。
在這期間,錢穆完全地開啟了他的“省電模式”,一心鑽進自己的研究中去。
他在聯大旁邊的小鎮上單獨找了一間破瓦房,除了自己講課的日子,其他時間就回到這裡寫作。
正是這段日子的全情投入,一代鉅著《國史大綱》誕生,也奠定了他國學大師的身份。
即便後來時局趨於穩定,錢穆依舊是常常隱居“山林”而居,擇邊緣自處。另外,錢穆還給自己起了個筆名叫做“孤雲”,在他看來,鄉野獨居反而更合自己的心意。
有一次,陳寅恪到錢穆的住所來拜訪,看到錢老的生活環境,不由得感嘆:“在此寫作真大佳事,然使我一人住此,非得神經病不可。”
沒事兒的時候,錢穆也曉得給自己找點兒樂子做,他有時看看花,有時吹吹笛子,或者找個安靜又愜意的午後看一下午的書。如此一來,那些似乎孤獨又寂寞的日子便一下子生動了起來,不再那麼難熬了。
在人生的最後幾年,錢穆雙目失明。都是在妻子的幫助下查閱舊籍,寫著文章,寫成之後,又讓妻子再讀一遍,不斷修改訂正。就這樣,錢穆完成了他晚年的最後一部著作《晚學盲言》。
錢穆一生勤勉自律,朝著心之所向勇往直前。他身上有著一些新時代的烙印,但更多的是他固守一生的“士”氣,他對於中國傳統的忠貞和守望。
站在世紀的末端,他抖動著蒼老卻依然堅毅的筆告訴世人他的思想、他的決絕、他的獨屬於老一輩文人的風骨和倔強。
參考文獻
【1】《現代學人一異人——錢穆先生》 張曉唯
【2】《國學大師錢穆養生得高壽》 趙德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