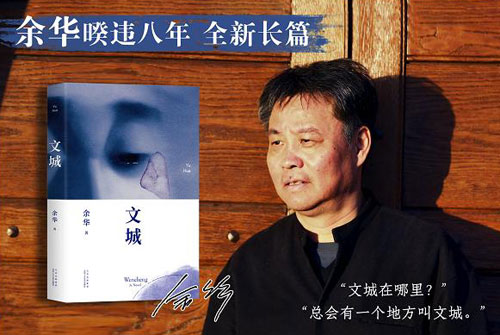作者:徐嘉莉
暌違八年,餘華的長篇小說《文城》於2021年3月出版問世。先鋒作家餘華再次對於構建逼近生存真相與本質的生命世界敘事、拓展表現人性的寬度做出新的探索與嘗試。小說延續餘華敞露生存困境與荒誕本質的意趣,及其一貫意欲展現的關於個人與命運對峙的思考與闡釋,以混亂倒錯的時代境地構成對抗性張力,書寫時代洪流裹挾之下個體的生存姿態與抉擇。
在作品《文城》中,人物無論是主動選擇還是被迫逃離,都因流亡而獲得一種特殊的生存狀態,並由此賦予生存以悲劇、苦難與英雄主義的多重意義。由一種生存方式發展為情感寄寓與理想追求的生存形態,流浪伴隨林祥福的心理歷程有了形而上的抽象意義,而漂泊感和失根狀態下的無歸屬感使得此意識與個體自我身份的解構與重建產生關聯。
逃離與眷戀兩種心態使得流浪意識在林祥福身上的呈現具有複雜性,一方面對妻子的承諾支撐他永不停歇地追尋,另一方面難以完全從過去生活模式中剝離,讓他陷入了自我質疑與迷茫。“葉落該歸根,人故當還鄉”是林祥福作為接受傳統書塾教育和家庭觀念長大的鄉紳心中根深蒂固的觀念和本能的選擇,回家意願的多次萌發和生長、邊緣人的尷尬處境使得流浪與歸鄉之間的矛盾貫穿並撕扯著他的流浪生涯。
同時,林的出走本質上具有一種荒誕性。作為信念支撐他尋找的文城自始至終是不存在的,而他與小美陰差陽錯地在城隍廟前近在咫尺卻又天人永隔,此後被動地在命運與時代的洪流中牽扯著經歷匪禍裡的動亂與犧牲,於荒誕不經中成為喪失選擇權的流浪者。
《文城》在某種程度上可解讀為對魯迅“出走之後何處去”的命題及出走話語敘事技巧的再思考與致敬,是對出走之後的荒誕歸宿與選擇權喪失的縱深探索,而“離去—歸來—離去”的結構模式隱喻著身份認同與家園歸屬的相關表達,將存在主義等現代性思想寄頓於人物空間與精神的雙重流浪之中,以此涵納探尋根性與身份歸屬的現代思想和話語表達。在時代的夾縫中回望,無法抵達的望鄉讓林的生命有了零落無常的悲劇質感。而他出走與迴歸之間的搖擺實際上是流浪意識與傳統觀念根植之間拉扯與遊移的對映,這種猶豫構成了他的不安、尋覓不已和抉擇的複雜性,同時也加深了他的流浪中荒涼無望的悲慼意味。
流浪形態——生存、情感的雙重流浪與生命倫理
《文城》的生存流浪表現在流浪者為了尋找精神根系與靈魂皈依而與本土相分離的形態,經歷種種劫難折磨與鄉愁的憂慮,產生與群體存在處境和精神處境相分離的生存形式與心理狀態,並在歸來的意願與離去的需求中尋求平衡。文字顯性的生存流浪形態由林祥福攜女南下尋妻的故事主線呈現,居無定所的憂愁傷感、求而不得的無奈無望伴隨著他漫長而無望的流浪旅程。餘華將江湖俠氣的快意恩仇融入顛沛流離的流亡和連綿苦難的敘寫中,透過建構期望以消解苦難,削弱人在歷史與命運中的無力感,同時強化了對生命的脆弱與柔韌、對悲劇底色與荒誕核心的展現。
文字對內在精神流浪的展現比生存流浪更為複雜和深切。以夢魘般的虛無感和心靈無歸屬感為代表呈現出精神世界的幻滅、迷失與流浪,他終其一生找尋肉體的安頓與情感的寄託,死後踏上落葉歸根的回鄉之旅,完成精神殘缺復歸於完滿的過程。那個在信仰之路上虔誠跋涉的朝聖者永不停歇地流浪,以定居溪鎮為節點,開始與過去進行和解,他小心地庇佑女兒林百家長大,在亂世裡掙扎著生存,自此過往種種開始沉寂。那些晦澀與惡意,羈絆與美德,最終幫助他完成從傾斜走向平衡的精神療愈之路。
小美的悲劇性情感流浪主要在背叛與信任的交鋒、歸家意願與逃離快感的權衡中展現出來。餘華在深層的對立與衝突中審視、反思生命中那些愛而不得的荒誕和情感放逐等生存命題,在放縱與壓抑、自由與約束的平衡中重建信仰,從生命倫理意義上尋找生存的本質價值與情感的終極歸宿,透過對情愛與肉體的微妙、背叛與愧悔的善惡等倫理本質的挑釁式處理,以漂泊的外在表現形式,消解與對抗傳統的單向度道德模式與情感抉擇。
望鄉情結下的異鄉漂泊與故土迴歸
林祥福的流浪與紮根過程隱含著對家園意識與身份認同的探索,肉體和精神上漂泊錯位的狀態賦予他無所適從的悲劇感和缺失感。從林祥福留遺書請翠萍轉交開始,引出了回望來處與故土迴歸的主題,多次歸鄉的動搖和猶豫從情感的歸宿和生命倫理角度為人物的抉擇展現出複雜性。羈旅鄉愁和迴歸意向的展現並沒有削弱其信念感和孤獨意識,反而透過對懷舊之念的思索與拷問,完成了倫理層面的對於人物流浪情結與精神漂泊中價值取向的多樣化呈現和多層次展示,包括對流浪價值的深度審視與反思。
對文城指向的家園歸屬的構建和尋找,不僅是在信仰解構與重建時期帶來傳統禮制與信義的讚歌,也是在更深層面對精神曠野的呼喚與迴歸。尼采說,“真誠的人——我如此稱呼在天神的荒漠上跋涉和虔誠之心破碎的人。”尋找的意義在於抗衡故園破碎的焦慮、找到劫後餘生或愛而不得的失落與恐懼引流的渠道,以填補精神家園缺失而帶來的宿命般的斷裂感和靈魂荒蕪。流浪者始終有著迴歸故土家園的指向,但是當他們從踏上異鄉之路的那刻開始,迴歸就只能成為一種理論上的可能,而尋找結果指向虛幻,導致了漂泊者的失落與迴歸者的再度放逐。
最終小美死於林祥福到達溪鎮的當天,使得林祥福的尋找與流浪指向虛無,荒誕感使得小說獲得超越性,抽象為形而上的關於人類精神歷程的永恆象喻。林在漫長的尋根之旅中完成自我身份與精神歸宿的形塑和體認,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文城究竟在哪裡、有沒有可能找到文城,已經不再重要了,對文城的找尋永遠在路上。
海德格爾認為,“無家可歸是現代人的命運”。從《文城》中我們能夠看到餘華對流浪意識和家園觀念的探討,他將這種流浪敘事放大處理,融入對於身份認同轉化、家園選擇與重新建構的可能性的思考。餘華把《文城》定義為“非傳統的傳奇小說”,文字中的自我放逐與迴歸、漂泊感等是作者自身“原泊”意識的某種對映。餘華說,“我只要寫作,就是回家。我的每一次寫作都讓我回到南方。”正因為如此,故事裡林祥福得到後失去、一生永不停歇地找尋,文城最終也指向餘華心理的暗示、想象的歸宿。
(作者徐嘉莉為湖南大學文學系在讀碩士)
來源: 光明網-文藝評論頻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