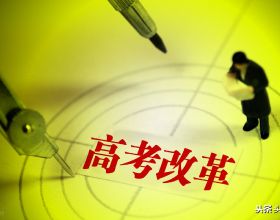從表面上看,國際法庭作為一個高大上的司法機構,理論上是完全按照法律在運轉和運作的。但在實踐中,由於國際法庭的法官來自不同文化與法系,在法庭運作過程中,有時候會不可避免地摻雜政治。那麼,當政治進入國際法庭的時候,法官們是如何處理的呢?這裡介紹三個相關案例,或許能給我們一些啟示。
案例一:東京審判中的梅汝璈
在電影《東京審判》中,大家都看到了中國籍法官梅汝璈在面對法官排座時的表現。由於庭長(澳大利亞籍)希望英美籍法官能夠坐在自己兩側,因而提出了“五常居中”的座次原則。
但梅汝璈很快發現,根據此原則,中國籍法官的席位理應在庭長旁邊,而不是英美法官在其左右側。梅汝璈因此而據理力爭。儘管如此,庭長依然沒有打算採納其建議。
在開庭前庭審預演的當天,庭長韋伯發動了“突然襲擊”。在法官會議室,韋伯宣佈入場行列及坐席的順序是:美、英、中、蘇、法、加、荷、新、印、菲,並說這是經過盟軍最高統帥同意了的安排。
對於庭長的這一宣佈,梅汝璈認為,雖然其表面上似乎符合五強居中的意思,但要英、美居中的用意表露無遺,於是他脫下法袍,表示不能參加這樣的預演,並離開會議室,回到自己的辦公室,準備離去。
韋伯根本沒有料到梅汝璈會有如此反應,趕緊來到中國法官辦公室攔住梅汝璈,並“解釋”道:“盟軍最高統帥要英、美居中的意思,無非是因為他們對英、美法程式熟識些,純粹是為了工作上的便利著想,並無歧視中國的意思。”又說:“中國的席位仍然在蘇、法之上,是五強的中堅。”梅汝璈並不接受這一說辭,同時也拒絕接受韋伯所稱的“今天只是預演,座次問題可以再討論”的說法,因為他十分清楚,大批新聞記者和攝影師等候在審判大廳裡,如果今天法官按照錯誤的排序預演開庭,被報道出去,就會造成無法改變的既成事實。
最終,經過他的堅決鬥爭,預演的入場順序和法官座次就按照受降簽字國的順序進行。
案例二:顧維鈞與前蘇聯法官之間的較量
顧維鈞於1957年當選為國際法院法官。到海牙赴任之後,根據國際法院院長的建議,顧維鈞逐一拜訪了其他法官。在拜訪前蘇聯籍法官科吉夫尼科夫之前,他曾有過顧慮,擔心該法官作出不友好之舉。在其他法官安慰和事先做好必要資訊溝通之後,他於1957年5月6日對該法官進行了拜訪。科吉夫尼科夫熱情接待了顧維鈞,說顧氏在蘇聯很著名,很高興與顧相識,並且說國際法院只是處理司法問題的機構。
1957年5月7日,顧維鈞作為法官第一次參加國際法院全體法官參加的不公開的案情評議會議。在國際法院院長對他就任法官表示歡迎之後,顧維鈞表示了簡短的致謝致辭。隨後,在輪到科吉夫尼科夫發言時,科氏稱,他反對顧任職於國際法院,並說蘇聯不承認派遣顧的國家。對於科氏的此發言,國際法院院長稱,國際法院是聯合國的司法機構,一切政治問題不應在法院會議上提出。隨後,院長請顧維鈞發言。顧發言稱,“院長講得很正確。聽了他的講話,我覺得沒有什麼可補充的了。鑑於法院規約第16條禁止行使任何政治或行政職能的規定,我僅僅願意表示,科吉夫尼科夫先生說了這樣一些話,令我驚訝而已。由於院長已向科吉夫尼科夫先生闡明,我不願意再多佔用法院會議時間。”
會議結束之後,科吉夫尼科夫本人走向顧維鈞解釋稱,請顧相信他對顧本人毫無惡意。
案例三:倒黴催的汗法官
Muhammad Zafrulla Khan(汗法官,巴基斯坦籍)於1954年第一次當選為國際法院法官。9年任期屆滿之後(1954-1961),他代表巴基斯坦常駐聯合國。1962-1963年,他當選為聯合國大會主席。1964年,他再次當選為國際法院法官,任期9年。
在他第二次當選為國際法院法官期間,國際法院正在審理衣索比亞和賴比瑞亞訴南非“西南非洲案”。1962年,國際法院就南非所提出的先決反對作出了判決(表決票數是8:7),駁回了南非提出的先決反對,裁決國際法院對該案擁有管轄權,訴求具有可受理性。其中,澳大利亞籍法官Spender投了反對票。
在1964年法官選舉之後,澳大利亞籍法官Spender當選為法院院長。為了謀求推翻1962年先決反對判決,Spender以汗法官在任聯合國大會主席期間曾參與西南非洲國際調查委員會活動為由,通知該法官稱,根據《國際法院規約》第24條,汗法官不應參與本案的審理,並稱這是法院全體成員的決定。實際上,此決定是院長自己的決定。
汗法官儘管此前已在國際法院任滿一個完整的任期,並有擔任聯合國大會主席的經歷,在國際場合外交鬥爭經驗理應是豐富的,遺憾的是,對於Spender院長的前述說辭,其卻沒有表示出絲毫懷疑,完全接受了,而沒有考慮到《國際法院規約》第24條第3段所賦予他提出異議的權利。
結果,在汗法官沒有參與此案審理的情形下,法院法官經過表決,最終以8:7(院長最後投決定票)的微弱多數,推翻了先決反對判決,稱自己對此案無管轄權。
當然,在判決作出之後,汗法官總算知道了前述決定是院長自己的決定,而不是法院全體法官的決定。得知真相之後,汗法官曾經暴跳如雷。然而,一切已經為時已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