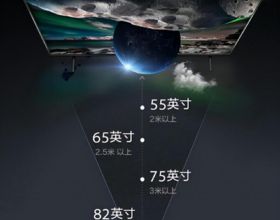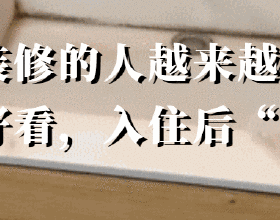《紅樓夢》中曹雪芹這樣描寫黛玉:
兩彎似蹙非蹙罥煙眉,一雙似喜非喜含情目。態生兩靨之愁,嬌襲一身之病。淚光點點,嬌喘微微。閒靜時如姣花照水,行動處似弱柳扶風。心較比干多一竅,病如西子勝三分。
癭木便如同黛玉一般,透著一股病態美。
癭木根雕賞件
北宋蘇軾曾在《答李端叔書》中,這樣描述樹木之癭:
木有癭,石有暈,犀有通,以取妍於人,皆物之病也。
然而,“物之病”,卻能“取妍於人”,讓欣賞者“以之為美”,這種美的根源不在“物”,而在於“人”,癭木之貴,在於人的審美之情趣。
清十八世紀 癭木“荔枝”蓋盒
從明清時期,聰慧的匠人們就開始用癭木雕刻和器物的製作,賦予它新的用途,並讓大眾都接受,這種病態變成了一種很高層次的審美。
明晚期 黃花梨嵌癭木小方炕桌
明代,蘇式傢俱一向用癭木作為裝飾材料,明初傢俱中已有運用。但由於癭木因其木紋紋理不似其它木料,紋路的錯綜複雜導致木料缺少韌性,且癭木較其它同樹種木料稀缺,所以癭木通常被用於製作小擺件,或者剖成薄皮作為傢俱表面的鑲嵌。
明末清初 黃花梨攢靠背活屜四出頭官帽椅
而清中期之後,清朝大量使用癭木,且多與珍貴硬木相配。多與用作桌心、案心、幾心、椅背心、椅面心、櫃門心等,也有單獨或與其他木材搭配作裝飾用,將木材各自的鮮明特徵有機結合,精美絕倫、相得益彰。
清中期 黃花梨鑲癭木無閂杆圓角櫃
清 紅木鑲癭木竹節工扶手椅
民國 癭木面銅內膽雙屜香火盆
但從清朝開始,由於大量掠奪性開採;
在民國以後,可用的癭木變得十分稀少。
而今,個性美感的癭木更是難得一見,很多國際傢俱設計師往往以癭木設計為提升突破口,以癭木自生形態及畸變形態為藝術創作物件,透過構思立意、藝術加工及工藝處理,創作出傢俱、器物等藝術形象作品,在近代逐漸成為見證自然與設計融合的至高藝術。
“其紋脈無間處,雲是老樹千年根也”。因紋理天然奇特,瑰麗玄妙;雖奇形怪狀,褶瘤交雜,洗盡鉛華,萬千雕琢之後,綻放溢彩的癭木給世人的,是美的嗟嘆,更是見證古今匠人那顆不追求極度完美,將審美包容永珍,亦求返璞歸真的工匠之心。
點選連結,可關注更多實木文化:致敬大師系列 | 坎爺和卡戴珊“極簡豪宅”背後的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