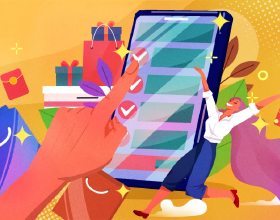差不多所有的散文,都要用散文家的筆調來寫。
這裡單拿敘說歷史的散文說事,是因為我看到的歷史散文,因為遙遠的年代,因為史實的限定,生硬和糾結,筆調放不開。
好一些的,是1992年出版的《文化苦旅》(餘秋雨著),成了一系列文化、歷史散文的代表作,成功點燃了大眾讀者的閱讀熱情。那時我也成了大眾讀者,喜歡讀這類散文,喜歡其中偶爾會有的散文家筆調。接下來是撥號上網的年代,沒幾年網路閱讀被喚醒了,靜心閱讀的閱讀者少了,靜心寫作的寫作者少了,一定程度上阻擋了歷史散文一步步成熟。
表面上看,把一篇歷史散文寫得像散文,就有了散文家的筆調。可是,事情沒有那麼簡單。
“筆調”這個詞,是傳統說法,源於用筆在紙上寫作的時代,一般指的是風格。要是再展開一點,散文家的筆調,也包括了散文家的大部分寫作能力,有看待事物的方式,組織語言的方式,等等。還有個重要因素,它是好作家才有的胸懷。
實際上,這是很難做到的事情。
用散文家的筆調敘說歷史,這方面比較突出的一個範例,是亨德里克·威廉·房龍的《寬容》。
我們先來看這部書對某個歷史環境的描述。你知道,無論是寫事件,還是寫人物,都是離不開環境的。
在《寬容》第25章《伏爾泰》裡,有一段描述,恰好把歷史環境和人物連線了起來。
“伏爾泰生活的時代是個充斥著極端的年代。一方面,極端自私和腐敗的宗教、社會和經濟體制早已過時,另一方面,一大批熱心的年輕男女想帶來一個黃金時代,卻是個沒有地基的空中樓閣,是他們虛無的美好願望。”房龍接著寫道,“他是個不引人注意的公證員的兒子,體弱多病,詼諧的命運把他扔進了鯊魚和蝌蚪的大漩渦裡,要麼溺死,要麼游出來。他願意游出來衝到岸上。他長期同逆境作鬥爭的方法常常令人懷疑。他乞求、奉承、充當小丑的角色。”
伏爾泰是法國人,比房龍早生了近二百年。他寫過劇本、詩歌、哲學論文、物理學論文,用房龍的說法,這些好不到哪裡去,還有他的歷史著作,既不可靠又很枯澀。可是,作為一切愚蠢、狹隘、專橫、殘忍事物的敵人,他勇敢又堅韌,他的影響力一直持續到1914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和房龍生活的時代連線在一起了。“布丁好壞得吃了才知道。同樣道理,像伏爾泰這種人的成敗,應該用他對同胞做的實際貢獻來衡量。”房龍寫道。
再來看看,房龍對伏爾泰的進一步描述。
“他是鵝的天敵,因為他使用的鵝毛筆比二十多個普通作家用的還要多。他屬於文學巨人那一類人,他們都孤獨一人,在最可怕的逆境中寫的文章也和作家協會所有作家寫的總數一樣多。”房龍寫道,有一年伏爾泰被趕到鄉下,“他在骯髒的鄉下客棧裡伏案疾書。在鄉下,天天都有二十四小時的閒暇時間,伏爾泰開始非常認真地學習文學並且創作出了他的第一個劇本。十二個月的清新空氣和有益健康的單調生活之後,他被准許回到花天酒地的首都,馬上寫了一系列諷刺攝政王的文章來彌補失去的時間。其實對於那個下流的老傢伙,罵他什麼都不過分,但是他一點也不喜歡伏爾泰這樣公開的宣傳……”
這還是寫歷史人物嗎?和我們現實中的人物有什麼區別?這樣的伏爾泰和這樣的攝政王,都走出了歷史,成為我們身邊的一個人。
在寫作中,很多作家都想與歷史人物拉近距離,可是極少有人像房龍拉得那樣近,聽得見歷史人物呼吸和咳嗽的聲音。
這是房龍個人化的風格,也是他個人化的散文家筆調。
同時,房龍又在拉遠這個距離。
他會把歷史人物從其時代、地域、民族、黨派、宗教等具體環境里拉出來,拉到人類生活的大背景面前,用看待人類一個普通成員的眼光來觀察描述。
比如,寫伏爾泰與一切愚蠢專橫的事物作戰,房龍只找個現代常見的宣傳戰角度,讓普通讀者很容易理解。社會彷彿一臺龐大機器,固執,殘忍,依靠惰性的力量運轉,但它的弱點是有些事情只能在暗中行事。它的對手伏爾泰,有冷靜,有韌性,利用一次又一次宣傳戰,打出了他的成果。
房龍生動描寫了三個具體事例後,歸納說:“這些重拳開始見效了。長舌老婦和一群老法官造成的恐怖事件結束了。有宗教私心的法庭,必須暗中行事,偷偷摸摸地動手,才能成功。伏爾泰採取的進攻手法,那些法庭根本沒法招架——他打開了所有的燈,僱了一個陣容龐大的樂隊,邀請公眾一起參與,然後讓他的敵人儘量施出所有卑劣手段。結果,他們一籌莫展。”
細讀這些文字,你會看到我在前面說到的散文家的寫作能力,其中看待事物、組織語言的方式,舉重若輕,靈活俏皮。可是要欣賞到好作家才有的胸懷,還要看這部書的更多章節,包括序言。
《寬容》的序言裡,房龍寫道:
“在寧靜的無知山谷裡,人們過著幸福的生活。……晚上,村民們飲畢牲口,灌滿木桶,便心滿意足地坐下來,盡享天倫之樂。守舊的老人們被攙扶出來,他們在蔭涼角落裡度過了整個白天。對著一本神秘莫測的古書苦思冥想。他們向兒孫們叨嘮著古怪的字眼,可是孩子們卻惦記著玩耍從遠方捎來的漂亮石子。……在無知山谷裡,古老的東西總是受到尊敬。誰否認祖先的智慧,誰就會遭到正人君子的冷落。所以,大家都和睦相處。恐懼總是陪伴著人們。誰要是得不到園中果實中應得的份額,又該怎麼辦呢?深夜,在小鎮的狹窄街巷裡,人們低聲講述著情節模糊的往事,講述那些敢於提出問題的男男女女。這些男男女女後來走了,再也沒有回來。”
前面這一段,有十多個像詩歌一樣的分行,也有詩歌的濃縮精煉。現在我給它去掉分行,詩歌意味也沒減少。這好像是在提醒我們,詩歌的重心不在於分行,而是它的意味。沒有意味的文字,分行之後也不是詩歌。
品讀這一段之後,你能不能看出,這樣好的文字,作者竟是慕尼黑大學的一位歷史學博士?你有沒有想到,他的文字之好,也與他最初獲得的康奈爾大學文學士有關?走出那所大學的作家,比較聞名的有賽珍珠、託妮·莫里森兩位諾獎得主,有散文和童書聞名於世的E·B·懷特,也有中國作家胡適、冰心、徐志摩。
請你再品讀一下,然後確定:這裡凸現的意味,是不是很好的作家胸懷?
什麼樣的作家胸懷是好的?《寬容》不再說了,我們來看房龍《地球的故事》。
其第一章寫道:“它擁有豐富的採石場、泥土和森林,還有草原上成群的綿羊,開滿藍色鮮花的海濤般起伏的亞麻田,還有中國桑樹上勤勞的蠶蛹。我們的家是一處樂園,它奉獻給我們太多的恩惠,每個男人、女人和孩子都可以得到屬於自己的那份,同時也為未來那些可以想見的日子留下一點剩餘。”
對於這個家園,房龍覺得,我們不可以再像父輩那樣肆意劫掠。“我們所有人都生活在同一顆行星上,所以其他任何人的幸福便是我們的幸福,其他任何人的災難也無疑是我們的災難。……如果人類不想那麼早就滅絕的話,請牢記這樣一句話:我們同在一個星球,我們所有人都應該共同為我們所生活的世界的安寧承擔責任。”
我個人以為,散文的題材比詩歌和小說開闊得多,所以一旦真正遇到題材的需要,不寫散文的詩人和小說家很少,不寫,很可能就表現不了那麼開闊的胸懷。
特邀編輯:董學仁
來源:中國青年報客戶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