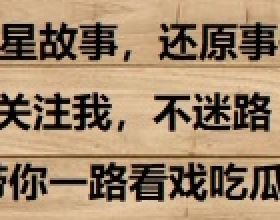“太幸運我讀到了這本書!”“強烈推薦,古老、簡潔而清晰的東方智慧。”在全球圖書網購平臺,《道德經》譯本多年來得到大量外國讀者的推崇。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統計,世界各國經典著作中,中國的《道德經》是被翻譯成最多種語言、發行量最大的傳世經典。
2019年,日文版中國科幻小說《三體》發售當天,旋即登上日本亞馬遜文藝作品銷量榜榜首。“《三體》熱”席捲海外,創造了中國當代文學譯作有史以來的最高世界館藏紀錄。
從哲學經典《道德經》到科幻文學《三體》,中書外譯經歷了從懵懂前行到積極探索的轉變。透過外譯走向世界的中國書籍,在對話與建構中,成為中華文化“出海”的重要載體。走向世界的“中國書架”在摸爬滾打中“開枝散葉”,但似乎遠未“枝繁葉茂”。在機遇與挑戰並存的時代,如何讓中國書籍向外“走深走實”?
1.中書外譯,從歷史中款款走來
“大規模中書外譯可追溯至16世紀末的來華傳教士,迄今已有400多年。雖並非以傳播中國文化為主要目的,但他們在客觀上完成了文明的傳遞。”北京外國語大學英語學院副教授王穎衝說。
“明末清初來華的傳教士,知名的有70多人。”華東師範大學終身教授、中國英漢語比較研究會名譽會長潘文國發現,這一時期,西去的主要是中國經典,比如利瑪竇翻譯的《四書》。
據考證,中國歷史上譯入歐洲的第一本著作,是1590年西班牙傳教士雅各布森翻譯的《明心寶鑑》。中書外譯的專業化發展始於19世紀下半葉。鴉片戰爭以後,中書外譯的數量和種類大幅提高。
與此同時,中國譯者也系統投入到中書外譯的事業中。例如,辜鴻銘將《論語》《中庸》和《大學》翻譯成英文。“這與當時的留學政策、國內外語教育大環境的變化密切相關。”王穎衝說。
改革開放以來,中書外譯“國家隊”逐漸壯大。20世紀80年代風靡一時的“熊貓叢書”,為中國文化走向世界修了“一條實實在在的路”。“大中華文庫”“中國圖書對外推廣計劃”“國家社科基金中華學術外譯專案”等一系列國家翻譯實踐,極大滿足了中國作品“走出去”的渴望。
“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更是拓寬了中國出版“走出去”的想象空間,給了中國出版更多互學互鑑、交流互動的機會。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簡稱“外研社”)與中國圖書進出口總公司合作,把中國當代著名作家的文學作品,如餘華的《活著》、王剛的《英格力士》、蘇童的《米》等輸出到多個“一帶一路”國家。
時至今日,中書外譯的舞臺上依舊活躍著眾多國外漢學家。比如,出生於1939年的美國漢學家葛浩文,已經翻譯了30多箇中文作家的60多部作品,被喻為中國文學在海外的“首席接生婆”。
物換星移,一些青年漢學家也攜譯作嶄露頭角。
《傳奇女書》是清華大學教授趙麗明的力作。意文版《傳奇女書》被義大利著名雜誌《全景》評為今年“義大利最值得閱讀的50本書”之一。彷彿“深山裡的野玫瑰”帶著南嶺的清芬和瀟水的溫情,走出了“與世隔絕”,為更多世界另一頭的人們“採擷”。
讓流傳於湖南省江永縣的女書文字走進義大利人文學視野的,是義大利譯者茱莉(Giulia Falcini)。“義大利人對於中國文化的喜愛和好奇與日俱增。”茱莉發現,莫言、餘華、蘇童等中文作家已在義大利出名,“他們的作品非常暢銷。”
文化,只有在不斷的交流中才能發展和延續。
“我十分相信故事的力量。故事的交換幫助人類理解世界,也能幫助我們理解自己。”從事中國文學作品翻譯與研究的思黛(Stefan Rusinov)來自保加利亞,曾翻譯過莫言《檀香刑》、劉慈欣《三體》等諸多中文書籍的保加利亞語版。
十幾年前在華中師範大學學習中國現當代文學時,“80後”思黛就“很想把學到的好東西分享給同胞們,推進文學對話”,因為“這些作品極大地豐盈了我的精神世界,很希望它們能給更多保加利亞讀者帶來相似的收穫。”
2.逆差明顯,尚待走出幽谷
縱觀20世紀,中國翻譯的西方著作品種數不勝數;相較之下,輸出西方的中國文學品種與此極不成比例——“中譯外”與“外譯中”整體上相差100倍。
近年來,隨著中書走向世界的步伐不斷加快,“中譯外”作品在數量上有明顯提升。但是中書的進出口貿易仍存在10∶1的逆差,與中華文化的悠久歷史和厚重內涵並不匹配。
逆差的背後,一系列問題亟待深入思考。
什麼是中國文化中最值得介紹給世界的?這是中書外譯“走深走實”繞不過去的問題。
上海交通大學智慧傳播研究院助理研究員王大可發現,相較於政治、經濟、科技主題圖書,文學和文化類圖書佔比明顯較高;相較於具有較高學術含量的著作,“概論式”圖書佔比明顯較高。“如果中國圖書對外輸出的重點僅僅停留在文學等議題上,就可能在無形中放棄了對世界政治經濟等重大議題解釋權的爭奪。”
“20世紀90年代,日本的中書譯本有所增加,但政經類出版物大多聚焦中國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問題。”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際商務漢語基地副主任郭德玉發現,不僅出版社多以中小型為主,譯者多為日本人,讀者群體也相對固化。“應該說,譯作帶來的正面影響不大。”
擇當譯之本,是提升文化影響力的關鍵。
中書外譯對譯者能力素質提出了怎樣的要求?譯事之甘苦,譯者最知曉。
“翻譯昌耀,卻不懂詩歌,這是不可想象的。”湖南文理學院文史與法學學院副教授肖學周認為,中書外譯必須具有綜合素養,然後再看外語水平。
“最難翻譯的是語言很獨特的作品。”思黛正在翻譯的中文短篇小說《棋王》,語言樸實而飄逸俊美,“文字中帶著某種古詩的味道,但用保加利亞語再現這種感覺,需要重新設計一種語言風格。”
為了翻譯好《傳奇女書》,茱莉每年都遠赴湖南江永,與小鎮上的人們生活在一起,瞭解女書文字背後的文化生態與地方風俗,“必須瞭解書籍背後的歷史文化,這非常難,也很重要。”
王穎衝認為,文學翻譯首選“譯入”母語,即中國文學譯成外語應該優先考慮外國譯者。“在國外,參與中書外譯的譯者以本國漢學家為主。但這一隊伍數量還非常有限。”
另外,受限於專業背景、視野、文化積澱,外國譯者要在譯本中完全再現原文所包含的中文語境含義,保留其獨特的文學藝術生態,確非易事。
“從理解的角度看,再高明的西方翻譯家,在從事中國古籍英譯的時候,不出現錯誤以至嚴重錯誤的情況是不多見的。”潘文國說。
如何跨越偏見、共享文明成果?曾任非洲馬拉維大學孔子學院中方院長的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助理研究員尤永紅指出,非洲一些大學圖書館關於中國的圖書資料並不多,其中一些著作帶有西方話語色彩。“如何在中書外譯的事業中降低‘文化折扣’,向世界展現一個真實立體全面的中國,仍需要久久為功的推動力量。”尤永紅說。
3.通盤謀劃,應中外合作、以我為主
“當我們把中書外譯作為一項重要的事業來對待的時候,就不能採取零敲碎打、‘抓到籃裡就是菜’的隨意辦法,必須有通盤考慮、系統認知。”潘文國強調。
不謀全域性者,不足謀一域。
在新加坡國立大學就讀的中國留學生沈天瑜觀察發現,中國的治理模式、減貧事業、科技創新,都是外國同學比較關注的議題,而新加坡對中國發展實踐進行全方位描述、深入分析的譯作還比較缺乏。“外國同學只能透過網際網路來碎片化了解關於中國的資訊。”
對中國發展之道好奇的,不只是外國學生群體。隨著中國科研和學術產出及影響力快速增長,國際學術界希望更深入地瞭解中國同行的研究情況。“尤其是當代中國經濟發展、社會治理、管理創新、產業模式等題材的圖書受國際學界關注。”外研社相關人員介紹,該社外譯的厲以寧《中國經濟改革發展之路》、陳雲賢《市場競爭雙重主體論》、徐湘林《中國社會轉型與國家治理》等書籍備受海外學界關注。
“在講好中國故事的同時,也需注重從中國視角‘講好世界故事’,讓中國書籍‘走出去’的過程與中國主體性世界觀的生髮過程同頻共振。”上海交大媒體與傳播學院院長李本乾說。
內容之外,外譯人才的培養和支援也是關鍵之匙。
“‘中外合作、以我為主’的翻譯隊伍建設是比較理想的譯者模式,既可以確保原著的立場觀點不走樣,也可以做到譯文語言流暢、地道可讀。”經過對中書日譯的長期考察,郭德玉指出。
面對高水平外譯人才匱乏的現狀,亟待儲備一批包括中國本土譯者、海外華人譯者和國外漢學家在內的翻譯和審訂隊伍。當前,僅僅依靠海外漢學家們譯入母語,還無法滿足我國對外傳播的預期。郭德玉認為,“大力加強‘中譯外’人才的培養,精通外語、具有專業背景、廣博知識儲備的高水平翻譯人才,才是翻譯事業生生不息的希望所在。”
“很希望看到中國文學在自己國家獲得更大的影響力。”對於思黛等中國文學的“小語種譯者”,他們期盼著得到更充足的翻譯與推廣支援,讓他們更輕鬆地從事所熱愛的中國書籍翻譯事業。
2013年,中外高階人文交流品牌專案“新漢學計劃”正式啟動,透過“博士生培養”“綜合學術研究”與“海外高階中文翻譯人才培養”等專案,致力為海外學生學者、各界精英人士與優秀青年提供優質資源,培養一批精通母語和漢語、文化學術背景多樣、科研能力突出的漢學與中國研究學者,服務國際中文教育大局,積極推動中外語言交流合作與世界多元文化互學互鑑。
譯作傳播不僅重在譯者,也離不開出版發行。
“從出版的角度,我們打破同行競爭的壁壘,國內外出版社共同策劃、合作出版、合力營銷,將優質中國圖書內容傳播給世界”,浙江大學出版社國際合作部主任徐倩介紹,“選題國際化、出版服務化、營銷全球化”是出版社提升版權“走出去”的重要路徑。
多方面的合作運作模式、多主題的選題空間、多渠道的發行場域、多模態的呈現形式,對於提升中書外譯質量、讓更多中國文化思想在海外圖書市場上亮相,都至關重要。
在深刻而宏闊的時代之變中,中書外譯更需堅定文化自信,拓寬世界眼光,在知己知彼中為多層次文明對話作出更大貢獻。
(本報記者 肖人夫 本報通訊員 舒天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