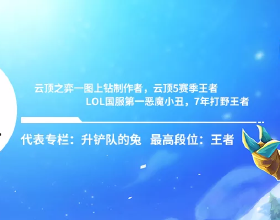作者:吳仰湘,系湖南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
今天只要提起皮錫瑞,人們就會想起《經學歷史》和《經學通論》。這兩部著作,是皮錫瑞為晚清新式學堂編撰的經學教材,一百多年來風行於世,堪稱新經學教育的經典,也給這位矻矻窮經的學者帶來經學教育名家的桂冠。
皮錫瑞少時嗜好詞章、議論,直到壯年才轉向經學。他從訓詁、名物入手治經,研讀諸經註疏,進而精究今文《尚書》,同時疏證鄭玄經注,至晚年融貫群經,創發大義。他一生著述等身,成就絕特,蜚聲學林。章太炎曾稱讚他的《尚書》研究“抱一家之學,鉤深而致之遠,上規平津,下模西莊”(《校經生》),夏敬觀又表彰他的鄭學研究“暢微抉隱,扶翼西漢今文之學,殆超越乾嘉諸儒而為清代經師殿後之一人。”(《善化皮鹿門先生年譜序》)總體而言,皮錫瑞治經雖然宗主今文,但始終堅持“解經當實事求是,不當黨同妒真”(《今文尚書考證凡例》),能夠融採眾長,折中於是,因而學風謹嚴,持論平實。如徐世昌主編《清儒學案》,即以皮錫瑞“研精漢儒經訓之學,宏通詳密,多所發明”,專門設立《鹿門學案》,並評析他的經學特色是“博洽精審,亦能折中群言,無所偏激”,可謂公允之論。
身為經學大師的皮錫瑞,同時也是晚清湖南教育名家。他因家計困窘,光緒十六年(1890)就遠赴湘南,出主桂陽州龍潭書院講席。兩年後,得江西學政龍湛霖力薦,皮錫瑞獲聘為南昌經訓書院主講,直到戊戌政變後才被迫離職。他教導院生“說經當守家法,詞章必宗家數”,大力變革經訓書院學風,“一時高才雋秀,鹹集其門”(皮名振《皮鹿門先生傳略》)。光緒二十八年(1902),久被禁錮的皮錫瑞趁著興學風潮,受聘創辦善化縣立小學堂。此後,他相繼執教於湖南高等學堂、湖南師範館、長沙府中學堂,並一度擔任善化小學堂監督,短期代理湖南高等學堂總理,兼任湖南省學務公所圖書課長,為湘省新式教育鞠躬盡瘁,有“經師人師”之譽。
參與新式學堂管理,以及多年講授經學、史學、倫理等課程,促使皮錫瑞思考經學命運,積極革新經學教育。隨著書院改制、科舉停廢,教育體制迅速更新,經學地位驟降,經學教育陷入空前困境:“今學堂因功課繁多,往往偏重藝能,反輕聖教,經、史、國文,鐘點甚少,或且並無經學、國文。”(《皮錫瑞全集》第12冊,中華書局2015年版,第556頁)新教育重藝輕道,已使經學課程名實難符,崇尚西學新知的激進派更公開鄙棄經學,皮錫瑞為此痛言:“近日邪說流行,乃謂中國欲圖富強,止應專用西學,五經四書皆當付之一炬。辦學堂者,惑於其說,敢於輕蔑聖教。民立學堂,多無經學一門;即官立者,亦不過略存餼羊之遺。功課無多,大義茫昧。離經畔道,職此之由。”(同前,第557頁)為在新教育中突出經學的地位,他從改善經學課程設定、革新經學課堂教學、編撰新型經學教材等方面,進行了不懈努力。皮錫瑞曾向湖南提學使吳慶坻當面陳訴“各學堂不用經學之弊”(《皮錫瑞日記》,中華書局2020年版,第1653頁),又奏請朝廷嚴飭各處學堂遍設經學科目,或增加課時,“凡學堂不教經學者,即行封禁;不重經學者,罪其監督、堂長,則聖教益以昌明,而所學皆歸純正矣”(《皮錫瑞全集》第12冊,第557頁)。他以修身、倫理本為儒經所常言,而新的課程體系卻是三者分立,滋生各種流弊,因此主張將修身、倫理兩科併入經學,“則聖經定於一尊,而歧途不至別出矣”(同前,第558頁)。最值得稱道的是,皮錫瑞身體力行,用心改進經學教學,捨棄煩瑣破碎的治經舊法,只向學生講解經書中的大義要旨,並以史事、時局作比證,做到深入淺出:“其教授時復不作艱深之論,以苦人索解,於闡明微言大義外,必取與現今時代情勢相合與事之關乎政教者,反覆發揮,以求通經可以致用”(皮嘉祐《師伏堂春秋講義跋》)。皮錫瑞革新經學教育的成果,還直接呈現在三部經學講義中,即思賢書局刊刻的《經學歷史》《經學通論》,以及在他逝世後由家人印行的《師伏堂春秋講義》。其中宏觀上借史立論的《經學歷史》和具體指點治經門徑的《經學通論》,上下千古,獨具裁斷,不僅對中國數千年經學加以全面總結,更為新體制下的經學教育提供了理想教材。
皮錫瑞在《經學歷史》開篇指出:“凡學不考其源流,不能通古今之變;不別其得失,無以獲從入之途。”他分十個時代論述歷代經學的嬗變,析其源流,辨其得失,尤其針對“自新學出而薄視舊學,遂有燒經之說”,特意強調“立學必先尊經”,同時力言經學簡明、有用、易學,表達了在新教育中延續傳統文化慧命的強烈信念。意猶未盡的皮錫瑞,接著編撰《經學提綱》,稍後定名為《經學通論》。他在序中明言:“前編《經學歷史》以授生徒,猶恐語焉不詳,學者未能窺治經之門徑,更纂《經學通論》,以備參考。”對於中國二千多年經學的源流、正變,《經學歷史》作了一次縱向的回顧,《經學通論》作為續編,則從經學的內層作了更詳盡的歸結。它依五經分卷,各卷再按議題設篇,“條舉群經之旨”,分別對《易》《書》《詩》《三禮》及《春秋》三傳的成書、流傳、義例、要旨,和歷代註解、考訂、詮釋的得失,以及今古文、漢宋學分立互爭的是非,作出簡要梳理和精闢論述,還特別指示治《易》、通《書》、讀《詩》、習《禮》、明《春秋》的方法,開列研讀各經的書目,“俾學者有從入之途,而無多歧之患”,為初學者提供治經的基本理念、學問根柢與關鍵知識,企望“使天下生徒盡通經術”。《經學通論》議題鮮明,取材豐富,分之為209篇經學專題論文,合之則不啻是一部經學小百科。周予同認為皮錫瑞“學術門徑很清楚,善於整理舊說”(《經學歷史序言》),用來評價他的經學教育成就,確是深得要領。
皮錫瑞晚年的經學教育,既凝聚了畢生研治群經的學術成果,吸取了南昌經訓書院的教學經驗,又因應著晚清的時代劇變,“思殫炳燭之明,用救燔經之禍”(《經學通論自序》),將紛繁複雜的古代經學加以清理、總結,含英咀華,化繁為簡,形成提綱挈領式的專題論述,開啟了近代經學通識教育的新路。民國以來湧現出一批經學通論或十三經概論性著述,紛紛效法或直接吸收皮錫瑞的《經學歷史》和《經學通論》。儘管有些經學教材後出轉勝,但迄今為止,皮錫瑞這兩部膾炙人口的經學講義,仍是引導人們進入中國經學殿堂的入門讀物,甚至被列作高校文科院系研究生的必讀書目。
《光明日報》( 2021年12月11日11版)
來源: 光明網-《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