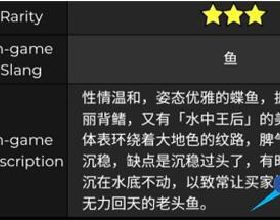西洲曲
南朝民歌
憶梅下西洲, 折梅寄江北。
單衫杏子紅, 雙鬢鴉雛色。
西洲在何處? 兩槳橋頭渡。
日暮伯勞飛, 風吹烏臼樹。
樹下即門前, 門中露翠鈿。
開門郎不至, 出門採紅蓮。
採蓮南塘秋, 蓮花過人頭。
低頭弄蓮子, 蓮子青如水。
置蓮懷袖中, 蓮心徹底紅。
憶郎郎不至, 仰首望飛鴻。
鴻飛滿西洲, 望郎上青樓。
樓高望不見, 盡日欄杆頭。
欄杆十二曲, 垂手明如玉。
捲簾天自高, 海水搖空綠。
海水夢悠悠, 君愁我亦愁。
南風知我意, 吹夢到西洲。
《西洲曲》是一首極為優美的南朝樂府民歌。但入們對這首詩的理解分歧很大有的認為全簡都是女子口吻,有的認為都是男子口吻。於是有的同志戲稱此篇是南朝文學中的一個“哥德巴赫猜想”。
此篇所以難懂,中心問題是詩中的人物關係不易搞清。其實,把它搞清也不太難,從結尾處“君愁我亦愁”來看,詩中寫到兩個人物“君”與“我”,均在互相思念,那麼,哪一個是女子,他們又各住在何處呢?可以從詩中找到答案。詩的中間部分寫道:“憶郎郎不至,仰首望飛鴻。鴻飛滿西洲,望郎上青樓。”不難看出,憶郎、望郎的女子住在西洲。“西洲在何處?兩槳橋頭渡。”這兩句之前,寫單衫和雙鬢,這之後寫伯勞和鳥日樹,也可知西洲是女子住處。詩的最後二句說:“南風知我意,吹夢到西洲?“南風”就是由南向北吹的風,“夢”即“魂縈夢繞”之“夢”,即思緒、憶念。“我”看“南風知我意”,把我的思念吹到西洲去,即吹到住在西洲的那個女子身邊去,則“我”就是男子,住在江南;“君”即女子,住在西洲,地點在江北。
這樣解詩,確有膠柱鼓瑟之嫌,但人們對這首詩分歧很大,理解不易,這幾處關鍵的詩句再不抓住,種種理解和欣賞豈不都成了想當然!
搞清了詩中的人物關係和人物的居住地之後,我們就會發現此詩的構思十分巧妙。此詩從總體上看,是表現男子對女子的思念,但是,卻從對方寫來:不說“我”日夜思念那個姑娘,卻寫在“我”的想象中,那個姑娘終年在想念著“我”。唐代詩人杜甫的《月夜》就深得此詩構思的精神。
詩的開頭兩句應是男子的自述。他想起梅(可能是女子的姓或名)到西洲去了,現在春回大地,梅花綻開,於是折一枝梅寄到江北去,贈給情人,聊表思念之情。從第三句起,詩由第一人稱轉為第三人稱,展開想象中的女子思念情郎的活動。先寫春末時節,她的衣服和鬢髮的顏色,次說她居住的地方在西洲,離橋頭渡不遠。夏天到了,風吹烏臼樹響,引起她的錯覺,以為有人來到門前。她的家門就在樹下,她悄悄開門窺探,情郎並未到來。於是她惆悵地出門下塘採蓮花。漸漸地秋天來了,蓮花結成了蓮蓬,她邊採蓮蓬,邊憶情郎,情意綿綿。情郎始終不來,她仰首望飛鴻,盼望鴻雁帶來他的書信,但鴻雁並沒捎信來。於是她登樓遠看,一天天地在樓頭欄杆邊痴望,卻望不見情郎。為了看得清楚一些,就捲起楹簾,只見碧天自高,江水空自搖動綠波。真是望穿秋水,悵惘不已……。男子想象至此,情不自禁地從心底深情地呼喚:“海水夢悠悠(海水悠悠如你思念之悠悠),君愁我亦愁。南風知我意,吹夢(我的思念)到西洲。”這樣的構思恰能表現男女雙方兩地相思,心心相印,增加詩篇的感情濃度。
《西洲曲》的第二個藝術特色是採用了四季相思的抒情方法,有很濃厚的民歌風味。有的同志說,此詩時間跨度是三年:這個女子到西洲去是第一年,她從春到秋(冬路去未寫)思念情郎是第二年,南風再吹是第三年。這當然是對的。但是作為詩篇主體的女子的相思是一年中的事。詩篇按照一年的季節變化寫女子的相思,不同季節的景物描寫,有助於抒發纏綿深長的思念,顯得十分優美動人。有些寫景的句子,如“採蓮南塘秋,蓮花過人頭”,至今膾炙人口。諧音雙關的運用,如以“蓮”關“憐”,也是民歌的本色。
此詩另一個成功之處是連珠格(也叫頂針格)修辭手法的運用,即透過許多詩句結尾與起首字詞的重複使用,使詩句後緊緊銜接。如“風吹烏臼樹。樹下即門前,門中露翠鈿。”“仰首望飛鴻。鴻飛滿西洲,望郎上青樓。樓高望不見。”這樣,詩句就前後銜接,蟬聯而下,十分流暢。再加上每四句一換韻,造成一種音韻流轉、聲情搖曳的音韻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