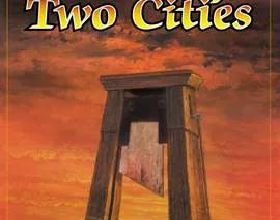中國歷史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美的文言文,就像燦爛的繁星,閃耀在這五千多年的浩瀚星河裡。學習文言文是與歷史對話,是與智者交流,是對古代文化的繼承。
但是,有些學生一聽到“之乎者也”就犯困,甚至感到非常痛苦,他們繼而想到這樣一個問題:古說話是不是滿嘴“之乎者也”?殊不知,這實在是一個天大的誤會。
先來釐清四個概念:口語、書面語、文言文、白話文。書面語是在口語的基礎上產生的,文言文和白話文都屬於書面語。但前者建立在先秦漢語口語的基礎上,後者則建立在近代漢語口語的基礎上。
大約在先秦時期,文言文還是和當時的口語一致的,諸如《論語》、《孟子》這類,可以說就是當時口語的實錄。“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當時說話,也就是這麼個腔調。
雖然文言文和口語都在發展,但前者遠遠跟不上後者的速度,距離越拉越大。可惜,由於反映當時口語的文獻遠沒有文言文獻那麼豐富。中古時期漢語口語的研究因而尚有很大空間。
這種情況在唐朝出現變化,很大程度上歸功於佛教的大發展。由於潛在教徒大多是文化水平不太高的老百姓,大量翻譯的佛經和佛教故事便多使用當時的口語。這,成為早期白話的重要來源。
到了宋朝,文言文和口語已經完全脫節。
到了元代,蒙古人征服中原後,由於統治階層的成員多不通漢語,語言文字自然以蒙古文為先。
然而,直接用蒙古語治理廣闊的漢地,難免困難重重,這就需要數量龐大的翻譯人員。在漢語文獻裡,這些人被稱為“舌人”或“通事”,蒙古語稱“怯裡馬赤”。用當代中國人熟悉的詞來說,就是“翻譯官”。
忽必烈初入中原,即在宣政院、宣徽院、中政院、儲政院等機構設定怯裡馬赤,此後朝廷中樞機構、地方機關都設有通事。
這些通事往往漢語素養有限,受教育水平也不太高,難以深入學習文言文,只能使用簡明易懂的早期白話。這樣就形成了“白話講章”。整個蒙元時期,聖旨和高階公文往往都是用漢語白話文傳達。
《長春真人西遊記》中載有一篇成吉思汗給丘處機的詔書,甚至有“丘神仙……你起身心裡好麼?……我不曾忘了你”之句。
到了明代,朱元璋登基稱帝之後,釋出了許多個性十足、前代帝王聖旨中聞所未聞的“白話聖旨”。
比如,洪武年間,倭寇侵擾沿海群島,地方官上報此事,朱元璋釋出這樣一道聖旨:“奉天承運,皇帝詔曰,告訴百姓們,準備好刀子,這幫傢伙來了,殺了再說。”
此則聖旨語言直白,簡潔明快,令人頗有痛快淋漓之感,其威儀殺氣盡在話語之間。
書面語和口語的雙軌發展,文言文和白話文對立的局面,直到五四新文化運動才終結。
新文化運動的號角吹響,終於讓白話文代替文言文,成為漢民族的共同書面語。
梳理從先秦到“五四”,書面語和口語、文言和白話的發展,我們不難發現,最早在唐宋時,古人的口語就和我們現在的差不多了。
原因大致有二:一是白話文出現的時間晚,且被傳統社會認為難登大雅之堂;二是古文教育重文言——文言文和口語脫節太嚴重,不論是散文還是駢文,如果不經過專門的學習,基本無法誦讀理解。
總而言之,最晚在唐代的時候,人們的日常交流已不再是“之乎者也矣焉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