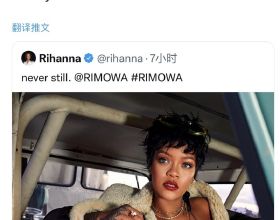作者:Sebastian Biba,法蘭克福大學中國/東亞區域研究政治學教授、研究員
引 言
鑑於德國在歐盟舉足輕重的地位以及歐盟的國際影響力,在日益深化的中美競爭中,德國對美國來說是一個重要的議題。儘管德國在中美競爭中總是更傾向於後者,但其對於是否全面接受美國的反華態度仍然猶豫不決。正如即將離任的默克爾在達沃斯論壇上的講話:“我非常希望避免中美兩個陣營的建立。如果我們要麼圍繞美國,要麼圍繞中國,那麼這對很多社會來說是不公平的。”
日益嚴重的國際形勢迫使德國進行明智和理性的分析。為什麼德國不願與美國站在一起對抗中國?德國當前(或替代)行為的可能性和陷阱是什麼?為了回答這些問題,本文采用了美國學者洛厄爾•迪特默(Lowell Dittmer)在上世紀80年代初提出的“戰略三角法”(strategic triangle approach, STA)。STA為我們的分析提供了明確的三角邏輯,而其他大多數國際關係理論都聚焦於雙邊關係。更重要的是,STA的分析強調參與者的國家利益(主要根據國家安全和福利進行定義)。
本文的結構如下:作者首先介紹了STA的主要理論主張,強調了“羅曼蒂克”結構中的驅軸國傢俱有的矛盾性,即優勢和高風險並存。此後,作者描繪了從冷戰時代到現在的中美德戰略三角的發展,並說明了德國最近是如何被置於驅軸地位的。自此,德國一直尋求維持這一角色,因為其與中美的友好關係有利於自己的安全和經濟利益。最後,本文以STA為基礎,對德國當前的行為和可選擇的道路進行了討論,展現了德國正面臨著艱難決定的境況。
戰略三角法(STA)作為理論框架
迪特默率先闡述了STA,為之前的研究提供了理論和分析的基礎,但他並沒有創造“戰略三角”這個術語。在此基礎上,臺灣學者吳玉山對STA作出了重要的理論貢獻。
戰略三角理論具有一些不言自明的原則。首先, STA的運作是基於以下假設,即戰略三角中的三個雙邊關係要麼是積極的(以“友好”狀態為特徵),要麼是消極的(以“敵對”狀態為特徵)。戰略三角結構具有四種模式:1.“三人共處型”(ménage à trois):由三種友好關係組成,三方互為朋友;2.“羅曼蒂克型”(romantic):由兩種友好的關係和一種敵對的關係組成,其中驅軸國與兩個側翼國保持著積極關係,兩翼彼此之間有消極的關係;3.“穩定婚姻型”(marriage):由一種積極關係和兩種消極關係組成,兩個夥伴國家之間保持積極關係,而兩者均對被排斥者持有敵對關係;4.“單位否決型”(unit veto):包括三種消極關係,三方互為敵人(見圖1)。
圖1
值得注意的是,國家的不同位置可以根據他們的“期許”進行排名。一方面,一個參與國與其他參與國保持友好關係比敵對關係更可取;另一方面,另外兩個參與國之間的敵對關係比他們之間的友好關係更符合期許(因為害怕兩者合作串通反對自己)。結果表明,六種可能角色之間的偏好排序如下:1.驅軸(pivot);2.朋友(friend);3.夥伴(partner);4.側翼(wing);(5)敵人(foe);(6)被排斥者(outcast)(見表1)。
表1
換句話說,在“羅曼蒂克”關係中扮演核心角色可以說是STA中最有利的位置,因為這為參與者提供了最大程度的積極關係,同時還會導致剩下的兩個參與者互相爭鬥。
然而,驅軸位置極具挑戰性並很難維持,因為戰略三角中的雙邊格局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動態的。處於不利位置的國家通常會設法轉向較有利的位置,從而提高他們的地位;與此同時,處於有利地位的國家試圖防止其作用下降。因此,一方面,驅軸國家位置意味著此國家可以(試圖)在其他兩國之間的戰鬥中從雙方獲得讓步。但讓步並非絕對,因為對於一個軟弱的驅軸國家,兩翼採用的方式可能不是說服和讓步,而是欺凌和脅迫。另一方面,驅軸國也會受到兩個側翼國的交叉壓力。因為側翼國會爭取驅軸國的青睞,積極尋求將“羅曼蒂克”關係轉變為“穩定婚姻”關係,將自己的角色升級。
總而言之,在戰略三角中扮演驅軸角色意味著在雙方之間保持微妙的平衡。這需要較高的靈活性並保持對側翼國的吸引力。
過去與現在的中美德戰略三角
嚴格地說,中國、美國和德國之間戰略三角的出現相對較晚。在冷戰時期和冷戰後初期,中德之間的雙邊關係無足輕重,因此可謂並不存在中美德戰略三角。隨著中德雙邊關係的發展,特別是在顯著增加的經濟交流和由此產生的相互依存關係的推動下,三國之間的戰略三角關係在2010年左右逐漸形成。
1. 德國成為驅軸的漫長而被動的道路
回顧過去的中、美、德三角關係,一個很重要的起點是美國與前西德的雙邊關係。兩國在1955年波恩加入北約(NATO)後成為盟友,西德對美國產生極大依賴,這種依賴也體現在對外關係上。冷戰期間美國、中國和西德之間的戰略三角,最終都是由當中美之間的搖擺狀態所決定的。在中美蘇三角關係的背景下,中美關係一直是消極的,直到20世紀70年代初,中美關係出現緩和,並逐漸呈現積極狀態。因此可以說,在冷戰時期的前半段,中美德(西德)戰略三角呈現出美德的“穩定婚姻”模式,而中國作為被排斥者。在冷戰的後半段,三方變成了STA所稱的“朋友”,中美德戰略三角呈現出“三人共處”的模式。(見圖2)
圖2
然而,隨著冷戰的結束,中美德三角關係中偶爾出現的磕磕碰碰變得更加明顯,於是“三人共處”關係變得不穩定。總的來說,美國與統一後的德國仍然是三對關係中最積極和最穩定的,雙方持續是非常密切的軍事和經濟夥伴。但這一時期,美德也出現了明顯的分歧。例如德國在2003年拒絕加入美國對伊拉克的干預,這在後來被認為是美德相互理解和利益協調減弱的“轉折點”。又如美德在利比亞問題上的分歧、2013年“稜鏡門”都加速了美德關係的衰弱。
對於中美關係來說,1991年蘇聯解體,中美建交最重要的基礎和共同利益消失,雙方關係岌岌可危。人權問題也成為中西方爭議的焦點。然而,在上世紀90年代和本世紀頭十年,中國開放經濟的強大吸引力和巨大潛力最終在中美和中德關係中佔據了上風,中國在2001年加入世貿組織(WTO)也證明了這一點。
對於中德關係來說,德國對華政策優先考慮開放市場、為德國公司建立公平市場環境這一首要原則,而中國期望獲得一流的德國技術。其結果是中德之間蓬勃發展的經濟關係,其主要特徵是“技術換市場”,在2010年代初,兩國經濟接近於經濟共生。雙方還建立了80多個對話機制,其中許多是政府高層對話。
中美關係不得不面對更大的挑戰。儘管兩國仍然能夠在一些共同關心的問題上進行合作,例如反恐和氣候合作,但中美兩國之間的戰略不信任隨著北約轟炸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南海問題等問題爆發而顯現。一方面,雙方在經濟上更加相互依存,另一方面,中國迅速增加的軍費開支和固有的政治體制引起了美國越來越多的關注。奧巴馬政府的“重返亞洲/再平衡”政策、《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簡稱TPP),均旨在對抗中國崛起。
2017年,特朗普的上臺加劇了已經在醞釀的負面三角關係。他臭名昭著的“美國優先”(America First)策略將中國和德國列為其最突出的兩個目標。在特朗普任期內,美德關係達到了“戰後最低點”,原因包括德國的鉅額貿易順差、貧乏的國防開支、對俄看似密切的關係,以及兩國在伊朗核協議和空襲敘利亞問題上的分歧。在中國問題上,特朗普政府不僅將中國拖入一場公開的、曠日持久的“貿易戰”;還在新冠疫情上“汙名化”中國,且在2017年12月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中直接將中國描述為一個“修正主義”大國,其目標是塑造一個“與美國價值觀和利益相悖的世界”。
因此,自冷戰結束以來,中美德戰略三角關係逐漸惡化,由“三人共處”關係轉為脆弱的“羅曼蒂克”關係,以德國為驅軸,中美為兩翼。(見圖3)即使美德關係也因為特朗普的政策而出現波動,然而總體上這種羅曼蒂克關係還是可以成立的。
圖3
值得注意的是,中美德之間相對較晚出現的“羅曼蒂克”關係、德國處於驅軸國家地位,顯然不是德國有意識的積極戰略和政治運作的結果,而主要是中美關係惡化的結果。儘管德國在這一發展過程中沒有扮演任何因果角色,但它一直顯示出保持驅軸地位的意願。
2. 德國維持驅軸地位的積極作為
儘管特朗普在2021年1月被拜登取代,但中美關係依然消極。在這種日益困難的情況下,德國仍然尋求與華盛頓和北京保持長期以來的積極關係。為了實現這一目標,德國試圖在軍事領域討好美國,同時尋求在經濟方面安撫中國。
在此背景下,德國最近非常熱衷於向華盛頓發出訊號:它不僅意識到自己對美國安全保障的依賴,而且願意透過北約自己做出更大的安全和軍事努力,以配得上這些保障。這一訊號表明,德國在安全政策上承擔了更多責任,近年來國防預算顯著增加(僅2019年就增加10%)。此外,德國還宣佈向東亞(並透過南海)派遣一艘海軍艦艇。該計劃自2021年8月開始實施,並立即受到美國政府的歡迎。
一方面,德國政府和強大的德國工業聯合會(BDI)近年來越來越關注與中國的經濟關係。這導致德國人認為,這個亞洲國家不再僅僅是一個經濟“夥伴”,而是一個經濟“競爭對手”。另一方面,2020年中國連續五年成為德國最重要的貿易伙伴。德國企業力圖在中國市場佔有一席之地。在此背景下,德國強調,無論是在經濟上還是在外交上與中國脫鉤都不是德國的選擇。
評估德國在中美德三角關係中的行為
從STA的邏輯來看,德國目前的行為是可以理解的,考慮到德國的安全和福利已經從與中美的積極雙邊關係中獲益良多,當時的“三人共處”模式非常友好,德國仍然不遺餘力地維持這兩種有利的關係。更重要的是,根據STA理論,在新的“羅曼蒂克”格局下,德國與美國和中國保持積極關係,實際上意味著德國的角色從朋友提升到了驅軸。然而,該角色也帶來了矛盾和不穩定性。因此,有必要分析一下德國作為驅軸國家迄今為止的表現,以及德國當前的代替選擇。
1. 作為驅軸的挑戰:在讓步和壓力之間行走
一方面,處於驅軸的地位可能會創造機會,讓其他兩個側翼國做出讓步,因為兩翼各自尋求提升其在三角關係中的作用,他們試圖將“羅曼蒂克”轉變成“穩定婚姻”關係,以將自己的角色從側翼國提升至夥伴國,或者努力防止出現相反的結果。2020年12月《中歐全面投資協定》(CAI)的簽署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
儘管德國在與美國和中國保持積極關係方面有著持久的利益,但我們應該記住,德國與美國的關係一直比與中國的關係更密切或更積極。因此,中國必須對可能的美德”穩定婚姻“關係趨勢特別敏感,從而避免在戰略三角中變成最不利的被排斥者。
與此同時,CAI的談判已經進行了7年,當時的德國歐盟理事會主席,包括默克爾本人,都渴望在預設的年底最後期限前達成協議。因此,歐盟抓住了拜登團隊的過渡時期,使中國在CAI談判中做出了讓步。儘管這項協議受到了嚴厲的批評,但一些專家認為它是“成功的”。顯然,如果德國不是中美德三角關係中的驅軸,這一結果幾乎不可能實現。
然而,另一方面,讓步也有可能帶來負面效果。側翼國也可能對驅軸國施加壓力,甚至是脅迫,原因仍然是為了促進“穩定婚姻”關係或是為了阻止它的出現。相對較弱的驅軸(如德國),特別容易受到來自兩翼的壓力,因為它往往更依賴於側翼國,因此必須小心管理各方不同的期望。我們可以舉5G的例子。特朗普政府強烈反對美國盟友在5G網路中使用中國華為的技術,否則就可能失去獲取美國情報的機會。
然而,如果德國方面真的將華為排除在其國內市場之外,中國將採取報復行動,可能會以安全為由將德國汽車擋在中國市場門外。德國汽車製造商越來越依賴中國市場。2019年,德國最大的汽車製造商大眾汽車(Volkswager) 有40%的汽車在中國銷售。面對來自兩翼的巨大壓力,德國一直在走一條微妙的路線。具體來說,與其他歐洲國家不同的是,德國沒有表現出禁止任何供應商使用華為5G網路的意願,轉而尋求透過一部新的IT安全法來提高市場準入門檻。
總而言之,德國作為驅軸國家的現實經驗反映了STA理論考慮所確定的矛盾心理。那麼其他選擇呢?
2. 驅軸的代替方案:作為朋友或者夥伴的利弊
德國首選的替代方案很可能是迴歸“三人共處”關係。儘管從嚴格的理論角度來看,這種格局的重新出現將意味著德國從當前的驅軸地位下降,但可以假設,德國仍然會欣然接受。一個原因是,在這種模式下,德國作為朋友的表現格外出色。另一個原因是,在德國看來,兩翼為重新轉向歐洲而展開的競爭所帶來的好處,很可能會被巨大的交叉壓力所抵消。德國作為這三個國家中最弱的國家,一直在承受且肯定會越來越多地承受交叉壓力。
然而,“三人共處”關係的唯一問題是,這種狀態極難返回。從特朗普到拜登的過渡似乎證明了一些學者的觀點是正確的,中美競爭不是制度的問題,而是國際關係結構的問題。更重要的是,在這種情況下,德國(以及整個歐盟)沒有很好的機會來調解這場迫在眉睫的超級大國衝突。
第二種選擇是德國(重新)與美國“聯姻”。拜登領導下的美德關係正處於上升階段,而中德關係正變得越來越緊張。從STA的角度來看,從一個“羅曼蒂克”中的驅軸國到一個“穩定婚姻”結構中的夥伴國,會比到“三人共處”結構中朋友的角色退化更大。但是,“穩定婚姻”模式通常比“羅曼蒂克”模式穩定得多,因為對於被排斥的一方來說,要改變三角關係的格局通常要困難得多。
因此,美國和中國對德國的相互壓力將大大減少,並在某種程度上使德國的外交政策更加直截了當,從而可能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補償其角色的退化。
即便如此,這種角色的退化也會給德國帶來其他一些嚴重不利因素。首先,美德“聯姻”將把中國變成一個完全的對手。儘管中德關係近年來變得不那麼積極,消極的中德關係與德國國家利益不一致。這不僅是出於經濟原因,而且也由於需要共同解決全球問題,並就非洲的穩定未來進行合作。此外,即使在拜登的領導下,美德“聯姻”也將由華盛頓主導。正如默克爾一再指出的那樣,這並不總是符合德國的利益。
另一個重大風險涉及特朗普主義幽靈的重現。雖然拜登確實是一個“跨大西洋主義者”,高度重視美國與歐洲和德國的夥伴關係,但德國不能確定,四年後特朗普或其他致力於推行其政策的人不會再次當選。從STA的角度來看,特朗普的第二次總統任期很可能意味著拜登領導下的美德短暫“穩定婚姻”的突然結束,並將此格局轉變為“單位否決”。對德國來說,這將導致其角色急劇下降,因為德國將從驅軸(第1位)變成敵人(第5位)。這將使歐洲國家在安全和福利方面處於極其脆弱的地位。
總而言之,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德國作為驅軸國家的備選項要麼不現實,要麼與驅軸國家方案一樣充滿矛盾。
總結
毫無疑問,美國和中國之間日益激烈的大國競爭讓德國進退兩難。本文采用了戰略三角方法,對德國在這個三方關係中的行為進行了理論上的評估。分析表明,德國在默克爾領導下的做法,即長期以來與中美保持整體友好關係的利益,大體上符合STA的理論主張。換句話說,積極關係比消極關係更有利,因為前者能產生更多與國家核心利益(如國家安全和經濟福利)相關的利益。
然而最近,中美德之間的三角關係從“三人共處”轉變為“羅曼蒂克”,德國現在處於兩翼之間的驅軸位置。一方面,德國在三角關係中的角色已經上升到最高,可能會迫使美國和中國做出讓步,以防德國與對方勾結。但另一方面,鑑於德國是三角關係中最弱的參與者,德國很容易受到兩翼的交叉壓力,因為兩翼都尋求提升自己在三角關係中的地位。此外,未來中美對抗可能加劇,可能使德國面臨來自中美越來越大的交叉壓力。
儘管如此,替代方案也會帶來問題。在德國能力範圍內,回到曾對德國非常有利的“三人共處”模式是很難實現的。鑑於拜登的跨大西洋行動和中國日益增長的實力,美德形成排斥中國的“穩定婚姻”關係的想法正在升溫。但這樣的“聯姻”也會有嚴重缺陷,德國對華政策將會服從於美國的偏好,而與本國偏好不一致。此外,特朗普主義幽靈重返白宮對德國也具有巨大的負面影響。
就目前而言,德國在後默克爾時代對美國和中國的定位懸而未決。如果德國想要堅持它的驅軸國家策略,就需要儘可能減少中美兩國產生的交叉壓力和脅迫。因此,無論是在經濟、技術、軍事還是其他方面,德國需要與歐洲夥伴和其他感興趣的國家合作,以減少對這兩個超級大國的依賴。
最後,本文應用STA理論解釋了為什麼美國的盟友和合作夥伴,在日益捲入中美競爭的情況下,不願選邊站。隨著中美競爭的繼續展開,美國“重返亞洲”戰略能否持續下去,只有時間才能證明。
原文標題《德國如何處理中美德三角的微妙關係?》,文章來自公眾號“國政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