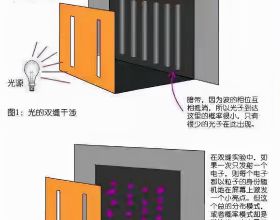“你是那天晚上那個醫生嗎?”站在病人身後的家屬突然冒出了這麼一句話來。
我看了看他,有一些遲疑,還沒有從這句話中回過神來:“哪天晚上?”
“就是那天晚上,你把我爸爸救回來的,就是他!”家屬說著話又指了指坐在我面前的病人。
剎那之間,我想起了那晚的故事,也終於明白自己為何會對眼前這個病人的名字還有著一絲印象。
“哦,對,對,你不提醒的話,我沒有記起來。”我有些不好意思自己竟然沒有察覺到坐在我面前的是一位老病人。
病人也從家屬的話中回過神來,他突然伸手握住了我的手:“謝謝你啊,真虧了你。”
這下子我更加不好意思了,內心也有些激動了。我從沒有想到這位病人會恢復的如此之好,也沒有想到過半年後還能夠再次遇見他。
“坐下來,坐下來”我又請病人坐了下來“現在恢復的還不錯吧?”
“還可以,還可以,多虧了你。”即使戴著口罩,我也能夠清楚地看見病人臉上的笑容。
半年前,深夜。
急診室裡來了一位六十多歲的男性病人,因為上腹痛伴嘔吐三個小時來到醫院。
病人剛進入急診室就向我要求輸液,他說:“我很多年前就有胃病了,今天貪涼又犯病了,給我掛點消炎藥。”
我沒有直接拒絕他的要求,只是按照自己的工作思路有條不紊的工作著。
生活中有很多類似的病人,他們一開始就會提出自己的要求。面對這樣的病人,我一般不會上來就拒絕,更加不會直接反駁,而是嘗試著將病人帶入自己的工作思路和節奏中去。
“有什麼胃病,做過胃鏡嗎?”我一邊觸診著病人的腹部一邊詢問著。
“記不住了,快十年了吧。”病人皺著眉頭勉強回答道。
“這不一定是胃病,其它問題也會出現這種情況的。”體格檢查完畢後我心中有了自己的打算,因為病人不僅有著劍突下隱痛,更有著心前區不適。
我看著趴在桌上的病人,解釋道:“有時候心臟病看起來就像胃病,這個年紀是高危人群,一定要先排除掉心臟病,比如心肌梗死這些,才能考慮胃病。”
“不掛消炎水了?”病人抬起頭問道。
“掛,但先要做心電圖、心肌酶這些檢查,沒問題的我就給你掛,不然就耽誤你了。”
就在我推來心電圖機準備在急診室內為患者完善床邊心電圖時,家屬開口說話了。
說完的是病人的兒子,一個看上去三十多歲,身上還散發著酒精味的男子。
病人的兒子說:“我看你這個醫生就是胡扯,看個胃病還要做這檢查做那檢查,真當老百姓的錢不是錢了?”
這句話讓我愣住原地了,也讓我至少花了五秒鐘的時間從震驚到羞愧,從憤怒到理智。
“我剛才解釋的話,你沒有聽明白?”我盯著這位對我滿是鄙夷的家屬問。
他沒有理我,只是帶著嘲諷扭過頭去了。
“胃病會這樣子,心肌梗死也會這樣子。他不僅胃痛,而且胸悶。你能說他一定就是胃病,沒有其他問題?這個年紀還是小心為好。你沒有遇見過,我遇見過太多了,有時候急性心肌梗死的首發症狀就是肚子痛!”雖然我知道家屬聽不進去,但我還是又解釋了一遍。
“你們就是想搞錢,我從來沒聽過看胃病做心電圖這個道理。”家屬還是要和我爭執著。
面對酒後有些激動的家屬,我選擇了沉默。一是因為我不願激化矛盾,尤其是這種酒後容易衝動的人。二是因為我要完成對病人心電圖的檢查,也只能委曲求全了。
我沒有繼續搭理家屬,家屬也沒有繼續說話,只有躺在偵查床上的病人在呻吟著。
心電圖果然有著問題,這位上腹痛伴嘔吐三小時的病人高度考慮急性下壁心肌梗死,Ⅱ Ⅲ AVF導聯均已抬高。
“還真是要考慮心肌梗死,心電圖有問題,和我去搶救室吧,要進一步處理。”我將病人扶了起來。
”心肌梗死就是了,你嚇唬我爸做什麼?“家屬有些更加不高興了。
而家屬的這句話也讓我更加震驚了:“什麼嚇唬你爸了,心電圖結果放在這裡呢!”
“你有什麼話不能和我說,非要當著我爸的面說,他能經受得了嗎?”很明顯家屬還沒有抓住重點。
“你不要說了,看病要緊,他是成年人,意識清楚,有權知道自己的病情。”我和護工師傅第一時間將病人推進了急診搶救室,留下心有不甘的家屬在搶救室門外。
此時,從病人進入醫院已經過去了十分鐘時間。
病人進入搶救室後,按照胸痛中心的流程很快便得到了系統快速的救治。
在護士為他開放靜脈通路的時候,他卻向我伸出了手。
我以為他尚以為他難受不適,於是便詢問道:“怎麼了?”
沒想到病人卻這樣說:“我兒子喝了酒,就這樣,你不要生氣。”
這句話同樣讓我震驚:“沒關係,能理解,這樣的情況天天見。”
雖然我口裡打著哈哈,但心中不免還是有一些不愉快。
心臟科醫生會診後,準備將病人送入介入導管室手術治療。
原本只需要病人送入手術室我的工作就可以告一段落了,但意外還是出現了:室顫!
只見病人突然雙眼上翻,肢體抽搐了幾下,心電監護上便是一串室顫波。
按壓、除顫、腎上腺素......
大約五分鐘後,病人漸漸恢復了自主心律。
搶救室門外,凌晨一點。
我拿著心電圖向家屬們交代著病情:“雖然現在恢復了心跳,但還沒有度過危險期,隨時會再次出現心跳呼吸驟停的,你們還是要做好心理準備。”對於這樣急性心肌梗死心肺復甦術後的病人來說,極有可能在下一秒便再次出現病情惡化。
雖然其他家屬也已經趕到了醫院,但能夠簽字的卻只有這位散發著酒精味的兒子。
面對著病危通知單,他遲遲不肯下筆,漲紅了臉緊張地問我:“醫生,風險大嗎?”
“都已經這樣了,風險能不大嗎?用難聽的話說,他已經是半條命的人了,剛才已經去鬼門關轉了一圈了。這個病就是這樣,你以前肯定也聽說過。”我必須要用最通俗的話讓家屬們在短時間內明白病人真實的病情。
但看著這位孝順的兒子,我卻又有些不忍了,安慰道:“放心吧,我們會盡力的,你只要配合我們就可以了。”
他沒有再說話,簽下了字。
後來,病人被送離了急診搶救室,進入了下一站治療。
而我,在那晚之後,也漸漸地將病人忘記了。
沒有想到半年後,這對父子竟然又會在深夜裡和我相遇。
只是這一次,病人只是有些咽痛咳嗽,而並非如把半年前那樣命懸一線了。
家屬認出是我後,尷尬地說:“醫生,你說得很對。我當時以為就是胃病,要是早點聽你的就好了。”
我抬起頭看了看他,笑著說:“你沒見過,我在急診見過很多。不是所有心肌梗死一上來就是胸痛的。”
開了藥後,這對父子再次向我道謝後便離開了。
雖然這只是急診日常工作中尋常的一幕,但最少讓我在那一晚充滿了自豪和感動。
談不上是我拯救了病人,但我最起碼可以無愧於病人的感謝,因為我曾為他努力過。
和將病人從鬼門關上拉回來相比,還有一點也更為重要,那就是病人的家屬從此之後將會對不典型症狀的急性心肌梗死體會深刻,甚至對一線醫務人員也會更多一點理解。
有人曾問過我:工作以來有哪些特別難忘的病人?
這個問題我無法回答,因為答案有太多太多了。
也有人曾經問我:是什麼樣的力量支撐你在醫學這條路上走下去?
我想沒有什麼特別的原因,只是因為自己還能夠去幫助別人,只是因為自己對那一絲絲滿足感、自豪感上癮。
醫師節到了,多巴胺想再說一句:願天下無病,人間無痛!願我們彼此多一份理解!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