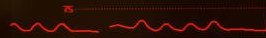快下班的時候,我拿到了明天的手術排班。
我的名字前面,寫著兩臺婦科手術的全身麻醉。
我換上白大褂去病房看看患者,評估一下麻醉風險再讓患者簽字。
這是每天的例行動作。
“高血壓、糖尿病有沒有?”、“有沒有過胸悶、心絞痛?”、“有沒有哮喘或者呼吸方面的毛病?”、“之前做過手術嗎?”、“有沒有藥物過敏”、“…………”
這是術前訪視的固定臺詞。問清楚了,讓我在手術前有個準備,知道這個患者麻醉的風險高不高。
“狀態還不錯,麻醉風險不大,就是睡一覺。晚上八點以後不要吃東西了,十點以後不要喝水,好好睡一覺。”這也是我結束訪視的固定臺詞,然後下班。
我再次見到患者是第二天早上,我把麻醉藥準備好檢查麻醉機的時候,患者被推了進來。
她的臉色是白的,護士給她打靜脈針的時候手臂還在微微的抖。
“別緊張,放輕鬆,沒關係的,就是睡一覺,我昨天和你說過的。”我想辦法讓她放鬆,同時也看到監護儀上她的血壓衝到了150/80。
我沒有再多說話,做著自己的準備工作。我知道,這個時候話越多,她越緊張。還不如讓她盯著手術室的無影燈,過一會,她的心率也就下來了。
這一點,教科書倒是從沒教過。
師傅從隔壁手術室走過來,他已經把隔壁房間的患者麻醉好了,現在過來到這個房間進行麻醉誘導。
麻醉誘導,就是用麻醉藥把一個清醒的患者誘導進入到麻醉的狀態。
誘導這個詞很妙,它既說明了進入麻醉狀態是外界藥物起作用的結果,但也體現出整個過程需要根據患者機體各種被“誘導”出來的反應,然後依次處理。
“放輕鬆,深呼吸,我們開始麻醉了。”我把呼吸面罩蓋住患者的嘴巴和鼻子,把麻醉機的氧流量開大。
她看著我,過了一陣問:“吸這個就能睡著嗎?”
“這個是氧氣,不是麻醉藥,你做幾次深呼吸。”我說這句話的時候,師傅已經把準備的麻醉藥從她的靜脈針裡推進了血管。
咪達唑侖、丙泊酚、舒芬太尼、羅庫溴銨;除此之外,還有我習慣給患者加上的地塞米松、帕瑞昔布。
有的時候覺得,麻醉誘導不過是把麻醉藥按照劑量依次推進血管裡,後續麻醉維持的時候把麻醉藥透過注射泵持續泵入血管就好了。
先用咪達唑侖讓患者進入睡眠狀態,然後推入丙泊酚進行鎮靜。舒芬太尼是強效的鎮痛藥,最後羅庫溴銨讓患者全身的肌肉鬆弛,包括她的呼吸肌。而我習慣加的兩種藥物,一種防止患者術後噁心,一種緩解術後疼痛。
師傅把藥推完以後,我把面罩扣在患者面部。我看著呼吸皮球的起伏逐漸減弱——她的自主呼吸逐漸消失了。然後從患者口腔置入喉鏡,把氣管導管插入患者的氣管。
固定導管、連線呼吸機、調整呼吸機引數、開啟吸入麻醉藥閥門。我熟練近乎機械的完成這一系列動作。看著呼吸機的波形穩定——現在她已經進入了麻醉狀態。
“師傅,我去洗手做深靜脈穿刺了。”我轉身往手術室外走去。
就在我轉身的瞬間,監護儀報警,血壓降到80/61。
麻醉以後血壓下降是常見的情況,因為大多數的麻醉藥都會抑制心臟的收縮,舒張血管,造成血壓下降。我從靜脈針裡推進去一毫升的麻黃素,希望透過逆轉麻醉藥的心臟抑制來提升血壓。
3分鐘,監護儀還在報警。
血壓袖帶充盈、測量、得出血壓資料的時間最快需要一分鐘。但連續兩次的測量結果,血壓都在逐步往下掉——73/40、68/38。而相對應的,心率上升到了120次每分鐘。相對於血壓的下降,血壓袖帶的測量時間太慢。
“再給麻黃素10毫克,去氧腎上腺素10微克。”師傅說的時候,眼睛始終盯著監護儀。
我已經拿著針做動脈穿刺了。為了能夠實時的看到血壓變化,唯一的辦法是在動脈裡置管,連線感測器,實時顯示動脈血管裡的血壓變化。而這也意味著我必須要在已經波動微弱的橈動脈中進行準確穿刺並置管。
監護儀一直在報警,師傅不斷從靜脈針裡推入升血壓的藥物,護士在把手術床調整為頭低腳高位,這樣做是為了讓腿部的血液儘快迴流到心臟。
在這一篇嘈雜聲裡,我用食指和中指觸控患者的脈搏,儘量循著脈搏的跳動,穿刺,然後再小心的順著針把套管推入動脈。
但此時,我摸不到一點動脈搏動。
“患者有沒有藥物過敏?”師傅的語氣已經明顯緊張起來。
“問過了,沒有。”我仍然低著頭試著觸控搏動。
“推40毫克甲強龍,快點。”師傅讓剛聽到監護儀報警而近來幫忙的麻醉護士準備藥物。
甲強龍是一種激素,主要用來抑制機體的過敏和免疫反應。我知道,師傅是懷疑患者藥物過敏,這和我的想法一致。
沒有原因的麻醉誘導期低血壓,藥物過敏和心泵抑制是常見原因。前者讓全身的血管舒張,像一根根疲軟的水管,心臟泵出的血液無法順著壓力前進;後者則常見於心臟病的患者,可能由於突發的心肌梗死、心臟的冠狀動脈痙攣,造成心臟自身的供血中斷,心臟沒有了氧供,愈發沒有力氣跳動。
“這個患者沒有心臟方面的毛病,應該可以排除心臟的問題,考慮是過敏。”我心裡這樣想著。
激素推進血管的時候,我觸及到了微弱的波動,循著指腹的那一點輕微感覺,我把針刺了進去。針管頓時湧進鮮紅的動脈血。
成功了。
我將套管小心置入,然後連線感測器。第一個顯示在監護儀上的血壓是,70/45。
這點血壓,遠遠不夠。低血壓的時間這麼長,我擔心患者腦部和心臟的血供。沒有足夠的血壓,這兩個臟器萬一供不上血,後果不堪設想。
“要不把去甲接上吧,給一點看看反應。”我試探性的問師傅。
師傅看著監護儀點了點頭。
去甲腎上腺素可以強力收縮外周血管,就像讓疲軟的水管重新緊張起來,把壓力維持住。我把去甲連結到輸液泵,緩慢推注進血管。
70/45、78/44、82/50、90/66、92/64……
血壓逐漸上升,我稍微鬆了口氣。
但師傅還是皺著眉頭。
“師傅,要不先這樣泵著,等等看?可能甲強龍剛起效,過敏應該逐漸會好。”
我這麼說是因為我並沒有看到患者胸口有大片的紅疹,加上去甲很好的把血壓提了上來,估計不是很嚴重的過敏反應。
“我剛剛看到了幾個室早。”師傅沒有直接回復我的問題。
——室早,是心臟跳動不規律的體現,說明心臟本身出了問題。但我分明記得,前一天訪視的時候,她自己說從沒有出現過心絞痛和胸悶,心臟超聲和心電圖也沒有提示異常。
我木木的杵在師傅邊上,不知道該怎麼辦。
“你把心電監護調到模擬胸前導聯。”師傅還是皺著眉頭。
模擬胸前導聯是監測心臟是否缺血的監測方法,我知道師傅懷疑患者低血壓是由於心臟有缺血。
我把監護儀的心電調整為模擬胸前導聯。
緊接著,就是一聲警報。
“ST-T改變”,監護儀顯示出報警內容。
“我操。”師傅輕聲的罵了一聲。
ST-T改變意味著患者的心臟出現了缺血,並隨時有急性心肌梗死的危險。
“給點艾洛,把心率降下來。”我知道師傅這樣做是為了給心臟儘可能舒張,跳動減慢,降低心肌氧耗。
“終止手術,打電話給ICU把患者轉過去。”師傅的語氣變得更加嚴肅。
麻醉誘導以後終止手術,我還是第一次碰到。
這是,在旁邊一直安靜看著的婦科醫生突然說話了,“那您看這個患者後面......”
“你們這群人幹什麼吃的,病史問清楚了沒有,問清楚了為什麼還是這樣的情況,看到那個T波了沒,處理不好人就可能過去了!”師傅幾乎沒讓他把話說完。
“把手術停了,冠脈CT、心內科會診,把心臟的事解決了再說。這個樣子你們也不怕下不了臺?術前檢查怎麼做的?”師傅依舊在責備管床的婦科醫生。
“教授,我也不知道患者心臟有問題,之前問的從沒發生過不舒服,之前也沒吃過什麼藥,心超心電都是好的。她就說偶爾有些悶悶的,但更年期這種情況很常見啊。冠脈CT也不是常規檢查專案,我們確實不知道會這樣啊。”婦科醫生有點委屈。
我知道,她說的也沒錯。
一箇中年女性,沒有任何既往疾病,偶爾的胸口發悶很難往心臟的問題上想,更多都是考慮更年期反應。更何況常規檢查都沒有提示心臟問題,讓患者做個冠脈CT才是真奇怪。
“總之推回去把檢查做好,心內科調理好以後再考慮手術的事。”師傅說完,轉身走了。
我拿起電話給ICU打過去。“嗯,對的,懷疑誘導期有心梗或者冠脈痙攣,沒有基礎病史,需要心內科會診一下。患者沒拔管,先放到你們那邊。”
我再到ICU見到這個患者的時候,心內科已經會診完給出了藥物治療的建議。她很焦慮的問我會不會留下後遺症,手術還能不能做。
我說,“你先彆著急,把心臟的這個毛病好好調理。調理好了再手術。”
“唉,你說睡一覺就好,你看,這一睡又睡出了一個毛病。”她還是一副焦慮的樣子。
“放輕鬆,別擔心了。”我沒有再說更多,轉身走了。
麻醉的確是睡一覺的事情,但在她睡覺的這半個小時裡,她幾乎在鬼門關走了一遭,而我的心跳也跟著起起伏伏了半個小時。
麻醉誘導不過是把麻醉藥按劑量一次推入血管,但推入血管之後的事情,才是麻醉的真正意義。不同的人,對不同的藥物,產生不同的反應。這三個不同,導致了麻醉的不確定性。
至於這個患者為什麼發生了心臟問題,可能由於藥物對心臟的抑制,也可能因為輕微的過敏反應使血壓下降,導致心臟的血管缺血痙攣;也有可能什麼都不是,就是自發的血管痙攣。
醫學,就是從這些不確定的事情裡找規律,然後根據規律得出我們的理論和方法。
麻醉狀態下,人體的保護性反射大多被抑制,身體對藥物、手術或刺激等反應不受控制。在這種巨大的不確定性中,總需要有人來處理可能的突發情況。
這個人,就是麻醉醫生。
我突然明白那一句關於麻醉收費的話,
“我讓你睡過去免費,但讓你平安醒過來則是收費的。”
在睡覺的過程中,守護患者的生命安全,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麻醉醫生也算是一個守夢人。
我還是習慣在誘導的時候對患者說
“放輕鬆,深呼吸,我們開始麻醉了。”
我知道,你睡過去了,我的工作就開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