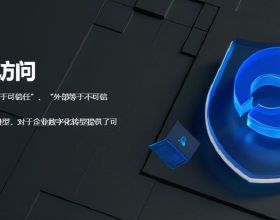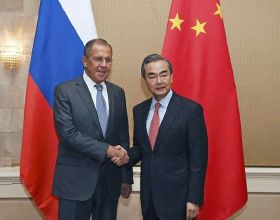直覺上來說,我們看起來相信,如果我們對一些人大喊大叫了,讓他感受到足夠的難過,他將會在邏輯上的選擇改變他的行為方式,或是,如果我們理智的解釋事情,他就會明白。但是當你大喊大叫或是與一個已經很難過的孩子來講理智,其他一些事情會發生,一些不與邏輯有關的事情會發生。實際上,你越多的大聲喊叫或是嘗試著與你的孩子講道理,他將會變得越焦慮和難過,他就越強烈的需要讓你明白他的感受和為什麼,這意味著他的行為更像是在逐步升級——你就在試圖避免極端的結果。更多的是,當所有這些事情在發生的過程中,他實際上沒有能力來理性的思考和控制,或是改變他的行為。
在最簡單的術語裡,人類神經系統裡許多功能中的其中一個就是,無論我們在何時感到受威脅時,都要設定一個鬧鐘。當這個鬧鐘失靈了,我們變得有所害怕或是生氣,我們的注意力變得完全地專注在我們感到害怕或是生氣的資源上,那麼我們其實從身體上是無法看見“更大的藍圖。”這是一種完全不由自主的反應,被大腦裡的一個叫做杏仁核的地方所控制,你可能聽說過一種介紹叫做“戰或逃”的機制。設計戰或逃是讓我們活下去的重要回應,一旦它被踢爆了,其實也就關閉了理性思考的路徑。我們是否感受到了焦慮和難過,其實不是至關緊要的事情,因為我們在身體上被一隻老虎攻擊了,或是在口頭上被對我們大喊大叫的一些人攻擊了,或是否定我們感受的人所攻擊了;我們的神經系統會對所有這些事作出一樣的回應。
作為成年人,我們都經歷過這樣的處境,我們是如此地感到難過,為此說了一些不經過思考的話,即使我們是知道他們是完全不合時宜被講出來的。然而,孩子們一直掉入進了戰或逃的模式裡。隨著我們成熟起來,我們更好地能夠區分真實和想象出來的威脅,發展更好的衝動控制(儘管一些人永遠不會非常擅長於此道,以生氣管理治療結束),但是年輕的孩子們總得來說是很不擅長於區分這些事情或是控制住他們的衝動的。
以這樣的例子來說,我們需要做的是,如果我們想讓我們的孩子傾聽和能夠改變他的行為方式,首先就是讓他感受到他是安全的。你的孩子更多地相信你是理解他在難過些什麼的,他將會越感覺到自己是安全的。再一次地說,你是透過鏡映來做到這一點的,讓他透過你的言語,你嗓音的聲調和你的身體語言知道你接收和不僅僅理解到了這些資訊,而且還有他正在發出這些資訊的迫切性。當你這麼做的時候,你不僅僅是有效的在說你“知道,”而且你也會“罩著他”——因為你仍舊在這裡繩索的另外一端——他能夠開始放鬆。然而,你能夠爭論,大叫,或是理智化你所有的一切,直到他自信於他的資訊被接收到了;這些行為並沒有太大的區別。
我不久在我自己的家庭裡經歷了這些事情,當我的大女兒,Zoe,她快要十一歲了,瞭解到她在這個世界上最好的朋友將要搬去法國了,因為她的爸爸被他的公司轉移了。在她知道這件事情的那天,我正在工作,一位家庭的朋友來做拜訪。Zoe從學校回家了,她完全的被這件事所震驚到了,抽搐著流淚。我們的朋友——一位非常移情神入和敏銳的女性,她做了很多年的教師——她被Zoe是多麼的難過所過渡充斥著,知道她自己需要做一些事情來讓她感覺好起來。當然,問題是真的是沒有任何人可以說或是做一些事情來改變她的最好的朋友搬去另外一個國家的這個現實。
Zoe感到非常的難過。“這一切太糟糕了。我永遠不會再有最好的朋友了!這是可以發生的最糟糕的事情了!她要搬去法國,法國,法國!”而我的朋友盡她所能的讓她自己聽起來是冷靜和理智的,說了一些這樣的話,“我知道這很難,但是你會找到另外一個朋友。這種感覺現在看起來是很糟糕的,但是你將會克服它,法國,好吧,又有多少人能夠說他們在法國有最好的朋友呢?當你停止想這件事的時候,這其實還是挺令人興奮的。”接著,Zoe大哭了起來,“不,這一點都不讓人感到興奮!這一切太糟糕了,我不想要克服它,而且我永遠不會再有一位像她那樣的朋友了,永遠不會!”
接著,我的朋友開始給出了像是這樣的建議,“這並不是世界末日。你能寫信,你能夠在電腦上給她發信息。”她甚至試圖想要有所共鳴地這樣說,“我知道這對你來說很難...”所有這些只是讓Zoe感到更加的難過了。
就在這時,我回家了,聽到了她們的談話,我可以這樣說,我的朋友開始有一些些惱怒了。從她的觀點來看,她正在努力讓Zoe打起精神來,Zoe卻沒有很好的回應她。Zoe聽到的內容卻是,然而,她不應該為此而感到難過,她最好的朋友搬去法國,是一件好事,這一點讓她感到很是生氣。為什麼我的朋友就不能理解,這並不是一件好事呢,這件事糟糕透了,這是在她身上發生過的最糟糕的事情?她逐步升級的回應只是在功能上簡單的試圖穿越它們。
之後,我和Zoe交談了起來。我鏡映了,我說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法國!你在和我開玩笑嗎?法國?你知道她會搬去法國嗎?太遠了,而且這太突然了!”
會話的其餘內容是一些諸如以下的對話:
Zoe:不,我們不知道任何事情;這件事就這樣出乎意料地發生了!
我:這是你最好的朋友,你所有的時間都和她在一起。我打賭,你甚至無法想像沒有她的日子。
我知道,這聽起來就好像我應該讓她甚至更加難過一些,但是並不完全是這樣發生的。Zoe繼續...
Zoe:是的,這是我不會再有的最好的朋友;我不會再找到任何像她一樣的人了!
我:所以你無法甚至在此刻想像出會有像她這樣的朋友來到你身邊。
我們繼續這樣交談了大約有三句或是四句或是更多的句子。Zoe說了這樣子的話,“若是沒有她這個朋友的話,我該怎麼辦呢?學校生活都不一樣了!”我是這樣說,“我能夠理解。你每一分鐘都是和她在一起。你甚至都不知道沒有她的一天將會是感受到什麼樣子的事情。”
就在此時,然後,有更多的眼淚出現了,就在不久前Zoe就在抽泣和問到,“你認為我們有什麼辦法去法國拜訪嗎?你能夠教我怎麼發即時資訊嗎?我能夠給她打電話嗎?”
我在當中有了這樣的想法,這真的是一段很美好的友誼。Zoe非常想要有這樣的一位好朋友,而這個小女孩對她來說是很完美的。她們互相仰慕著。當我上八年級的時候,我最好的朋友搬去了加利福尼亞,我記得這件事有多麼地令人傷心,我感受到了多麼的孤獨,和我是如何地害怕我將不會再見到她了。這簡直糟透了。我希望這件事會遠離我。她又是如何將會渡過這樣的事情呢?我想要為了她拿走這樣的痛苦。當你的孩子在情緒上受傷時,這是非常令人感到痛苦的;你非常的想要讓這件事好起來,你希望你能替代她,這一切都發生在你的身上。但是我知道我一定要把這些念頭拋擲腦後,足夠勇敢的和我的女兒一起呆在這個當下。因為我能夠做到,Zoe在想,噢,wow,我的母親真的理解到我了。她真的理解這件事是如何的傷害到了我,和我是如何地害怕於失去我的朋友。
我知道,我無法修補好這個問題,我所需要做的就是坐在那裡,和我的孩子一起經歷這段痛苦,不用嘗試著縮小這個問題或是流傳這個問題。我知道這也是讓我的孩子渡過這痛苦的時間的唯一方法,和學習著知道她已經足夠的強大來處理好這件事。經常是,當我們的孩子感到難過和受傷的時候,我們用我們的日程安排插入其中。我們瘋狂地想要讓她感覺好起來(以致於讓我們自己感覺好起來)我們有所行動和試圖修補它。問題是這樣做能夠真的妨礙了我們的孩子想要和我們交談的渴望。如果我們無法忍受她們的痛苦的話,要不他們就發現和我們交談是沒有生效的,或是他們擔心他們會傷害到我們,所以他們就選擇不要這麼做。足夠的勇敢來與你的孩子停留在這個痛苦中,是為了讓她能感覺好起來和鼓勵她來告訴你,她的生活裡究竟發生了什麼樣子的事情。我記得有一位母親這樣說過,“你要有膽子在那裡。”
我們的會話到了這一步,Zoe不再需要說服我,她的資訊是多少的緊急。在我陳述了四句或是五句話之後,她聽到的內容是,我很領會到她的問題的嚴肅性,和她為什麼會感到這麼的難過,因為我這樣做了之後,她能夠足夠的平靜下來了,最終接受了我的朋友一直以來試圖告訴她的事情和繼續解決問題本身。最後一步是,給她一種競爭力的感覺,以此來再次確定她的感覺,我相信她具有一切她所需要的資源來渡過這個困難。
我在之後又與Zoe有了一次或是兩次有關這件事更多的會話,而且我堅定地相信,如果我沒有允許她去感受到她的痛苦的話,她將會有多次這樣的遭遇,就像她和我的朋友那樣的狀況。取而代之的事情是,她渡過了這個困境,交到了她之前沒有機會了解的新朋友。
當你經歷這些會話的時候,你不一定要很妙語如珠的,和斟酌著你將會說些什麼偉大的話語。最重要的並不是你說了多少的話(儘管這一點也很重要)而是你是如何把它說出口的才是最關鍵的。你的孩子將在離開的時候記得這場對話給她帶來的感受是什麼樣的,而不是你所運用的每一個特殊的詞語。我們的會話讓Zoe感受到了被擁抱的感覺,被愛,被理解,和在情緒上被抱持住的,就我的朋友而言,除去她最全心全意的努力之外,還是讓她感受到了有在說廢話的感覺,和對方並沒有對她的資訊的緊迫性有所上心。
翻譯自《Connected Parenting》by Jennifer Kolari, MSW, RS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