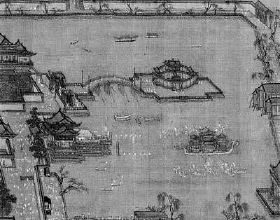澎湃新聞記者 高丹
中國色彩的所指是非常不穩定的,甚至具有欺騙性。
蘇軾在一首寫牡丹的詩中有這樣的句子:“一朵妖紅翠欲流,春光回照雪霜羞。”其中,“翠”的使用令人感到迷惑,為什麼“妖紅”的牡丹花是“翠欲流”呢?原來,“翠”不是青翠的翠,它不表示顏色,而是表現牡丹顏色之鮮明奪目,由此可見,顏色詞在古典文學中有多種可能。而在更宏大的層面上,中國傳統色長期受五行的影響,有著非常強烈的象徵性。
在這種強大的不確定性中我們怎樣去研究中國色彩?
中央美術學院研究員王京紅談道,要建立一箇中國傳統色的理論模型,不能只是套用西方的色相、明度、彩度提純的三要素,而是應該用正色、間色來表達。此外還涉及質感、面積、溫度、溼度等物理科學上的分類。還有人文上文化意象的東西,中國的色彩從來都是把不便說、不能說的事情用色代為言說,這說明色彩背後有更多的隱喻性、象徵性,指向其背後的精神特質。此外,中國色彩還和自然時空相結合,古人以陰陽五行、八卦來概括時空觀念,在這個秩序中,還有從太極、兩儀、四象、八卦、十二卦、二十四節氣、七十二候......以這個模式來展開。
在最近舉辦的“2021中國傳統色彩學術年會”中,學者們對東方色彩觀念及表現進行了研討。
五行陰陽系統中的中國色彩
回到中國的歷史與文化語境中。中國古代習慣將顏色分為“正色”與“間色”。孔穎達疏解《禮記·玉藻》說:“玄是天色,故為正;纁是地色,赤黃之雜,故為間色。皇氏雲:正謂青、赤、黃、白、黑,五方之色;不正謂五方間色也,綠、紅、碧、紫、騮黃是也。”正色指青、赤、黃、白、黑。其中,青是藍靛、天藍色;赤是硃砂即中國紅;黃即雄黃、橙黃色;白是鉛粉呈現的銀白色;黑是墨色、赤黑色。
與正色相對的則是間色。汕頭大學的學者肖世孟在《“間色”考》的報告中指出:間色在中國古代是非常生活化的顏色,比如民間的年華等幾乎全用間色。事實上正色只是用在一些禮儀性的場合和正式場合,用途遠不如間色使用的這麼廣泛。如果我們穿越到古代去,可能看正色是比較少的,多數的時候看到大量的是間色。
顏色在古代夾雜著強烈的價值判斷。先秦文獻最早出現“間/間色”的三處:《禮記·王制》中談道,市場上不能販賣間色的布帛,“間”帶有一種染色不過關、質量不過關的意思。《禮記·玉藻》、《荀子·正論》都是將間色作為與正色相對的抽象大類,“間色”有不符合禮法規範的含義。受到宇宙陰陽二分與五行思想的影響,“間色”除了帶有價值判斷以外,也有鮮明的陰陽五行特徵,肖世孟認為,間色之所以生成有三個可能性,分別是陰陽相剋(陰陽相剋相互打散、互相消解產生新的事物)、五行相剋、正位之偏。
西方色彩學的“色”僅僅指色彩的面貌或者種類,中國的“色”則涵蓋非常複雜,有著強烈的象徵性,相對穩定的正色就如其名字所顯示的,成為正面的、德性、身份的象徵。
五色與正統王朝統治的合法性
“從春秋、戰國經秦漢實踐並至南宋滅亡,以視覺色彩形式最終顯現的‘五德終始’的觀念體系成為了中國正統王朝統治合法性的具體表現。在五德終始的應用階段,它自上而下,從國家層面向下影響到了國家政治、倫理、社會、文化、生產方方面面的視覺表現,國家象徵色彩成為了各應用層面的核心存在。”汕頭大學的學者陳彥青指出。
我們以各個朝代所崇尚不同顏色的具體案例來看。
比如提起最能夠代表中國的顏色,我們首先想到的紅色,為什麼“中國紅”紅了三千年一直沒有改變?中國為何“尚赤”?西安美術學院教授彭德認為,其實,尚赤是普遍而古老的習俗,透過考古發現原始人均崇尚赤色,翻閱各國國旗顏色,大概有九成左右都有紅色,其中紅色比例最多的國旗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旗,中國將對赤色的喜愛發展到極致。像我們前面介紹的,中國的色彩與陰陽五行密不可分。周朝五行屬火,色彩尚赤。孔子說:“周監於二代,鬱郁乎文哉,吾從周。”周借鑑夏商兩代文明,周朝的制度和文明模式影響後世,也在很大成都上確立了“尚赤”的傳統。
歷朝歷代是天命神授,不可更改。就像是現在很多地方依舊保留著為新生的小孩算卦看命格的傳統一樣,每個朝代都會卜算自己屬於金木水火土五行中的哪一行。比如歷朝歷代中,五行屬火崇尚赤色的王朝和皇朝有東周和西周、東漢、六朝梁國、隋朝、宋朝、明朝。五行屬土崇尚黃色的朝代:西漢、曹魏、六朝—陳國、唐朝。他們也都崇尚赤色,因為涉及到五行相生。唐朝的天命屬土、國家標誌色是黃色。按照五行相生的規則:火生土,所以赤色是黃色的生色是吉色,它相當於宰相的地位,黃色就是帝王皇帝的標誌。其它的三色對於唐朝都是壞色。
比較特別的是元朝和清朝,他們不是漢民族,原本沒有所崇尚的單一的顏色,所以元朝在北京的宮瓦是五色,但是諸如北魏、金、元,以及最晚近的、我們最熟悉的清朝其實都或多或少地被這種色彩的觀念體系所同化。
學者陳彥青分析:“從農耕文明傳統中發展而來的‘五德終始’一代一代中心疊加迴圈的方法,從某種意義上成為了應對那些試圖滲透、征服農耕文明的遊牧民族的隱形防禦體系,它甚至帶著某種吸附轉化的攻擊性,將遊牧者轉化成為了安居之民,並進而融化成了中原歷史、文化傳統的一份子。遊牧民族的漢化,成為了五德終始應用與國色選擇的典型表現,它不同於漢族內部的五德終始與國色的表現,在其應用的過程中表現出了適應性與多重的選擇性。而漢族文人士大夫在這上面參與極具主動性。”
因時代而異的東方色彩:語言學視閾下的顏色詞
東方色彩已經在多維景觀下顯現出獨特而複雜的體系結構,色彩與文化領域的其他內容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牽一髮而動全身,不能孤立的研究,必須做總體論的研究。
東方色彩絕不是一直像五行五色系統的大框架中呈現的那種簡明,山西大學文學院副教授侯立睿在名為《〈爾雅〉原文及郭璞注顏色詞系統的語言學觀察》 的報告中,就呈現了色彩在語言學中的複雜性。
中國最早的一部辭書《爾雅》主要彙集了先秦時期的文獻詞義訓釋,也有少量西漢時期內容的增寫,反映了我國早期文獻詞彙的使用情況,其中所收錄的詞中即包括顏色詞,東晉郭璞(276年—324年)的《爾雅注》是留傳至今最早的《爾雅》注本,後世研讀《爾雅》的最重要注本。
顏色詞主要是指事物色彩屬性的一類詞,一般從具有某種色彩特徵的名物詞當中抽象出色彩特徵的。抽象出的顏色詞往往和它所屬的事物關係密切,但已經不再表示事物概念本身,而是可以描繪具有相同色彩特徵的事物。
《爾雅》時代是含彩名物詞向顏色詞轉化的活躍時期。今天的一些顏色詞在《爾雅》書中既有仍屬於名物詞的情況,也有已經變為顏色詞的情況。如“驪”,本指毛色黑的馬,《爾雅·釋畜》:“小領,盜驪。”郭璞注原文,此處的“盜”,指顏色淺,“盜驪”,指淺黑色的馬。雖然明方以智在《通雅·衣服·彩色》中將“盜驪”釋作一種顏色。但是從嚴格意義上來說所引《爾雅》此處的“驪”還是實指毛色黑的馬,是名詞,而非顏色詞。而在同一篇《釋畜》中:“驪馬白跨,驈。”郭璞注:“驪,黑色。跨,髀間。”此處的“驪”已明確地置於“馬”前,修飾馬的顏色,屬於顏色詞,表示全身黑色跨部白色的馬叫做驈。因此,在分析《爾雅》顏色詞的時候,要根據出現的語境和場合來判斷,具體情況具體分析。當一個詞指向具體事物時,為名詞;當一個詞指向描述事物顏色屬性或特徵時,為顏色詞。
《爾雅》全文十九篇,共1313字,其中真正的顏色詞有27個,其中單音節顏色詞有23個,分別是:黃、白、素、皤、赤、朱、丹、彤、縓、頳、纁、駵、青、蔥、蒼、黑、烏、玄、黝、驪、陰、夏、茈;雙音節顏色詞有4個:竊玄、竊黃、竊藍、竊丹。
郭璞注全文共7890字,其中真正的顏色詞共有51個,按顏色詞比例來說,雙音節顏色詞佔23個,是整個顏色詞當中非常多的一個比例。從它們的對比上可以看到,許多詞的顏色義在郭璞所在的時代消失了,繼而被新的詞所取代。同時也可以看到顏色語義的豐富,有由《爾雅》名物詞引申出顏色義,成為顏色詞的方式,還有透過增加音節和顏色語義的疊加得到實現的方式。
郭璞和《爾雅》成書的時代相差千年,郭璞的時代,顏色詞的使用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而郭璞距離現在也有近兩千年,中國傳統顏色詞系統與現代色彩學視域下的顏色詞系統,在認識論、歸納和命名方面存在差異巨大,已不單純表現在某個上位概念的更替上。因此,在構築傳統顏色詞系統時,有必要從文獻材料出發,結合中國古代文化、考古、科技等知識來逐一進行辨析和考證。
責任編輯:梁佳 圖片編輯:沈軻
校對:施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