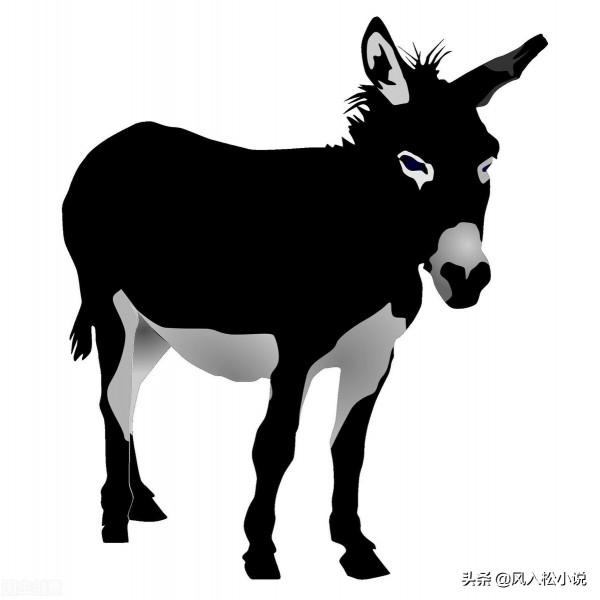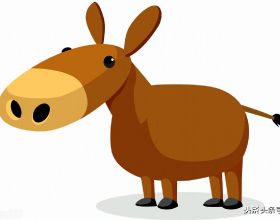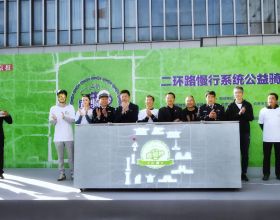“你不要撇下我啊!啊嘿嘿……你讓我難活得怎麼過呀……啊嘿嘿……”
打麥場上,中年婦女懷抱著氣若游絲的中年男子嚎啕大哭。哭腔悲涼而又滑稽,像職業哭喪者的表演。但那痛苦之情卻是真的,因為這個將死之人是她的丈夫。
男子翕動的嘴唇,上面沾染著猩紅的血跡,但卻面無血色,喃喃地說:“二娃怎麼會殺人呢……”
在那中年男子的左手邊,堆著兩大捆新鮮的苜蓿草,是他剛從田間用肩挑來的餵驢的。墨綠的草葉上懸掛著一些血滴,如清晨的露珠,但卻猩紅而粘稠。那躺在女人懷中的男子,臉色蒼白如紙,嘴唇弱弱地翕動著,艱難地說了幾句話後,喉嚨裡嗚嗚咽咽就再也說不出話來。
婦女的哭喊聲,引來了一群女子,看見氣息奄奄的中年男子,都扯開嗓子哭喊了起來:“大啊!啊嘿嘿……大啊!”
那躺在地上奄奄一息的中年男子,不是別人,正是駱煙鍋,懷抱著他的女人是郭三娘。夫妻二人雖勢同水火,但眼看駱煙鍋出事,郭三娘卻最是焦心。駱煙鍋就像一條檁子,平時裡瞧不出他的重要來,但一旦他倒下去,郭三娘心中的那間屋子也就垮塌了。
駱煙鍋自因借驢,被駱風打了之後,便落下了咳血的病症。之後巧兒被休的事,又讓他憋了一肚子窩囊氣,更加重了病情。捨不得花錢看病,一直沒有看過醫生。以前身體不舒服,還有駱半仙瞧病,現在駱半仙去世了,身體不舒服就硬扛著。駱煙鍋身體不好人卻要強,還把自己當成健康人,仍每日干重活。
這日駱煙鍋去地裡給驢割苜蓿草,為了一次割夠幾天的量,就割了兩大捆。用扁擔一頭挑著一捆,踉踉蹌蹌地挑到打麥場裡。一路上就覺得胸口沉悶、陣痛,但仍硬撐著挑了來。
駱煙鍋掙扎著把兩大捆苜蓿草,挑到場裡放下時,就看見兩個身穿警服頭戴大蓋帽的人,從他家的大門裡走出來,氣勢凜人地向他迎了上來。兩個警察的突然到訪,讓駱煙鍋心裡咯噔一下慌張起來。手足無措地站著,接受警察的詢問。
“你是駱江鰲,駱雲是你兒子?”警察直截了當地問道。
駱煙鍋雖不知發生了什麼事,但預感不祥,雙腿不由得顫抖起來,顫聲問道:“我娃他犯事了?”
“駱雲捅了人,已被拘留。傷者在醫院呢,你帶上醫藥費,跟我們走一趟。”
駱雲捅人的訊息,像一記重錘,狠狠地敲擊在駱煙鍋的胸口上。駱煙鍋覺得胸口一陣劇痛,渾身不由得顫抖起來,一口鮮血突然噴了出來。踉蹌著栽倒在地,沒能再起來。
警察本想帶駱煙鍋一起走的,看駱煙鍋吐了一口血栽倒在地,覺察到情況不妙,相互遞了下眼色,徑直走了。
太陽光溫煦地從西半天照下來,大概是個下午五點鐘的樣子。太陽光把駱煙鍋的臉映照成了古銅色,像一尊平躺著的雕塑。一群人圍著他,嚎哭著,那景象悲涼而又祥和。像一場古老的祭祀儀式,每個人都扮演著各自的角色。
庸庸碌碌一輩子的駱煙鍋,從未做過什麼轟轟烈烈的事,在最後卻上演了一場悲壯的結局。駱煙鍋在駱半仙去世的時候,就想到過自己的死。他想:自己死的時候,也要體面地安詳地死去,就像父親那樣,自己穿好壽衣,坐在那一樹開滿百花的梨樹下,悄然地死去。但他怎麼也不會想到,自己的死竟會以這樣悲慘的方式到來。
駱雲進了局子,劉建國生死不明,駱煙鍋猝死,這重重禍事,都是因她而起,讓她自責痛苦。若不是因為她,駱雲就不會犯事,劉建國就不會受傷害,駱煙鍋就不會死。
一群女子急促而悲痛地嚎哭,聽得駱江龍心裡一陣恐慌。聽女子們的哭聲,心知是駱煙鍋出事了,急忙向西山坡上趕來。當駱江龍趕到時,駱煙鍋早已停止了呼吸。駱江龍看著弟弟毫無生氣的面孔,鼻子裡一陣酸楚。走上前去,用手合上駱煙鍋無神的眼睛。
“江鰲他歿了。”駱江龍哽咽地說。
駱江龍的話,就像是對駱煙鍋生命的宣判。一家人知道駱煙鍋再也活不過來了,就哭成了一團。
聽到哭聲的村民們,知道駱煙鍋家肯定是出事了,男人們都自發地趕來了。駱煙鍋的兩個兒子都不在場,只有一群女子啼啼哭哭。看到亂成一鍋粥的駱煙鍋家,村民們開始自發的主張起喪事來。有人從草垛上扯下來麥稈,抱到上屋裡鋪到地上;有人把駱煙鍋的屍體抬進屋,平放到鋪在地上的麥稈上面;有人在爐子裡生上火,在爐子旁擺上茶具,招呼前來的村民們喝罐罐茶。
駱江龍找來白紙,撕了半張蓋在駱煙鍋的臉上,又用另半張紙用毛筆簡單地勾勒了一副毛驢的形象,拿到院牆底下的水眼處焚燒了。意圖是讓死者的魂魄,騎上毛驢上路,免得黃泉路遠,路途艱辛。
按習俗,父母的喪葬事宜由長子操辦。駱風是駱煙鍋的長子,村民們等他前來商討各項事宜,可等了許久都不見駱風的人影。村民們等急了,就商討了下,指派了兩個人前去尋找。
尋駱風的人到駱風家時,駱風正對著鏡子,抹著頭油來來回回地梳頭。前來尋駱風的人被氣笑了,打趣地說:“你先人都死硬求了,你還顧著打扮呢!”
“我大死了?”駱風有些驚訝地問。
“村裡人都到齊了,就差你這個長子來操辦事情呢,你竟然還在四平八穩地打扮自個兒呢。”那人瞥了一眼,依舊坐在凳子上照著鏡子梳頭的駱風,有些氣惱地說。
“我住持啥,找老二去。我大把好地都分給老二呢,他死了我可不管。”駱風霍地站起來身來,臉紅脖子粗地高聲叫道。
“哎呀,你呀,死的可是你先人呢?”前來尋駱風的人,氣得忍不住在駱風的臉上捶上一拳頭,狠狠地瞪了駱風一眼,氣呼呼地離開了。
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心,那村民沒想到自己拿熱臉去貼了個冷屁股,又是鬱悶又是氣惱。把駱風方才的話添油加醋地向大夥兒轉述了一番,村民們聽後都涼透了心。看到駱風撒手不管,村民斷斷續續地都離開了。只剩下駱江龍垂頭喪氣地,仍在準備著喪葬用品。
駱江龍用黃紙裁剪後疊成牌位的樣子,一張上面寫“供奉:駱氏祖宗靈位”字樣。一張頂上寫“供奉”二字,正中間豎著寫“駱江鰲之位”,兩邊寫著生辰年月及去世日期。紙疊的牌位,豎著插入一根細棍,再插入一半切開的土豆中間,兩隻簡易的牌位就做好了。
駱江龍自不當民辦教師以後,一邊開油坊一邊學陰陽方術,近年來跟著師傅操辦婚喪嫁娶大大小小十多場,師傅的本領學全了就開始自立門戶。遇上親弟弟的喪事,他義不容辭,就操弄起了駱煙鍋的喪葬儀式。
巧兒站在上屋的臺階上,望著駱江龍忙活的背影,心頭更加地酸楚。大伯背影,和父親的背影是那麼地相似。望著駱江龍的背影,巧兒總會恍惚,覺得眼前的人就是父親,父親他還活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