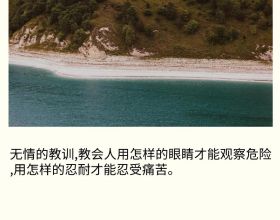田徑場的塑膠跑道上,晚間散步的人絡繹不絕。輿論已經深入人心:走路有助於祛除百病,更使氣血旺盛。籃球場上的奔跑與衝撞必須有一副強壯的軀體,柔若無骨的瑜伽則要求富有柔韌性的四肢。走路是普及版的鍛鍊,不存在任何技術難度。為什麼在田徑場上跑步要逆時針跑?通常的解釋是,心臟居於左邊,身體的重心偏左;同時,人們的左腿更為有力,跑步向左拐不易摔倒。然而,對晚間散步是不是可以有另外的觀點?我固執地認為,逆時針行走猶如把時鐘往回撥——頑強地把耗去的生命一分鐘一分鐘地撥回來。
耗去的生命堆積成了年紀。一把年紀的人,時間藏匿在生命的哪些地方?成熟了,安詳了,知天命的年紀換得了一副坦然的神情。當然,還有皺紋、白髮和日益肥胖的身軀,歲月是一把殺豬刀。
一把年紀未必就是垂垂老矣:不拿柺杖,走樓梯的時候拒絕攙扶,面不改色地喝一杯烈酒,與年輕的女子開一個無傷大雅的小玩笑——如若身為女子,挺拔的身姿與輕盈的步態是甩下衰老的標記,必要時可以與年輕人鬥一段廣場舞,咬牙忍住肩周炎的劇痛和膝蓋的顫抖。年紀多少依據的是出生檔案的記載,客觀而確鑿;老不老則是心裡的事,不服氣就算不上老。
一把年紀了還算不上老,不是虧了嗎?另一些人願意儘快領到“老”的牌照。老是資格,是威望,有時還是耍賴的基礎,例如倚老賣老。背起手來,腆著肚子踱方步,放慢語速,任意加標點符號斷句;喜怒不形於色,高深莫測地輕笑一聲把臉轉開,讓他們揣摩去;要麼用鼻孔哼一聲,毫不客氣地表示不屑——滿臉皺紋難道還兌換不到教訓人的資格嗎?即使沒有什麼顯赫的業績,一把年紀真實地擺在那兒,對方再大的本事也趕不上。有時與子女鬥氣,那些曾經耳提面命的傢伙遠比外人放肆。如果辯論的聲音越來越大,經典的一招是心臟病發作——沒有多少子女敢於領取道德風險如此之大的口頭勝利。
義大利哲學家阿甘本談到一個有趣的觀點:一個人既置入自己的時代,又適度地與時代脫鉤——這種人更具有時代性。保持一些距離也許能更為完整地認識時代的整體。我覺得,這種觀點似乎更適合一些老者。年輕的時候必須深入時代的每一個縫隙,目不轉睛,撲上去捕獲種種一閃而過的機遇,他們甚至沒有喘一口氣的閒暇,也沒有心情評判自己的生活。老境將至,漸漸地從忙碌的軌道滑出來,人們開始滋生一些反躬自問的念頭。反省上半輩子的成敗得失,無形之中也反省自己置身的時代。然而,另一些人可能覺得多此一舉。老境將至,還不能留一些時間給自己嗎?他們微微一笑,決定拋下自以為是的精英主義觀念。年輕人的世界交還年輕人管理,退休就是退後一步,專心休息。心頭無事一床寬,睡覺的時候可以放聲打呼嚕。醒來之後,悠閒地喝幾口茶,翻若干閒書,種一些不知名的花,招呼幾個老友打麻將。
無論多麼低調的人,一把年紀總是自尊的資本。譬如,我們多半願意援引長者的觀點,很少複述後生的思想作為佐證。“ 一個年輕人曾經指出……”誰肯對年輕人如此畢恭畢敬?“痴長几歲”只是老派的客氣話,心裡想說的是“我過的橋比你走的路還多”。經驗就是資本,老人家當然可以擺開架勢訓一訓年輕人。然而,一個麻煩的問題是,遇到歷史上的先哲怎麼辦?魯迅五十五歲逝世,王國維才活了五十歲就自沉於頤和園昆明湖。後人的壽命往往長得多。不知不覺到了六十歲,還好意思引用他們的言論作為思想的指南或者學術依據嗎?事實上,這種情況比比皆是。杜甫的壽命是五十八歲,王羲之也是五十八歲,曹雪芹四十九歲就溘然長逝。英國的浪漫主義詩人拜倫不過活了三十六歲,雪萊才三十歲。似乎沒有多少人關注這些顯赫的名字配置了多長的壽命。“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歷史剔除了種種瑣碎的情節而僅僅留下耀眼的偉業。進入先賢祠的大人物可以拋開年紀以及輩分這些世俗秩序。他們跳出了歲月鋪設的階梯而獲得了俯視眾生的資格,高高在上,年長者躬身請教也沒有什麼可羞愧的。
當然,先賢祠的入場券極為稀罕,絕大多數人無緣問津。先賢祠裡的大人物往往擁有超長的精神年齡,以至於可以跨越自己的時代與未來持續對話;相反,凡夫俗子的精神年齡遠不如身體年齡,許多人早早關閉了與世界對話的思想通道,六十歲的身體可能只有四十歲的精神積累。當然,他們不可能察覺與承認內心的貧乏,而是熱衷於依賴年紀爭取權威——這時的皺紋與白髮產生了實際的意義。“有的人活著,他已經死了;有的人死了,他還活著。”這句詩的後半句稱讚的是魯迅,前半句並非沒有物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