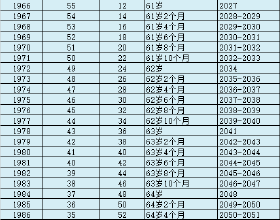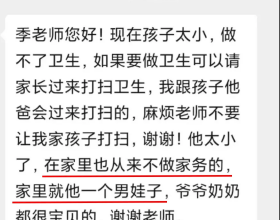還 生
第 一日
多日,我聽著外面咯吱、咯吱的開、關門之聲,老是無法清醒,醒來又睡去,當再睜眼時,周圍已是漆黑一片,蟲子啾啾的叫得人頭疼,大概是保持著同一躺姿已是很久,生硬的床板割著全身都發酸發疼。一動彈骨頭似於皮下熾烈碎開,我硬撐著身子緩緩坐起,動作幅度稍微大了一些,除了身體的痛楚,臉上的撕疼更顯,因臉上裹著厚厚的棉布,棉布裡那股奇臭的藥腥味撲入鼻腔,噁心得作嘔。身體的痛楚,讓我不自主的呻吟,引起了外房亮起了燭火,一個粗苯的身影朝我走近,沙啞得有些滄桑的男音傳進耳朵,“姑娘,你醒了?”我未應聲,著實是身上沒多大力氣,能勉強呼吸已經是我最大的極限,我仔細瞧瞧想知道自己在哪兒,或者是瞧清楚面前的人是誰。地方依然是前幾次醒來看到的景象,眼前人卻不認識。我到也未害怕,兩眼直直地望著眼前這個粗布衣裳,臉色黑油浮腫的村夫,村夫顯然是被我瞧得不好意思,侷促地說了一句“姑娘,我去給你做吃的。”我冷淡地點點頭,身體好不自然地滑進有些僵硬的被窩,幸得被褥中沒有什麼異味,只有淡淡的柴火氣。這是一間木材修葺的房屋,除了我身躺著的床,和不遠處的桌椅,房間裡無多餘的裝飾,暗沉古舊的傢俱,一扇破舊的竹屏風,實在不值得予以詳加描述。我從一場火光四射的夢中驚醒,渾身疼痛、無法動彈,腦袋昏沉,不記得自己姓什、名誰,怎麼到的這間木屋,怎麼躺在這床上。只是經過幾日與房屋主人的攀談,得知:七天前,這房屋的主人一個砍柴為生的樵夫在一里外的懸崖下發現了我,把帶了回來,還請了江湖中赫赫有名的神醫郭虛子替我療傷。然,傳聞這郭虛子曾是個和尚,法號虛無,為了一女子還俗,為她闖蕩江湖,因一身好武藝、一身好醫術,在江湖中一時聲名鶴起,時常奔命於各地,不曾想該女子難耐閨中,與一江湖知名人士做了苟且之事,後被郭虛子當場拿獲,女子便嫁作他人,郭虛子暗自神傷,不顧萬人挽留,自個隱姓埋名在這深山之中做了個隱士,鮮有聞塵俗之事。彼時,與郭虛子相熟之後,我便為他的經歷嘖嘖稱奇,一時驚,一時奇,因已對他有了幾分瞭解,看他不像是眼拙之人,怎就生生地遇到這般不識趣識相的姑娘,我一面摸著他及腰的長髮,一面拍著他英俊無比的臉蛋淫笑道,公子莫灰心莫灰心,定是那知名人士給你心儀的姑娘下了迷藥,你家姑娘才著了道。他用他深不可測的眼盯著我,似乎想把我抽絲剝繭一樣,我看看他的眼,又瞧瞧自己,裹了裹胸前的衣襟,嚥了咽口水,自覺的繞開他正欲發火的面容,暗想自己定也是個有故事的傳奇女子,沒曾想五年以後成了現實,這大概叫夢想成真。
在後來的回憶裡木盞告訴我,他瞧我的反應,隱約覺得我該不是普通人家的姑娘。大概因我當時心是空的,不驚訝自己發生了什麼,似乎生來就這般冷漠無情。也或是被什麼深深的傷得太過透徹才會在受如此大的傷後,不卑不亢。話說我失憶之後,當然失憶並非重點,重的是這滿身的傷,著實讓人疼得想死想死的。許多人是無法體會那種,每次醒來的感覺只有疼,從頭到腳都疼,疼到連哼都不想哼的境界,這些可能尚且能接受,畢竟還能用些言語來表述,最無法形容的是動一下猶如五馬分屍般身體立刻裂開,然後又進入一種完全沒知覺的狀態。值得慶幸的是,我遇到的確實是名神醫,不但醫術高明,顏值擔當,還能琴棋書畫,相當的悅耳、潤眼,以至於在心情愉悅和醫術高超的前提下,我身體的各個關節開始開放式的接納新生力量,能動之處愈加的多。
第二日
陽光瀟瀟灑灑地從床頭的窗戶裡灑了進來,懶懶地溢在我身上,我斜依在床頭,看著這個粗笨的村夫忙前忙後,他端來的熱粥帶一股青澀的藥草味,嘴裡咕咕嘮嘮的說“這粥裡有郭神醫開的一味山藥,聽他說是止疼的,你從百丈高的懸崖摔下來,多虧有郭神醫,不然……,哎咱不提這些了。”我停下舉到嘴邊的碗,煩悶地嘆了氣,未再繼續吃下去,如村夫所說,我一個女子從百丈懸崖怎麼就摔了下來,怎的也不見誰家丟了人,前來尋的?也或是遇了仇家復仇,那也要前來確認屍首身在何處?可很顯然,我更像孤魂野鬼,無人問津。村夫略顯緊張地走到我面前問:“姑娘可是哪兒不舒服?”我微微地抬頭看著他,昨夜不太光亮,沒看得太清,今兒看看,明明是個男兒,卻生了一副狹長的丹鳳眼,濃濃的一字眉,額頭高闊,臉頰豐滿,也沒有昨天看上去那麼黝黑,但絕稱不上好看,只能說普通平常,他被我望得不好意思地低了低頭,憨笑著撓撓頭退了幾步,我才淡淡的回了一句:“沒有,只是胸前似乎憋了口氣,要嘆出來。”想是覺得我的聲音僅如此悅耳,村夫臉瞬間紅到了脖頸處,扭扭捏捏的傻笑:“想不到,姑娘的聲音這麼好聽。”我看他那傻樣,有些不屑,有些厭惡,隨便打發他,就繼續睡了過去,亂七八糟的夢,一會兒是一個滿頭銀髮的老太婆舉著一根通透的玉杖,手顫巍巍地指著我大罵,一會兒是一群手舉火把的家丁到處亂砸,又是一嚶嚶哭泣的嬰兒躺在草堆裡,我多麼想伸手去撫摸,卻又變成我不停從懸崖墜落的景象,嚇出一身冷汗。醒後再難以入睡,直到天邊翻亮,才昏睡過去。
第三日
我還未醒,便聽到床前窸窸窣窣的聲音,又是嘆氣,又是拍床的,我警覺的睜開眼,發現一身青布衫的男子,束著高高的頭髻坐在床前,一雙修長白皙的手緊緊地按著我手腕,眉頭鎖得緊,我莫名地想使勁從他手裡滑出來撫平他的眉頭,他卻用了些力又拉了回去,“姑娘,在下正在為你診脈,切勿亂動。”聽著他悠悠的聲音,心裡格外的舒暢,便放鬆了神經,任由著他。他把眼神落在我臉上,我不自覺地撫了撫臉,還是厚重的棉布,腥臭的藥草滲進我的整個鼻腔,他笑了起來,白皙的臉蛋,清晰的輪廓,濃黑的劍眉,一雙好看的桃花眼,高挺的鼻樑,嘴唇紅得讓人想咬上一口,這男子長得既靈秀又英朗,竟也不好找更貼切的美男子詞彙來與形容,總之,美矣。“姑娘,莫驚慌,你臉上的藥敷上七七四十九日才可取下,現下也不過十幾日,還長著哩。”他這麼說我倒吸了口氣,這麼說來我已經昏睡了半把月,這一慌,我這幾日的平靜被攪得七葷八素,我是誰?我在哪兒?我這是怎麼了?所有的問題都衝進腦裡了,回想夢裡那些亂七八糟的景象,一下攪得我頭痛欲裂,青衣男子見狀又加勁按住我的脈搏,“姑娘,切勿動氣,你已經筋脈盡斷,在下可是用了深潭龍鬚為你續脈,切勿再出差池,否則我也無迴天法術。”興許是他聲音特別,聽著讓人特別踏實,漸漸平息了胡思亂想的念頭,嘴裡乾乾的吐出幾個字:“多謝郭神醫。”我剛說完,感覺他捏著我手腕的手輕微地顫了些,才驚覺外面吹起了涼涼的風,我緊了緊身上的被子,安靜地看著他的眼目,聽著外面流水經過的聲音和他沉重的呼吸。我驚喜神醫的醫術除高超外,服務也很到位,把了脈,親自護我入睡,卷被,熬藥,陪我到深夜才慢步離開,這才稱得上醫德。
第四日
村夫把藥遞到我面前,我瞧了瞧他的手裹上了一層厚棉布,但血色仍然滲到了表面,我不緊不慢地問:“你的手怎麼了?”他尷尬地搓搓手塞到了後面,含含糊糊地說是自己砍柴的時候被樹枝颳了,我仔細看他粗紗灰布料的衣著,手上的老繭,屋子裡堆著的柴火,我便猜想他該是個樵夫,我沒有繼續再問,喝了他遞來的藥又覺得乏了,還沒來得及睡去,一白衣身影提著個籃子繞過簡陋的屏風走了進來,我仔細一瞧,是郭神醫。我便也直挺挺地坐在床上,等著他走近我,我不自覺地笑了起來,但估摸著他是看不穿我的麻布直擊我的臉,待他坐定,我才發現他身後是隨著一個小女子,婀娜的身材,楊柳般的細腰,及腰的長髮簡單地攬在身後,青黃的底衣,白紗的外套,腰間的黃玉特別的顯眼,許是看著我直望著小女子,郭神醫回頭望望,又瞧著我說:“我小徒兒,月娟。”我看著她那清麗的樣子,杏仁眼,玲瓏鼻,櫻桃嘴,討巧得很,面善得要緊,忍不住向她招招手,郭神醫示意她到我面前,我伸手便摸了她的小臉,滿意的笑起來:“果然水靈,這面板倒也水嫩。”小女子竟被我說得嬌羞地跑了出去。我把看著她跑出去的身影收回來放在郭神醫身上,他一臉愕然地瞧著我:“你倒也是豪爽之人。”我有些不懷好意地將手撫向他的臉,他兩指便夾住了我的手腕:“姑娘,且注意分寸,容在下為你把脈。”我咯咯地笑出聲來,他的手顫了一顫,我笑道:“生氣我調戲你小徒兒,我只是覺得她好生眼熟”。他不再理睬,認真且仔細地號著脈,眼睛緊閉若有所思,我瞧著他的臉,除了一張白皙的臉,眉頭總是緊鎖外,挑不出半分毛病,手指纖長,能分明地看出每一骨節,我細細品味著眼前的人間極品,他好不適宜的長長地嘆了一氣,我正要問怎麼的,他反而微微一笑,“姑娘真是鐵打身軀,這從萬丈懸崖摔下來,竟可以恢復得如此神速。”我也禮貌地回笑道:“神醫過譽了,分明是神醫的醫術高明,否則小女子的命修矣”,郭虛子緩緩將手收了回去,淡淡的說道:“且不說我醫術如何,姑娘的臉是毀了,在下單獨給姑娘換了臉皮,不知姑娘可有不妥。”他這麼一說,我竟不曉得該如何答下去,要說我不在意,顯是不真實,那畢竟是我父母給的,可要說我在意,我本就不記得自己原來的面貌。我壓了口水說:“暫且沒什麼不妥,要是到時拆了一看,沒法入眼,我倒有話要說。”郭虛子噗地笑了起來,“姑娘的心態到是好得讓在下心眼小了一些,看樣子是我多慮了,姑娘且多休息幾日,容在下回去想一想到底是給姑娘植了誰的皮?要是動了個男人的麵皮,我看依姑娘的脾氣,在下才活不久矣。”我們倆默契地呵呵笑出聲來,引得在外的月娟好奇地往裡瞧了又瞧。
第五日
郭神醫今日未來,聽樵夫說御劍山莊的灼小姐得了心病,已經連發一月的高熱,今日突然驚厥不醒,御劍山莊的老太君出了家中的奇寶才動了郭神醫前去。我盯著樵夫家石板上的蜘蛛一動不動地聽著樵夫說關於御劍山莊如何那般快一柱香的功夫,悠然的問到:“那最近是不是郭神醫的小娘子幫我把脈?”樵夫顯是沒料到我會開口問話,被問得一愣,半晌沒回上話,我依舊說著:“我倒也喜歡那小娘子。”樵夫焦灼的望了我一眼:“姑娘,你這是打哪門子心思?人家月娟可是許得有人家了。”我被樵夫這一答噗嗤地笑了出來,樵夫更是不知所措咯咯巴巴地說到:“姑娘,姑娘,她可是御劍山莊要新進的……”我便不笑了,我心裡莫名地跳得厲害,我押了押聲音居然和樵夫正言起來:“我是個女子,難不成還真能瞧上人家黃花大姑娘,喜歡她全然是因著她這臉有幾分眼熟,我非磨鏡。”樵夫尷尬的望了望我,又看了看天色,才退出身去,說是去做吃食。還沒等我那顆煩躁的心平靜下來,郭神醫那清雅之聲便在我耳畔響起來,“姑娘,可是看上我家徒兒?”我稍有喜悅的轉臉看向他,又忽覺他有些戲謔,也無心和他玩笑,正打算給他甩個臉色,才想到,他也看不著,心裡又煩悶開來,自覺地躺在床上,任他直接將手放到了我腕上,一上脈他便望著我:“有心事?”見我遲遲不開口說話,便也不再多問。是的,我有心事。而且急火攻心,但就是不知道怎麼的。他只接過樵夫手裡的藥,一口一口地餵我吃了下去,也沒發聲說些什麼,這一場景一瞬間有些熟悉,卻不知從何說起,喝完藥眼皮漸漸沉重,郭神醫掖了被角,輕輕的退出房門,任我裝睡。
第六日
我今天知道樵夫叫二狗蛋,從小沒父沒母,是山裡的老樵夫將他養大,後來老樵夫死後,二狗蛋便繼承了衣缽,郭神醫兩年前遊歷於此,見此地風景宜人,便做了他的鄰居,還給他取了一個附庸風雅的名字---木盞,我卻更喜歡叫他二狗蛋,而且叫他二狗蛋時,他分外地高興,成天吹著哨子出去,又哼著調子回來,每天換著口味的給我做些山珍野味,我吃著也很順當,實在沒瞧出什麼不妥來,直到郭神醫出現在面前,他站在二狗蛋背後,就這麼望著二狗蛋瞧著我吃東西的場景,默默地咳了一聲,我抬起頭瞄了一眼,淡淡的冒一句:“你走路不帶聲麼?”二狗蛋才反應過來身後有人,慌忙站起來往後看,“呀,郭神醫,你什麼時候到的?”郭神醫沒理狗蛋,反而慢慢地揮了長衫坐在我面前,掐了我脈搏,帶著刺的口氣:“不帶聲,姑娘也是好耳力。”我繼續喝著碗裡帶著山野清香的肉湯淡淡回著:“過獎,過獎。”他卻有些用力地掐著我的手腕,我有些吃疼地哼了一聲,方才稍微放鬆了手力。誠然,我確實不知道他是不是在生氣,只覺得周圍的氣氛有些驟降。狗蛋招呼了郭神醫,退了出去。房間裡只聽到我倆此起彼伏的呼吸聲。我居然不適宜的有些嘴巴乾燥,全身發熱,傻傻地說了句:“我熱。”郭神醫淡定地抬眼看看我,手輕輕一揮,窗戶就開了。真就是手一揮,窗戶竟開,一陣涼風襲來,舒爽了許多。這功夫很是了得。我識趣地扯扯被角,挪挪身子,打趣地笑道:“你沒帶上你那嬌俏可人的小徒弟來走走?”他板著臉:“姑娘關心的地方可真寬。”寬麼?沒覺得呀。”我抽回自己的手,仔細看了看,細皮嫩肉,才驚覺我太閒了,閒到已有人嫌棄了,我懦懦地抬頭對郭神醫說道:“嗯,過些時日我能起身下地,便不打擾大家了。”郭神醫捏了捏手指節,咔咔地響,我更加不敢說話,雖心裡不算恐慌,可實在不知對方的實力,萬一是個狂躁分子,武力又如此高強,一掌劈了我,我還真是走得不明不白,我討巧的笑笑八卦著:“神醫,可是因為小月娟要嫁作他人,有些許不捨?”郭神醫拋來一臉我多管閒事的表情,倒了一杯茶,離我遠了一些,我暗自失望,心裡一副捶胸頓足的狀態,我怎麼哪壺不開專拎哪壺,只好壓制住內心的彷徨,靜靜的望著他。一望他便察覺,也轉眼盯住我,終於在我們眼神對峙的三分之一柱香後,笑道:“姑娘可不是尋常人,被在下這般望著,也不眨眼。”我扯出一絲絲笑容回道:“莫不是神醫經常這麼專盯女子看。”郭神醫扯出一副無奈的表情,隨即又笑了起來,好看極了。我抬手一招示意他過來,他顯是無動於衷,我裝一副全身疼痛的樣子,他竟像風一般刷得到了我床前,我個人感覺他還有些慌張的問我:“哪兒不舒服?”我嬉皮笑臉地盯著他:“沒事,來笑一個,我就想扒近了看看你,特別標緻。”他又是扯扯臉上的表情,很是無奈的起身就走,當然不忘囉囉嗦嗦地交代了這不動那不吃的醫囑。我在他身後嘎嘎地笑個不停。
第七日
清 晨,我一個夢衝,腿踢開了被子,我的腿會動了,我有些小激動。小心翼翼地爬了起來,確實能夠站著,沒有鞋子,沒有襪子,興奮地光著腳踩著冰涼、擱腳的石板,蹣跚地走到了屋外,滿山金黃,綠水幽幽,小橋靜靜地橫在大石山,對面一排小竹樓,美不勝收,外面清晰的空氣,滲進我的五臟六腑,舒坦得讓人想尖叫,狗蛋從橋上急忙跑來,緊張地扶住我,毫不生疏,大聲說著:“哎呀,姑娘你還不能下地走,怎麼還跑到外面來了,這快深秋了,著了涼可咋辦?”我反手扶住了他的肩膀,慢悠悠地坐到了大石上,他先是身體一直,後高興的任由我扶著。“姑娘,郭神醫讓我轉告姑娘,最近幾日他就不來給姑娘把脈了,說是脈象平和了,稍加休息便是。”我點了點頭,顯然點頭的樣子滿是失落,不過這山野村夫大是看不出的那看不清面貌的憂傷,我輕點水面上的落葉,轉頭強笑:“嗯,我喜歡這兒。”狗蛋愣了愣神說道:“姑娘,不嫌棄就好。我還是扶你進去吧,外面風大。”我顫巍巍地站起來隨狗蛋進去,在灶房裡看他做吃食,感覺特別的溫暖,心裡想留在這兒也無妨。就怕人家嫌棄,不過我也可以打打雜幫些忙,混口吃食大概也不是什麼問題。狗蛋利索地收拾了灶臺,乒乒乓乓便做了一桌吃食,他說他至今未娶,差一位女主人,家裡自從來了我以後就特別的溫暖。我趁機說道:“狗蛋,要不你就收留我,我至今也無家可歸,我雖不會砍柴,但這些簡單的家務大概不在話下。”狗蛋驚得跳起來,急忙說:“哪敢勞煩姑娘您。”我正想怎這麼快就被拒絕了,心裡稍有失落,狗蛋又興奮地說道:“那些粗活不適合姑娘做,您愛住多久就住多久,這些活我自己會拾掇。”我們兩默契的相視一笑算是達成了共識,我安心地吃著飯,他努力地往我碗裡夾菜,我們吃得嘎嘣嘎嘣的香。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