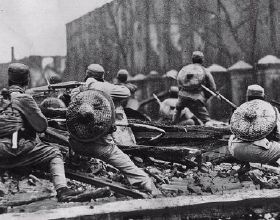澎湃新聞記者 王諍
編者按:在大銀幕上為優秀共產黨人光輝形象樹碑立傳,伴隨著新中國電影事業的發展。不論是江姐、趙一曼、董存瑞,還是上世紀90年代的焦裕祿、孔繁森,新世紀以來的任長霞、楊善洲、鄭培民、鄒碧華等等……這些銀幕上的優秀共產黨員形象,感動著一代又一代的觀眾。
特別是近二三十年來,英模紀實和扶貧脫困題材中湧現的共產黨員形象分外生動鮮活。與一般劇情片不同,依據真人真事改編,依據現有的歷史材料描繪典型環境,藝術摹寫、呈現其人其事,且片中主人公就是以傳主的真名示人,都讓這類反映優秀共產黨員事蹟的電影,共同匯聚成了意蘊豐贍的共產黨人形象譜系,積極擴充了國產人物傳記片的內涵與外延。
“人總是要死的,但死的意義有不同。中國古時候有個文學家叫作司馬遷的說過:‘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還重……”這段朗朗上口的文字,連帶文字所關聯的烈士,早已透過入選小學課文,在中國廣袤的大地上婦孺皆知。
2004年,是張思德同志犧牲60週年,也是毛澤東主席發表著名的《為人民服務》60週年。如何紀念?何以追緬?是年金秋,電影《張思德》的全國公映,交出了一張令人滿意的答卷。
17年前,中國內地電影市場經過上世紀90年代的蕭瑟,業已呈現出復甦的蔥蘢——自1994年開啟引進第一部好萊塢分賬大片,內地觀眾的觀影口味已然同世界接軌。而隨著《臥虎藏龍》《英雄》《十面埋伏》等國產大片的出爐,“宮廷秘幃”與“江湖武俠”是美式個人英雄主義之外,院線大銀幕上的另外兩大主題。
以黑白影像風格示人的《張思德》的出現,乍看有些“不合時宜”。這一方面源於彼時人們對主旋律電影的刻板印象——除了組織觀看,觀眾願意掏錢用腳投票進影院嗎?另一方面,相較於過往主旋律電影的程式化,作者風格明顯的《張思德》,會不會兩頭不討好呢?
時過境遷,由著當下中國內地大銀幕上新主旋律電影的蔚然大觀,再去“想當年”。彼時的疑慮迷思早已冰雪消融,而當年的先鋒前衛恰成而今的參照鏡鑑。
電影《張思德》公映後,一度讓導演尹力拿獎拿到“手軟”。僅舉一例,次年第二十五屆中國電影金雞獎上,該片一舉入圍七大獎項,並最終摘得最佳編劇(劉恆)、最佳男配(唐國強)兩項大獎。《張思德》之後,尹力又馬不停蹄拍攝了《雲水謠》(2006年)、《鐵人》(2009年),完成個人在新世紀第一個十年的主旋律“三部曲”。依次在大銀幕上塑造了中國革命戰爭時期的典型農民形象、中國現當代典型左翼知識分子形象、以及新中國成立建設時期的典型工人形象。2021年,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週年之際,在國家電影局推出的“百部經典影片獻禮建黨百年”片單中,這三部電影悉數入選。
接受澎湃新聞記者專訪時,尹力回憶說當初接拍這樣的電影,固然有“領命”的緣故在,更在於自己一向偏愛為“小人物”做傳的藝術追求,“什麼樣的作品是好作品?什麼樣的作品能讓觀眾在黑漆漆的影院被吸引,進而擊中他們內心最柔軟的所在?那一代共產黨人,他們懷揣的抱負、不墜的信仰,依舊值得我們去敬仰、去探究、去弘揚。”
提到《張思德》的拍攝過往,尹力先就一口氣說出了3個“嚴重違背”,“嚴重違背藝術規律,嚴重違背(電影)生產規律,嚴重違背電影規律,完全就是在‘倒計時’的方式下完成的。”
以下以受訪者口述形式呈現。
【尹力自述】
不拍成人物傳記片 “一滴小水珠折射太陽的光輝”
2004年3月初,北京市第十屆政協副主席張和平找到我,那年是《為人民服務》發表六十週年,也是張思德逝世六十週年。張和平早年間就讀於北京藝術學院話劇表演系,參演過話劇《張思德》,有這份情結。
其實,對於我們這代人而言,“老三篇”(指毛澤東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發表的《為人民服務》、《紀念白求恩》、《愚公移山》三篇短文)那是太熟悉了。童年、少年或青年時代,都曾背誦過,它跟我們每個人的經歷都息息相關。但怎麼能透過一篇文章,做出一部電影來?我思考了很久。
當年,一個燒炭的最普通的戰士犧牲了,毛澤東同志做了一篇題為《為人民服務》的文章和演講。它的發表有怎樣的時代背景、歷史背景?這是必須思考的一個問題。從國際形勢來看,義大利已經投降,德日法西斯的末日也為期不遠;太平洋戰場上,美軍節節勝利,日本軍國主義倒臺也是指日可待。這時,無論共產黨,還是國民黨的領袖人物,都在思考中國未來的命運。蔣介石提出了“新生活運動”,洋洋灑灑寫了一部《中國之命運》。毛主席講的是一篇文章《為人民服務》,開篇就把共產黨和共產黨所領導的人民軍隊的宗旨一語道破。直到今天,“為人民服務”仍然是中國共產黨的立黨之本。
張思德其人,留下的文字影像資料寥寥無幾。收集資料過程中,找到過一張黑白照片,一位戴著白帽子的戰士從燒炭的窯洞裡爬出來,有人說這就是張思德。我透過別的途徑找到北京武警某中隊(張思德生前所在班演化而來),一位90多歲的教導員,當年和張思德是戰友,卻說照片裡的不是張思德。
張思德到底長什麼樣?有人說很魁偉,有人說是小矮個。索性都拋一邊,我們不去拍一部人物傳記片,而是把張思德本身作為一個藝術形象來處理,在他身上是那個年代千百萬個八路軍,普普通通戰士形象的集合。
具體的,怎麼能夠讓張思德和毛澤東、讓張思德和延安發生聯絡? 我對他的概括就是六個字:訥於言,敏於行。就像電影裡毛主席說的那樣,張思德最大的優點是不愛說話,最大的缺點也是不愛說話,“他就像是清涼山上的草一樣。走到延安大街上,沒有人會多看他兩眼,可正是他們默默地付出,才支撐起了我們全部的事業。”
我在創作初期就定下一個基調:透過一滴小水珠折射太陽的光輝。影片中看不到驚天動地的行為,擷取的都是主人公生活中的細枝末節,透過情緒化的、資訊化的傳達方式,我們讓“延安”和一個“小人物”互相輝映。從能夠看到的資料中可以強烈感受到,雖然,當年延安物質生活是那麼貧困,還有日軍的圍剿、國民黨的封鎖、黨內黨外的各種各樣的事情,但那個時代的共產黨人確實是一批精英,一群有信仰的、朝氣蓬勃的人。
十一個字立項 “倒計時”拍攝
影片《張思德》的拍攝是在已經確定了2004年9月5日全國公映,卻還沒有劇本的壓力下,以“倒計時”的方式在148天內完成的。時間緊,任務急,要求高,手裡掌握的素材又少,是以拿去立項時就十一個字,“張思德,毛澤東,為人民服務”。中國電影這麼多年靠十一個字就能立項,拿出100萬馬上進行前期籌備,可以說是沒有先例的。
4月1日下達生產令,我和編劇劉恆4月3日就奔赴延安,跑遍了延安、綏德、米脂、榆林等多個陝北的縣市。那會兒延安的面貌,建築和周邊的環境已經發生了非常大的變化,坦白講,已無法再現六十年前的場景了。
當時大家開玩笑說劇本沒一個字呢,看什麼呀?肯定得看窯洞、警衛班駐地。我和劉恆去了延安的紀念館、棗園、王家坪、楊家嶺,兩天時間馬不停蹄,快節奏裡給我們的觸動,在而後幾個月裡一直貫穿在腦海裡。
張思德完全忘我,完全利他,犧牲奉獻的精神,在今天的市場化社會里是否還需要?這層反思某種程度上說,恰是我們願意費這麼大勁兒拍這部電影的原因。我認為這種精神不論在什麼時代,作為一種價值導向的存在都是值得弘揚的。
從編劇(劉恆)下生活、查資料到完成劇本,前期籌備到正式開機滿共用了45天,攝製組再以邊籌備邊拍攝的滾動推進的方式在66個工作日裡完成了米脂、綏德、延安等外景地96個場景的拍攝任務,又連續加班加點37天完成後期製作,終於在當年8月26日交出了完成複製,這期間的工作強度可想而知,每天最少工作十八、九個小時。
開機時把演員集中起來,我對大家講,在革命聖地,所有創作人員一定要懷有敬畏之心,要對得起先輩的付出,更要把那個時代的精神信仰和做人準則帶到拍攝當中去。兩位主演,從唐國強到吳軍,創作這個戲也是脫胎換骨,心靈歷練的過程。
攝製組當時提出一個口號,“以張思德的精神拍《張思德》”。《張思德》是唐國強第一次在電影裡塑造中年主席形象,鏡頭雖然不是很多,但我認為,這是他扮演毛澤東影片一次質的飛躍,從化妝造型的形似達到了收放自如的神似。
吳軍之前拍過我的《無悔追蹤》,他身上有普通戰士樸實,生龍活虎的勁頭。進組前他剛從一部古裝劇裡下來,胖得夠嗆。開機前不到一個月,他開始減重。每天只吃三個乒乓球那麼大的蘋果,然後就是曬太陽把膚色曬黑,還得爬兩次山,跳繩兩千下。結果,20多天裡愣是瘦了30斤。即便開拍後,他照樣天天跑步,穿著棉衣爬山,就是為了把他“逼”到生理極限。他在劇組到最後成什麼樣了?看見別人嘴巴動,都能有條件反射(笑)。其實不止他,這部戲裡凡是體重嚴重超標的,一概不要。
影片中,不管張思德是在風中雨中,是穿著草鞋還是光著腳,鏡頭都在刻意呈現他一溜小跑的狀態。影片開篇、結尾都在展現八百里秦川,張思德一個人在上面奔跑。片尾吳軍回眸一笑,拍的時候他瘦得幾乎得了抑鬱症。跟我說,“導演,我笑不出來。”
這個鏡頭在陝北沒拍好,回到北京,不甘心,又拉到昌平山裡拍,禿嚕了三本膠片才拍成。我就是要拍出一個淳樸、憨厚的青年農民形象,讓他能久久地立在大銀幕上。你甭說個一溜兒夠,千言萬語在觀眾心裡頂不上這一個鏡頭。
毛澤東和張思德作為全片最重要的兩個人物,我是把他們作為互為講述者來處理的。觀眾透過毛澤東的眼睛認識了張思德,建立起對於“張思德”的親和力和認同感;而張思德的所作所為,又提煉成毛澤東發表著名的演講《為人民服務》。
這篇文獻開篇怎麼講的?我給你背出來,“我們的共產黨和共產黨所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是革命的隊伍。我們這個隊伍完全是為著解放人民的,是徹底地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張思德同志就是我們這個隊伍中的一個同志。”
黑白膠片拍攝 “再現當年沸騰的延安”
我希望這部電影既能帶著觀眾回到那個年代,感覺到歷史沉澱下來的質樸、深沉的東西,還要讓人們感覺到那個年代的人的呼吸。
作為一部主旋律電影,《張思德》藝術特色之一,是採用黑白膠片拍攝。當時國內已經不生產黑白片,要從美國柯達訂購5222膠片,每次攝製完用專機從陝北送到北京,而後透過定期航班送到澳大利亞悉尼,洗印完了再送回來,可以說是大費周章。第一批樣片回來,洗出來一看,簡直有種緞子般的影像質感,全組人激動得都流眼淚。
在我看來,黑白未嘗不是一種色彩。首先,做出這個決定是從真實再現歷史的角度來考慮的。彩色片對物質現實的再現已經達到了非常完美的程度,但是,20世紀40年代在我們記憶裡沒有留下任何彩色。世人能夠看到的真實記錄著那個年代的資料,照片也好,影像也好,都是黑白的。如果我們把它濃墨重彩地搬上銀幕,很可能會造成一種“間離”效果,而不是一種親和的效果。選擇黑白片就是為了能夠在最大限度上讓觀眾認同這部影片的歷史感。
其次,電影在當年五月至七月在陝北拍攝,劇本所反映的是1943年夏到1944年秋這段歷史,在場景上,冬夏雨雪都將有所涉及。拍成黑白片對處理劇中場景和實際拍攝環境之間的矛盾有很大幫助。
六月時節的陝北高原,比照冬天大地一片溝壑縱橫的蒼涼,不太能反映黃土高原的地貌特點,沒有冬天時地貌的那種震撼力。另外,那時退耕還林,黃土高原上到處都在植樹,但樹林還未成氣候,於是黃綠參差,看上去也不好看。選擇黑白片,就避開了今天我們所看到的這種黃綠色彩參差不齊的感覺。
黑白片的運用絕不是簡單的“遮醜”,各個部門要在有限的時間內力求在每個細節上下足功夫,包括對演員的選擇、大量服裝的做舊、在黑白片中的特殊化妝等等。此外,拍陝北、拍延安一般來說都會用到很多類似標識性的東西,比方說:信天游、爬山調、陝北的秧歌、安塞的腰鼓、寶塔山、延河水等等,這些都要儘量迴避,因為都有“標語口號化”的嫌疑。
我們怎麼去拍?如果你只寫一名八路軍戰士在編草鞋、在燒炭,影片的格局恐怕就無法達到現在的高度。當時我花了一個星期,沒拍劇本上的一個字。拍什麼呢?拍的是大練兵,識字比賽、紡線比賽,沿著延河邊跳芭蕾舞,由此營造了一個生龍活虎的革命根據地,這個氛圍或許和電影主題沒啥直接聯絡,但它讓你要表現的人物生了根。
明代畫家石濤提出過一個美學觀點,叫做“搜盡奇峰打草稿”。老百姓也有句話,“牙縫裡面搜芝麻”。什麼最香?吃慣大魚大肉它不香,前天吃了個燒餅,一粒芝麻塞牙縫裡了,過後咂摸出來才香,最有回味。所以要去啃資料,不是去啃那些“大路貨”,而是要在那些不起眼的地方找出對拍電影有用的東西來,這叫“文似看山不喜平”。
貫穿道具“大紅棗” 《為人民服務》全篇講夠5分鐘
強調歷史感的同時,我們也不拒絕當時的數碼特效。影片中有一個貫穿道具“大紅棗”,成為細節有意地一次次重複:從第一場戲毛澤東看演出,就和朱老總抓紅棗吃;張思德認老炊事班長,“我就是你兒子,你就是我爸爸,延安就是咱們的家”,炊事班長很感動,取出一把紅棗;張思德去看戰友時,揣著一把紅棗;張思德到延安魯迅藝術學院去向炊事班長拜年,也是在炕上抓起一把紅棗來。
紅棗這個影像或者是拿棗的動作,在當時的延安已經是一種象徵:一提到陝北,“黃米的油糕,大紅的棗”啊。直到張思德犧牲以後,老炊事班長從兜裡抓出一把棗——這時,棗子變紅了!
有人說我這是模仿《辛德勒名單》中的那個穿著紅衣服的小女孩。其實斯皮爾伯格也是借鑑前人的經驗——愛森斯坦拍攝《戰艦波將金號》的時候,既沒有彩色膠片也沒有數碼特技,為了增強影片表達力,愛森斯坦完全是依靠手工把膠片一格一格染紅了。這說明傳統的東西一旦用好了,在今天仍然能煥發出藝術表現力。
1943年9月8日下午,中共中央直屬機關為張思德舉行追悼大會,毛澤東參加了追悼會,並發表了《為人民服務》的著名講話,高度讚揚張思德“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精神。影片到這裡,開始用彩色膠片呈現。
在關於該怎麼表現毛澤東的演講上,是不是要把《為人民服務》全篇演講一遍?有人認為電影之前都在追求平實的色彩,最後卻讓領袖滔滔不絕開講,會不會有點不搭調。我不同意這個說法,電影《巴頓將軍》的開場形式感強不強?喬治·斯科特邁步走上臺,光是亮相擺造型就有1分鐘,戰爭動員嘚吧嘚,講了整整6分鐘。巴頓在影片剛開始就敢講,咱們這片子到在快結束的階段,讓毛主席敞開講上5分鐘,當然未嘗不可。
這裡面其實是對觀眾心理學的研判,可以理解為一種欲揚先抑。前面大段的鋪排都是在幫助觀眾積累一種情緒:張思德是個什麼樣的人?哦,不過如此。哎,他不一般。唉!可嘆……人都犧牲了,電影就這麼完了嗎?要知道到這一刻,觀眾對於張思德在感情上已經難分難捨, 這就像一壺快要燒開的水,再添一把柴,才能咕嘟咕嘟地冒泡兒,毛澤東的長段演講正是觀眾心聲的直接傳達,恰到好處。
演講結束,操場上的人們漸漸散去,銀幕上獨留下一個小戰士在打掃——雖然張思德走了,但像張思德一樣平凡卻精神高尚的人到處都有。
責任編輯:張喆
校對:張亮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