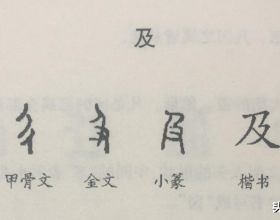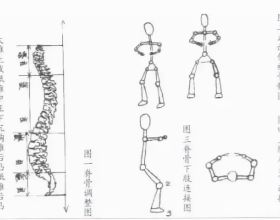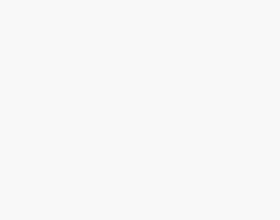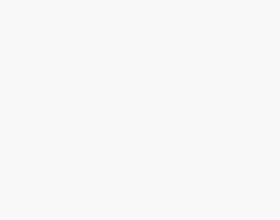白雲蒼狗,風朗氣清。
平江府南面,有宅數畝,門廳開闊,門前沒有威武的石獅,卻有一位著青布衣的僧人。僧人衣著簡樸乾淨卻不甚將就,此刻正在一顆蒼翠樹下打坐,手拄禪杖,唇齒開闔,似在輕誦佛號,跟前還有幾個嬉鬧頑童,正一臉稀奇的瞧著他。
微風吹響禪杖上的銅環,清脆叮咚,僧人驀然睜開眼睛,驚得那幾個孩童羞跑開來,唯有一個粉雕玉琢的男童還痴痴的望著他。
“小施主為何還望著貧僧?”青衣僧人笑道。
“看你枯坐在此,怕你無聊,因此盯著你。”男童也不怕生,囔囔答道。
青衣僧人道:“貧僧在等一個人。”
“什麼人?”男童撲閃著黑白分明的眼睛道。
“一個叫復的人。”
男童疑惑的抓抓頭,說道:“竟與我同名,怪哉”
青衣僧人聞言而動,站起身子抖抖衣襬,向男童施了一禮,便作勢要走。
男童忙問:“何故要走”
青衣僧人答道:“人已找到,貧僧故不久留了”
青衣僧人與男童對視一番後,眼底流露出莫名的含義,沒頭沒腦的開口道:“人生匆匆,輪迴幾多,難免出現相似的花朵,只是這花朵究竟何時才能開放何時又會歸於凋零,小施主要把握住呀。”
男童還在低頭思索之際,僧人大步流星,行色匆匆而去,轉眼便消失在路的盡頭,唯聽其高聲誦道:
情緣如草似飛蓬,雲端高處早回宮。
省卻紅塵多歧路,復走人間只為儂。
……
這是年幼的復第一個見到這個古怪的和尚,下一次便是十年之後了。
這一年復十五歲,恰似尋常年紀,性跳脫,喜活潑,不服管束。
七月初七那日,平江府內華燈初上,一年一度的乞巧夜市喧譁熱鬧,復身在屋內,卻隨著外界的歡鬧聲被牽走了心神。是文也難念,書也難讀,躁動難安之下索性翻出牆去,臨行前取來面具一塊戴在了臉上,乞巧節也是情人相會之日,帶上面具之人不在少數,也就不足為怪了。
他手搖摺扇強作鎮定,左顧右盼下閃入人群之中,要說這復,年不過弱冠,眉眼稚嫩,身型卻頎長勻稱,讓人看不出具體年紀。
他四處逛逛,見萬家燈火下游人如織,或是纏綿悱惻,或是共享天倫,或是高聲叫賣,或是吟詩作對。舉頭望去銀漢迢迢暗渡,璀璨萬千。
復好奇的穿梭在人群之間,忽聽得聲聲脆響,周遭隨機萬籟俱靜。復寒毛倒豎,之間人群中一位青衣僧人拄杖而來,四周熙熙攘攘,但在復的眼中此刻只剩下那僧人和他手中的禪杖。僧人大步流星,從他身邊路過,沒有絲毫停頓。
復許久才會回過神來,向僧人消失的方向追去,卻已無半點蹤跡。
這時他路過一片花燈,姑蘇乞巧節時有風雅之人舉辦燈會,以詩詞會友,在花燈之上寫上前句,路過之人但有對上的即可填上下句,主辦者會在乞巧夜市最繁華的地方將其中的良詩佳句張榜公佈,受人瞻仰,以此比鬥。
復驚魂暫定,隨意捉來一隻,卻見粉白色的花燈上娟秀的提著兩行字:
寥落銀弧撒江天
半扇孤月何處眠
復嘖嘖幾聲,見其詩風苦愁,只道是哪個落魄書生,不由起了勸慰之心,思索片刻,提筆而上,筆法蒼勁,沾紙無悔:
莫憂人前無知己
天涯處處共嬋娟
復滿意的看著自己的大作,餘光無意一瞄,見人群中有個嬌弱的姑娘,愣愣得望著他,也不知有多久了,見他察覺忙轉身跑開。
“怕我作甚。”復想要追去,又考慮影響不好,只得帶著疑惑留在原地。
他摸了摸鼻子,突然想到了一個可能,這個可能讓他也不禁啞然失笑,遂邁起步子走入遊人中去。
一晃月明星稀,但遊人卻未散去,繁華交匯之地有一座思婆橋,花燈會評選出來的優秀詩篇盡數的掛在這兩邊橋幹上。
眾人你擁我擠間,卻見一小個姑娘一掃嬌弱,順著橋幹一一看去,是前也看了後也找了,一無所獲,最後她停在某處橋幹前,終是垂頭喪氣的搖搖頭。正待轉身之際,耳畔傳來一聲低語,讓她渾身炸毛:
“為何躲我?”復的聲音溫柔而來,他立在姑娘身後,有力的手臂從她肩旁越過,手裡提著一盞粉白色花燈,輕輕得掛在了那個空蕩的橋幹上。
姑娘急忙回首,卻感受到了復身上散發的暖熱,臉頰不由緋紅,連連後退。
“我我……我不識你,躲你作什麼?”姑娘強辯道。
復失笑,見她身穿碧色輕衫淺白羅裙更顯嬌小不由愛憐,雖此刻他還不知道愛憐的含義,但也有兩抹紅雲飛上臉來。
“姑娘贖罪,小生莽撞了。”復忙退開,卻又壯著膽子道:“我見姑娘花燈上詩文極好,想與提者引為知己,見你行色古怪,便猜到你的身份,故提前在此等你。”
“我叫芸,他們都叫我芸。”
讓複意外的是,那姑娘並未怪罪與他,反倒對他報以淡淡的微笑。
“引為知己有些誇張,但你若是願意,你我可為筆友,近日我可能前往虎丘遊玩,屆時將在劍池題字,你有興趣可去瞧瞧。”說完那叫做芸的姑娘紅著臉跑下了橋。
……
復第三次見那僧人,是在他與芸的大婚之前。
自七夕巧遇已過去數年之久,復此刻身姿越加挺拔,早沒了少年時的那股稚嫩,唯有佳公子般的氣質。
這一日,他於亭中獨酌一杯美酒,卻見天地忽靜,他似察覺到了什麼,再看之時那個熟悉的青衣僧人已然落座在他面前。
“不請自來,可不是大師的做派。”復淡然處之,這些年他早已沉穩了不少。
“我最近這些日子總是會想起你,你可是我幼時那個古怪和尚?”
青衣僧人道:“然也。”
復說道:“你不是尋常人,何故總是叨擾我這個凡人。”
青衣僧人仰望天宇,悵然說道:“你此生註定要遇到我四次,這是第三次,雖然我希望是最後一次。”
“何解?最後一次相遇會發生什麼。”復皺著眉頭,又飲下一杯。
“酒有何滋味,能抵得過你所要品嚐的人世歡喜悲傷嗎?”
復猛然起身,亭軒帷幔飄飄,哪還有那僧人的影子。
……
復滿腹的心事,還是在嫁衣紅裝與滿屋賓客的祝賀中被逐漸淡忘。
往後數年,復與妻子芸相敬如賓,情深意切,時而滿月下對飲,時而名勝處放歌,夫妻情濃似蜜,彷彿是擔心情深不壽,又好像是唯恐自己獨佔的太多,某次芸怯生生開口,想要為復添一房妾室,復自然不允,反倒用寬厚的手掌落在她的頭頂,自上而下撫過她的髮絲,帶起一片幽香,隨後復將她攬入懷中,勸慰道:“天邊的孤月已經不孤單了,何必再要一輪皎月呢,我願意做一片群星,始終拱護著你。”
然而命運並未始終偏袒於他們,這一年芸懷有身孕,復行商在外,約定等他回來後便為孩子取個好聽的名字,兩人三日一箋五日一信,從未斷過,竟突然緲無迴音,復生疑惑,連忙歸家,再見之時卻是陰陽相隔,滿目紅綢換白幡。
復一瞬間蒼老了許多,他手捧著芸的衣物,在椅子上縮成一團,耳邊聽見來往賓客說道“溺水”云云,“溺鬼”云云。他的心揪得更深了,他哪裡不知,妻子最後一封信裡說道,她將前往他們看月之所,對著天空之滿月祈願他平平安安,而那處地方邊上就是一處水澤啊!
這一夜復獨自為芸守靈,實則是家人見他癲狂不敢與他交往而已。他披著頭髮,踏著赤腳,一頓一慢的敲著缽盂,眼底都已哭的渾濁,此刻只剩下噓噓的低訴聲。
“你可願,為她赴死?”青衣僧人來了,他複雜的問道。
“我願意……什麼我都願意。”復猛然抬頭,面目潦草只剩下苦痛的折磨,他眼帶血絲的嘶吼著。
“你能用四十年壽元換她二十年復生,你可能活不過四十歲,你願意嗎?”
“我願意。”
“來生芸會因為償還你今世的付出而早夭,你 願意嗎?”
“我……我不需要她還我。”
“這是天意!天意不可違!”青衣僧人一掃淡然,猙獰喝道,彷彿在提醒復,又好像在提醒自己。
“我一定會讓芸脫離苦痛,無論自己沉淪多久。”復早已跪伏下來,以頭觸地,磕出一個個血印。
青衣僧人雙手合十,低聲道:“命運難改,不知何時才能超脫。”
……
沒人知道那一晚發生了什麼,只知道府中的大少爺復失蹤了,連帶著他妻子芸的棺木也空了。兩個人好似人間蒸發一般,世人皆傳言:復公子悲痛過度,失心瘋了,帶著妻子的屍體去投湖殉情去了。也有早起的更夫說看到復牽著妻子芸的手,兩人依偎前行,芸狀若活人,而復則披頭散髮,眼中卻明亮無比,兩人往南去消失不見了。
一晃數十年過去了,復與芸入深山結廬隱居,終是到了大限之日,復和芸似乎早有預感,早上兩人犁地織布,中午復親自下廚做了一桌好菜,夜裡星空璀璨,復與芸手牽著手望著月亮,訴說著一件件往事,許久復覺得身上輕飄飄的,在看芸早已沒了氣息,他把手握得更緊了,低頭吻在了芸的髮絲上,說道:“睡吧睡吧,我的芸娘子,路上等我。”
隨後他也滿足的合上了眼睛,他的思緒好似一下飛到雲端去了,在那裡他做了一個夢,夢裡還叫復,是個莽撞書生,再見芸時他發誓非她不娶,再後來他們遊山玩水夫唱婦隨,再後來他們同甘共苦不離不棄,再後來芸娘早夭他則隱入空門,再後來他得道明悟,他披上青色布衣行走人間,復看著那個熟悉的僧人的面孔慢慢與自己重合,心中終是瞭然。
不知何時,夢幻終醒,他睜開眼睛,卻見一個粉雕玉琢的男童痴痴望著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