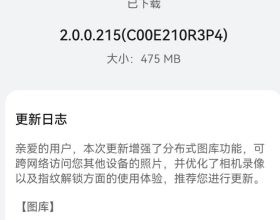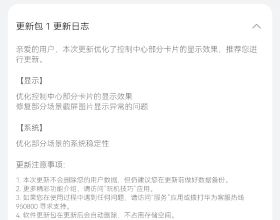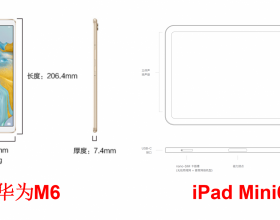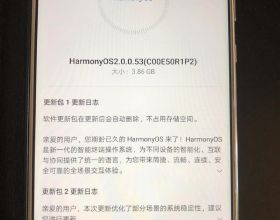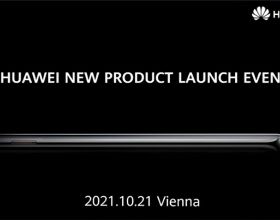文/陳啊妮
“此在”的語言效力與推衍
詩人梁平的詩歌對傳統文化屬性的觸控呈現精神形態的大氣象,也在內部思想縱深交錯某種異質混成的詞根效力,即他關注的是生命、靈魂以及世界的本質性命題,他所著力勾勒的是融合哲學、詩學與傳統精神渾闊的精神氣象,在其中蘊含豐富和龐雜的思想體系,新穎又鮮活,獨特又厚重,充滿一種純粹的打磨思想和相對完善的詩歌藝術。
在梁平創作的歷史時間長河中,幾十年如一日孜孜不倦地筆耕不輟,他以前輩詩人難得的進取精神,葆有了可貴的熱情和執著的堅守。如果詩歌作為一種理念的感性凸顯,其目的並不是將所見所聞的物象塗抹在紙上。對梁平而言,就是他所追求的是“此在”生命和生活裡物象承載的內部靈魂,並以此擴充和加深自我的語言經驗,來展示和澄清某些不可言說的存在之思,並在傳統的意義加持某種思想情感的互融、共情和理解。如《蒸發》中,“蒸發”的意義在於一種緩慢揮散和最終的了無,在詩人的筆下,他趨同於文字視角的思想色澤附著,而這種色澤附著又趨於從文字情感與架構性走向。在縱向情感領域,詩人凝注的“此在”頗具共時精神價值。詩人嗅到的語言氣味,自帶一種覺知感。
“而我/所有的看家本領/只能在紙上行走”,毋庸置疑在詞根的線索中,梁平安插了嶄新的生命經驗,以及用他的智識學養指認一種詩學向度的生命體驗。在他的詩中,象徵、修辭、隱喻和比興,都力求穿透物象的靈魂。他的詩歌《投名狀》《水經新注•嘉陵江》《我是我自己的反方向》《爆破音》等,無不體現一種抽象的、孤勇不屈的靈魂詩者的決心和覺醒,在日常瑣碎的生命體驗中,不斷鞏固和夯實詞根的情感“重力”。
歲月如歌,生命如風,那些櫛風沐雨的生活,首先回饋給梁平的是苦難之思,是逆行者的題材剔除。詩思的闊域性定位,在梁平而言,只有更多地投入注目當下和此在的生活,才能撈出骨頭連著血肉的鮮熱詞根。他始終對消極和浮躁有著天然的排斥,在他的語言座標系中,直覺、理性、警覺和慈悲,都帶有某種智識的輝光。他從不以任何理由貶損人生和生命,讓詩歌的骨頭挺拔,絕不騷首弄姿,也是一種接納傳統,包容當下和理解共情的詩者大義。
如《反轉》中,具體到“反轉”的具象承載,詩人呈現出事物真正意義的輪廓,這種反轉的意味在整體詩歌文本里可以瞬間傳遞出主旨詩意,對於“風”在文字上的作用和原始主宰者還是有所偏駁的。詩人用生命的直覺臨摹世相悖論,也有了一種反諷藝術的填充,而正視現實境映,亦是詩人真實面對自己的詩學心態。
在生命現場尋找語言的“出路”,永遠是高明的寫作方向。從《時間筆記》可窺其詩學之思想豹變,當時間的“在場”具有生活的特質,承載精神的潛意識觀照,那麼詩人就除了用眼睛洞察之外,在用心打量審視的詩學半徑就有了雙重的生命經驗。
“我睡在一張紙上/夜色調的墨不是黑/睡在紙上留下的痕跡/都拼接成漢字/清瘦/飽滿/或者殘損/那是我一生健全的檔案”《一張紙上》。在時間的紙上在場,詩人用極具抽象的隱喻進行了細膩的描述,這些表象的特徵在詩人抓住它們的精神核心時,“復活”了它們跳動的心臟,這是語言行使的巨大效力。
“我在紙上的一詠三嘆/被自己珍藏”。顯然,梁平始終在控制一種自由精神的揮發力,他沒有受制於現實的桎梏思想,在“紙上”落地於一種形而上思想的推衍和進化。在詞根的鞭撻下,用語言刨得一念之間的覺醒詩思。他用心遵循傳統審美,也用語言落地執行於精神象徵。
語言向度與傳統互融的隱性寫作
梁平的詩歌策略以修辭的嚴謹,隱喻的活脫和意義的超負荷而凸顯其詩學向度的鮮明。他似乎有著天然的孤獨、沉鬱和對塵世深深地隱憂,在他的字裡行間常常彌散一種動盪中的感傷和悲憫。而恰恰就是那種悲憫直抵人心,垂直地落地於精神共顫與警覺,“很多意外猝不及防/生活裡好端端的瓶瓶罐罐/七零八碎/一片破碎的玻璃/在滴血/我檢查了全身沒有出血點”《意外》。他可以把生命深度體驗的孤覺摁進傳統詞根的骨血裡,那種深刻的孤獨,凋敝的疼痛與直覺互融滲透,把人的精神不斷空間化,把空間亦不斷人格化,衍變成為一個用語言強化了的“生命的內心”。
這是複雜的情感體驗,在人間值得中多少有些降溫的悲憫之意會,可生命蒼涼無常的本質即最真實處境的語境,而直面慘淡的真實需要詩歌造就耐人尋味的意義褶皺,就如詩人所言“我知道傷在哪裡了/不能說”。
與萬物和解,與生活和解,用語言的治癒性效力清醒並決絕。詩人在生命深度體驗中,用清晰的邏輯描述人“此在”物象的心理狀況與空間狀況的碰撞,以及交錯後形成的巨大孤獨感和悖謬式的抒情,好似一個完整的思想三級跳過程,有一種深入淺出的思想抽離感。詩人在不經意之間用隱性的抒寫、誠實的語言向度裸露出情感中的深沉、痛楚的一面。
從梁平的生命視角意象探幽,詩人對“薔薇”似乎有著情有獨鍾的喜愛,在語言觸碰到意象“薔薇”也散發天然的精神體香。如《野薔薇》中,文字的“野”在不經意間得到有效匯入,這種匯入恰恰是在平靜中得到渲染的有四兩撥千斤的力量,同樣也構成了詩歌的張力。誠如平靜之下一顆叛逆的心。
而在《狂風大作》中,詩人所羅列出的“狂風大作”很大程度上趨於非常理構建的精神家園,及內在與外在不斷演變且具有矛盾、衝突從而讓裂變的思想得到慰藉,當然它是在詩人的見證之下成型的。在《顏色》中,從“陽光”到一個人的眼睛這種轉變的過程,其實它源於精神上的轉變,當然它在反襯與外界的過程中得到原始的“捕捉”,而薔薇藤的存在是一種情感的踐行與落實。
而《絕句》中,在這裡詩人所陳述的“天意”並非是傳統上的解釋,而是從傳統延伸出的一種新的含義,當詩人所勾勒的場景的轉換與“天上與地面”產生某種呼應時,詩歌的主旨思想也就無間斷滲出。
這幾首詩歌,梁平無一例外地帶有某種悲憫主義色彩。他運用簡樸精煉的冷抒情,又充滿溫柔、冷酷或神秘的精神意境淘洗詞根,他用沉痛的靈魂呈現一種理性或非理性的隱憂和渴望,在隱性的生命經驗中提煉詩歌藝術的高維思想,這也讓他的寫作有了與詩人穆爾類似的正視現實的無畏精神氣象。
“每一個時刻都有斧鑿的痕跡”,用生命經驗行文,以生命視角開啟語言審美,與暮年詩人米沃什的沉鬱慎靜同構思想價值等同,梁平在傳統與現代詩語之間互為觀照,也不斷抵近某種沉穩平和之生命詩學意境。儘管“每一寸光陰都不能生還”,而詩人的本職就是揭示生命的本質,正視生命深度與現實矛盾的殘酷真相。
詩歌已然已經成為粱平精神的圖騰,摒棄浮泛之詞,對傳統審美的文化屬性的準確把握。詩人清醒的生命哲學詩思,語言審美向度和精神內視洞察,或許在其不斷跋涉的詩歌思想征途上,不能用我們俗常的片面的理解去考察之。
【如果您有新聞線索,歡迎向我們報料,一經採納有費用酬謝。報料微信關注:ihxdsb,報料QQ:33864057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