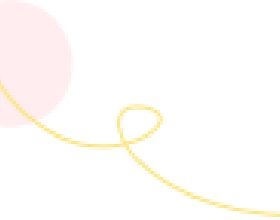踏出房門
這天下午,我不再穿印有初音未來的T恤。穿一件紫色襯衫,釦子繫到最頂上一顆,我開始準備一次影片面試。長髮留了半年多,長到肩頭,亂糟糟的,原本我打算在腦後梳個辮子,最後想想還是算了,把頭髮剪短,修出劉海,用髮膠簡單打理了一下,顯得整齊。
三點鐘,面試我的人讓我再等等,說還要除錯相機裝置。“這麼正式嗎?”我心想,我面試的,只是一家相機體驗店的店員而已。要不是我媽給我下了“最後通牒”,對我不工作這事忍無可忍,我會像往常一樣,找個藉口推脫,可能是“我不懂相機”。
幾天前,我二舅把這份工作的訊息告知我媽。十年來,31歲的我被視為“家族之恥”,畢業後一直沒有找正式工作。親人和朋友,叫我“啃老族”的不少。
每年過年,親戚們都會催促我找工作,我每次都敷衍過去,說自己在學日語、雅思、考導遊等。我不想多費口舌。這成了一個固定的“節目”,大家聊著聊著,氣氛就突然安靜了下來,沒了聲音。我抬頭一看,所有人臉都黑了。
那天我媽下班回家,告訴我這家店在招工,叫我給這家店投份簡歷試試,我下意識地說“不去”,就這麼不小心點燃了我媽的怒火。
“你想吃我一輩子嗎!我死了你怎麼辦!”我媽歇斯底里地怒吼,摔門而去。我不為所動,繼續躺在床上打遊戲。
十年間,我和我媽的關係時好時壞。有時我們推心置腹,聊人生、情感,無話不談。我和她分享我瘋狂迷戀上虛擬歌姬“初音未來”的諸多事情,還和她跑到日本看過一場初音未來的演唱會,教會她打Call、給初音未來應援。我為了追初音未來花了快35萬元,大部分錢都是我媽支援的。
只是,有個在家啃老十年的兒子,想來我媽面子上還是會掛不住。因此,三天兩頭,她會在心情不好時把氣撒在我身上。大部分時候,我都不會搭理,或者敷衍地說:“我不是在學日語、雅思嗎?”儘管,我很清楚我並非專心致志地學日語和雅思,也沒有認真地找過工作。
激動時,我媽會砸家裡的東西,甚至哭著給我一巴掌。我不能還手。只有無法忍受的時候,我才會跟她對罵。我深諳刺痛她的方法,用一句話就能揭開她的傷疤,卸掉她的氣焰:“我最困難、最痛苦、最無助的時候,你在哪?”
我六歲那年,我媽堅持跟我爸離婚。她一開始沒帶上我,讓我跟著我那沒有穩定工作的父親生活,我也因此體會到什麼叫做朝不保夕的生活。直到我12歲這年,父親失蹤了,才不得不跟著母親生活。
往後的二十多年間,我都憎恨著我媽。在我看來,是她讓我一下子失去了幸福的生活和圓滿的家庭。她也很愧疚,想盡辦法彌補我。這也是為什麼,她能忍受我在家啃老十年之久。
在這方屋簷之下,我們互相取暖,也互相傷害,擰巴地生活著。
三點一刻,影片面試終於正式開始。面試我的其中一位是門店的負責人,如果我拿下這份工作,他就會成為我的頂頭上司。看著影片訊號裡的他們,我有些緊張,因為在我看來,他們都是知名大公司的白領,而我只是一個躲在家裡的宅男。同時,我生出一種莫名的感受——這場面試可能是我人生最後的退路。我還生出了一種想抓住它的感覺。抓住了它,或許就是我走出房門,結束十年啃老的契機。
面試繼續,他們問我先前做過什麼工作。我回答說,先前,我在學校裡做過一份實習,2015年的時候,還做過兼職導遊。後來我打入了初音未來元祖粉絲內部,還給初音未來的官方及同人活動做過策劃和商務。作為一個31歲的求職者,這樣的“職場經歷”可以說與空白無異。因此,在寫簡歷時我用了些心思,重點描繪了我做活動策劃的經歷,期待面試我的人能看到我這些策劃經歷時,看到我在與人打交道上的某些天分和優點。
我坐在客廳裡,對著攝像頭回答他們的提問。我的身後,是大白天還開著頂燈的客廳。2015年之前,姥姥還在世時我都住在這裡。後來姥姥去世,我才得以搬進她的房間住。這裡存放著我過往十年的生活。
由於不用上班,我每天睡到中午11點起床。通常來說,我媽媽早已出門上班,桌上會出現她上班前給我留的午飯。十年裡,我正是在她這樣的照料下存活。
陽光照不進我們的客廳,不開燈的話,白天和黑夜在這裡沒有區別。事實上,我的生活也不需要時間感,一整天,吃、睡、看動畫、打遊戲,不參與團隊協作、不需要交付工作,沒有所謂“死線”,也就不需要知道自己身處白天還是黑夜。
一小時後,面試結束。我開始回想剛才是否有沒發揮好的地方。自覺還可以,我哼起了歌。或許,我可以告別過去十年的啃老生活了。
十年啃老的開端是2011年6月,我從北京一所大專院校畢業。大專三年我渾渾噩噩,逃課、掛科,每天的功課就是在宿舍玩PSP遊戲機、看動畫。畢業那天,我覺得好日子到頭了,拍畢業照的時候站在人堆邊緣,嘴角勉強上揚,笑得尷尬。
全班40人,只有我在家啃老,並堅持了十年。
畢業的前半年,海投簡歷近乎大學準畢業生的本能一樣,發生在每個同學身上。他們忙著到處面試,我的表姐在大學的最後半年參加了七十多場面試,是其中的典型代表。相比之下,我抱著無所謂的態度,投了三四封簡歷,參加了兩三場面試,最後都沒有了訊息。這可能跟我缺少足夠的實習經歷,和不如意的學習成績有關。在這之前,我只在一家手機品牌的校園俱樂部裡實習過半年。在班裡,我成績排名倒數,畢業時還補考了兩科。
回到家,我敷衍我媽說我在很努力地找工作,轉頭就把書包一放,躺在床上癱著。我當然憧憬成為白領,穿著正裝打著領帶,在人前風光。但我討厭跟人打交道,討厭團隊合作,因此害怕職場,總覺得它平靜的外表下暗潮湧動,些微不小心,就會把我捲走。
腦子裡一根絃斷了,一個念頭冒了出來。我決定放棄找工作,先回家待著。這個決定沒有讓我迷茫,反而給了21歲的我解放身心的感覺。
我不擔心我媽養不起我。在北京,她有兩套房,其中一套還是西城區的學區房。接受我的啃老,某種程度上講,是她決定離婚後,傷及無辜的我,理應給我的彌補。
2013年,家裡的親戚催促我去澳洲。二叔在那邊開了生意,想讓我去搭把手,幫他忙,也解決我的生計問題。我動搖過,開始學雅思,準備出國。第一次雅思考試,我只考了4.5分,加上因為一些口角,我跟二叔家的關係惡化到極點,第一次離開啃老生活的嘗試,就這樣夭折了。
為了掙點零花錢買周邊,2014年,我向我媽要了2000塊錢,花了兩個月考了個導遊證。隔年開始,每年暑假、春節我都會帶一下旅遊團,一個月掙3000塊錢,但這也是杯水車薪。為了收集各種限量周邊,我經常哄騙我媽的錢。在我眼裡,這本來就是該給我花的。我媽也不傻,發現不對勁後跟我叫板:“你別把我當傻子,錢都去哪了?”
2018年,由於我不節制地購買初音未來的周邊,演唱會也場場不落地追,我在各種網際網路信貸產品上到處借錢,最終背上了五六萬的信貸,無力償還。我才發現,原來自以為的瀟灑,其實不過是拆東牆補西牆的狼狽。這一刻,我深陷決堤般的無措。
在我家陽光照不進來的客廳,我哭著跪下來跟我媽坦白、認錯。她憤怒地讓我“去死”,卻還是借錢替我還了債。那是我第一次意識到,我媽面對我的啃老,其實也有無能為力的時候。
蹲在家裡啃老十年,怎麼躲開親人間的閒言碎語呢?平常聚餐時,親戚們都會催促我去找工作,讓我“找點正事幹”。每年過年,這也成了一個固定的“節目”。我總是選擇敷衍過去,用那套學日語、雅思、考證的說辭。我不想跟他們說太多,反正他們也不理解我。更沒必要和他們發生衝突,那樣只會讓我媽覺得更沒面子。
隨著我家裡蹲的時間越來越長,親戚們也懶得理我了。在他們眼裡,我已經“沒救了”。姥姥有時甚至說我“就像個殘疾人”。她更疼愛我二舅和表哥,但她沒想過,陪在她身邊的,卻是我和我媽。
有一次,姥姥在洗手間摔倒了,我把她扶起來,送到醫院。那一次,我媽問我姥姥說:“你兒子、大孫子在哪?你出了事,還不是你外孫扶你。”那之後,姥姥對我和緩了許多,把她對我表哥的愛,部分轉移到了我身上。2015年,姥姥去世前,跟我媽說:“你別操心,這孩子將來自個兒會懂的。”
其實,我一直都懂,也不像他們以為的那樣不自知、沒救了。在家裡蹲了一年之後,我開始重複地做同一個噩夢,在夢裡,我的牙齒掉光了,身體完全壞掉。像是某種暗示,我的體重報告開始出現尿酸超標、心律不齊等症狀。或許那個夢代表著在我的潛意識裡,其實覺得生活正和身體一樣逐漸壞掉。
我私下曾給一家線上教育公司、一家動漫遊戲公司和幾家自媒體公司投過簡歷,但沒有一份簡歷透過篩選。他們都挑剔我的學歷、工作經驗、專業知識,給我打了“不及格”的分數。
啃老十年,聽起來是一件不尋常的事——實際上也是。但我必須說,這個結果並非我一開始決心而為,只是十年來,我錯過了一個個離開這種境地的機會。
一開始,我只想躲回家裡,拖延幾年。後來錯失出國機會,又耽擱了幾年。最後,這空白的幾年成了我的求職硬傷,我的簡歷永遠會被卡住,並且一年一年地,愈演愈烈,我逐漸變成了一隻寄居家中的蟹,一次次縮回殼裡。當我意識到我難以離開我寄居的殼時,一切都太晚了。
面試結束第三天,這家公司的人事通知我,我被錄用了。
我不再是被刷下來的失敗者,拿下了人生裡第一份正式工作。
2020年11月16日,我入職第一天,也是我人生裡第一天正式上班的日子,內心五味雜陳。我免不了有點擔心能不能適應職場生活,也擔心自己對相機領域一竅不通會給我招惹一些麻煩,因此心情忐忑。
公司有兩個月的試用期,我媽時不時會敲打我,說:“不是試用期過後就一定能留下。”她還是擔心我在家待了十年,走出家門後還能不能改掉先前萎靡不振的狀態,去適應職場生活。
但我還能繼續往前走,因為佔據了我的內心的是另一種聲音:我想要抓住這個機會,證明我不比別人差。
每天7點多,我從家裡出門,在正式上班時間半小時前到崗。第一天,店長到店裡發現我早就到了,寒暄了一句:“呦,來得夠早啊。”後來,同事們每天見我都來那麼早,慢慢地也就習慣了,覺得我就是這麼一個人。冬天的北京很冷,有些同事難免遲到,但在實習的兩個月裡,只有我從沒有過遲到記錄。
“反正韓奕肯定第一個到,保證準時開店。”店長說過我。
早到崗不是作秀。我比其他人少了十年,更覺得在其他方面,不能輸給別人。
開啟店面後,我會先盤點相機、鏡頭,掃去展示品上的灰塵,之後開始打掃店裡的衛生。這是我入職後帶起來的風氣。一開始,同事們覺得我是多此一舉,覺得沒有必要天天擦玻璃,就連旁邊的店的人都認為我只是“三分鐘熱度”,在作秀似地表現自己。直到店長髮現衛生狀況確實有待改善,才開會要求所有人每天打掃衛生。
後來,我們直營店開了網路直播。作為店員,我們也被要求坐到鏡頭前,詳細、有重點地介紹各種相機機型。第一次直播時,我吞吞吐吐地介紹著,半小時後,已經說不出話了,整個人頓住,啞口無言。幸虧店長臨時進來,坐在我身邊接著介紹,我才逃過一劫。一旁的督導看到後,開玩笑說:“你們怎麼還換著來?”
直播結束後,窘迫的我打開了郵箱,才發現店長在上一週發了一份口播資料給我,它安安靜靜地躺在未讀郵件的列表裡。我已經記不起是我忘記這事,還是店長忘記通知我了。那一刻,我想得更多的是,如果我要保住這份工作的話,我還要學習更多、付出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