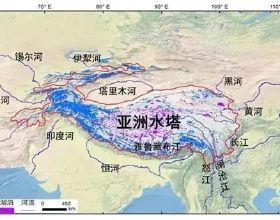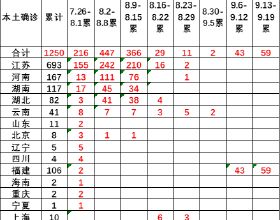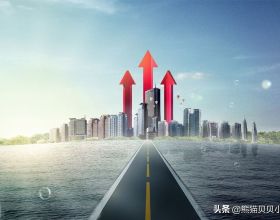南京大學文學院 許心瑩
2021年10月31日,按天干地支紀年,當為辛丑。是日天朗氣清,惠風和暢,“《文選》研究”課程的諸位師生以及南大臺港澳同學盡皆集合,前往南京郊野尋訪南朝石刻。南朝石刻之事前人已備記,餘因途中感懷眾多,略潤筆端,僅錄幾件趣事以寄縹緲之遊思。
烈日
剛下車,我便覺著一陣後悔:天太熱,我從未想到10月底也能有這樣的太陽,使身上的毛衣變作盔甲,鎖住全身的汗水。
藍天中掛著的明晃晃的太陽,那彷彿能把眼前悠久之物所代表的南朝的幽魂都蒸發開去,一切都是明亮的。在我胡思亂想的時候,童嶺老師早已介紹了眼前文寶碑的主人——蕭暎。他最重要的貢獻是提拔了陳朝的開國皇帝陳霸先(蕭暎做廣州刺史的時候,陳霸先做了中直兵參軍,是一個比較重要的武將,後來蕭暎去世後陳霸先扶柩回京,被梁武帝任命為交州司馬)。如果蕭暎泉下有知,不知是否會為這一提拔感到高興?
現在我們圍繞著的便是蕭暎的華表(石柱):柱頂的蓮花盤和小辟邪都已無存,柱子是希臘羅馬形的,下寬而上窄,中間還有一段汙水浸泡過的痕跡,柱礎是兩條盤龍咬珠——然而還是巨大,在烈日和陽光下,存著一股浩蕩的古氣。童老師又說因為附近是煉油廠,下的是酸雨,所以這華表上的字便愈見模糊了。去年他和魏宜輝老師來的時候,華表上還綁著木板保護。
我凝視著那磨滅的幾乎看不清的刻字,遙遙地又看見遠處晴空中煉油廠煙囪飄出的巨大的白煙。古與今交織在一起,催動了我的步子——該前往下一處古蹟了。
公與母
“這石獸是公還是母?”
不知是在場哪位同學誰提出了這個疑問。本來在蕭融墓石獸的雄壯的胸肌、吐出的長舌、雕刻的飛翼(有翼神獸,據說來自斯芬克斯)、有力的爪牙(爪前還有個小辟邪——本是華表上的,後被移動到此)等等遊移的視線不由地都聚焦到了某處地方,然後忽又受驚般地移開,彼此尷尬地一笑。
童老師卻大大讚賞這個問題:“…..2015年首師大《綜合的六朝史研究》會議上,日本中央大學阿部幸信教授認為神獸(即之前所提石獸)是分公母的,他觀察得很細,發現一些神獸有雄性象徵,而一些沒有……當時我擔任評議人,我的意見和他不同,我認為:第一,(鎮墓的)‘神’獸是不分公母的,第二,如果硬是要分公母,兩個一定都是公的。因為有史書記載,從清朝以來到建國之後,都有破壞六朝神獸雄性生殖器的記錄——當地的老百姓認為這些神獸夜間會作怪把村裡的女性擄走,一些強盜做的惡事,被他們認定到神獸身上……所以把這些雄性生殖器都敲掉……我們找到了這樣的記錄……”
眾人都聽得津津有味。我和一旁的好友也討論起來:我認為長久以來陰陽調和的思想,讓我覺得凡是成對出現的石獸都是一公一母;她也表示同意。
蕭秀、蕭憺、蕭景
接下來眾人來到了蕭秀墓神道處。映入眼簾的便是左右對立的四排石刻:兩辟邪,兩華表,四碑。童老師說蕭秀墓形制完整,並且是“五王”中唯一四碑共建的,由王僧儒、陸倕、劉孝綽、裴子野所作。可惜如今不是碑體不存,就是磨損不堪,只留下蒼白的“遺體”供人憑弔。然而可暢想四碑共建時的風流!魏宜輝老師又說這些石刻為集中保護而“屈居”在一所小學之中,當時間隔肯定不是那麼密。我拍了88年的文寶碑,趴在木柵欄上伸出手掌,假裝撫摸到了那石刻冰涼的面板。
接下來就讓我們跳過蕭恢石獸胸前撒下的捲曲的穗毛、蕭恢墓石刻文寶碑上曬地瓜幹“其樂融融”的景象,直接來看始興忠武王蕭憺的“南碑第一”:那石碑被緊緊地鎖在碑亭裡,僅能在縫隙中略窺探到些字影。據童老師說2013年的時候還只是鐵柵欄,還可以伸進去拍照,只是2014年被人盜拓,所以如今才被關在這“鐵屋子”裡。童嶺老師將那碑文吹得天上有,地上無,“僅就書法而言,只一個碑就把所有北魏的碑比下去”,弄得我們心癢癢。可是陽光實在太烈,根本聚不了焦。喪氣的我們只能把注意力放在同樣是文物的碑亭上:瓦當上刻著五角星,而牆壁上滿是“到此一遊”的“簽名”——讓人覺得鎖起來也是可悲的應有之義了。
之前損耗的石刻讓我覺得完整的石刻是再不可見了,蕭景的華表卻讓我大吃一驚——那實在是太精緻的漂亮——之前童老師說始興忠武王碑把北魏所有碑都比下去,我就要說蕭景的這個華表要把之前所有的華表都比下去。從上至下,小辟邪、蓮花蓋、柱身、柱礎都完完整整,甚至連上面“梁故侍中中撫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吳平中侯蕭公之神道”的反書都清清楚楚,反書下面的味獸也栩栩如生。在旁邊的避雷針建造之前(尖端放電),這華表竟逃過一劫,怎不讓人直呼是“天選之子”呢?
蕭景墓神道的辟邪也相當有名。南京大學校徽、南京電視臺的標徽,包括南京地鐵卡等等,都採用了這個辟邪的原型。只看它從胸前垂至腹部的美麗的蜷毛、線條流暢靈動的小翅膀,就知道這尊石獸的精美。
晚櫻
我想我一定要記錄發生在以上旅途中的一個插曲:那是在參觀完蕭憺碑,我們繞路去看蕭憺辟邪的時候,發現一旁的樹杈上開了幾點粉色的櫻花。眾人的拍照之熱情,絲毫不遜於拍各類石刻。有人叫著“反常”,又有人反駁說是“晚櫻”。我想這還暖的氣候確實助力了這脆弱花蕾的綻放。但人們擁簇著拍攝它的熱情與喜悅,一定是來自它的美。
——多美啊。綻放在殘缺石刻旁的、這小小的、新生的花朵,粉嫩得彷彿少女的唇彩。又是十月的天氣,暫且拋去對反常氣候的憂慮,與這幾朵晚櫻的不期而遇足以激起人們心中對自然的那份親近。
我也按下拍照的鍵鈕,把那份自然與歷史交匯的美永遠留存在手機裡。
獅子衝的主人
上午的最後一站是獅子衝。童嶺老師為我們介紹起此地的主人:“關於這個墓的主人,2013年的時候——在挖掘之前是兩說,現在是三說:在那之前說的最多的一種是陳文帝陳蒨的永寧陵,第二個說法是宋文帝劉義隆——我當時認為是宋文的可能性大一點;2013年考古發掘之後出了兩塊墓磚,‘中大通’‘普通’的紀年磚——初步認為有可能是昭明太子的墓……之所以是帝陵級的,是因為有可能昭明太子的後人所建立的後梁政權,把他的祖先昭明太子追封為昭明皇,所以它採取是帝制,即單角和雙角的石獸……
“所以到現在為止一共有三種說法:陳文、宋文、昭明太子。”聽著童嶺老師的講解,我們都頗有興致地圍觀起單角和雙角的石獸:飛翼靈動,舌頭上翹,胸口的回紋有別於諸侯王的四散,而成束狀垂下(狀若樹幹與樹枝),爪子如推球狀,尾巴由頭至尾、一氣連貫,而身上多著飛紋——這石獸雖然小,卻屬精美的帝制。“你們看這兩頭都是雄性,所以我認為:第一,神獸沒有性別,第二,如果有性別,兩個都是雄的……”童老師又補充說。
趁著大家自由合影拍照,我找到童老師請教有角獸的命名問題。“我同意日本學者曾布川寬的說法,他統一稱‘石獸’,‘石獸’就不會出問題,如果非要計較單角是天祿還是雙角是天祿,父子兩個(指朱希祖、朱偰父子)都有不同意見…..”“可是似乎也有統稱叫‘辟邪’和‘麒麟’的?”我問道。“你說得對。‘辟邪’是唐朝人對於南朝石獸的統稱,民間也時常叫‘石麒麟’的。但在單角和雙角哪個是天祿,哪個是辟邪的問題上,還沒有很確切的說法。”老師補充道。
關於蕭宏公園
“為什麼蕭宏的墓可以建成一個公園啊?他人品又不好……”
“這差距也太大了……”
我們走在蕭宏公園的石路上,看著建設完好的公園大發感慨。照我所想,蕭宏和其子蕭正德可謂南梁滅亡的“罪魁禍首”——再退一步也是“從犯”,死後石刻居然得到了最好的風景,甚至在其上造了個公園,而先前所看的有文治武功的蕭憺、蕭秀等等,其神道要麼在荒涼的郊外,要麼蜷縮於學校裡,保護也難說得上完善——不免讓我難以理解。
可能地理位置好吧……吃著午餐的麵包,望著美妙的湖景,我休息了一陣。正和好友聊著,恰巧看到湖對面的老師三人正坐在蕭宏的石碑前聊天。(那石碑側面的畏獸也極精緻。)
“快拍下來!”我以眼神示意好友。然而說時遲那時快,老師們已經發現了我們,正站起身往這邊走來——於是我們就匆匆忙忙地溜走了。
“不如無錫的湖好。”對著蕭宏公園裡的湖水,我最後留下孩子氣似的不屑。
草的喜劇
下午的行程是先去探看宋武帝初寧陵、然後是兩座失考石刻,再去看陳武帝的萬安陵。初寧陵倒沒有什麼好說的,只是過馬路要當心;麻煩的卻是失考墓和萬安陵:因為地處偏僻,通往石刻的路上滿是過人高的雜草,路也是草和泥混雜的路——我們需要“披荊斬棘”,才能找到那幾尊石刻。我因此稱這段旅途“草的喜劇”。
草的喜劇,自然是人的悲劇。在侯村失考墓石刻雜亂的蘆葦蕩裡,曾有同學發出“迷路陷密林,迷路多荒僻”“言語難表述,內心存餘悸。”的哀鳴。而在宋墅失考墓的建築工地上,魏老師也以身犯險,走到危險的架子上觀察被包起來根本看不到的石刻。我的好友,那更是悽慘,在萬安陵周遭的農田裡一腳踩進泥水,直把白鞋變作黑鞋,好在並無大礙。
歷經這種種“艱險”,我們能看到的也只是被土濛濛的玻璃罩住的石獸——那與我們上午看到的差不了太多,毋寧說,更模糊些。然而,在夕陽的斜暉下,聽著童嶺老師娓娓道來陳霸先與王僧辯、王頒父子的恩怨,仍有一種歷史的厚重浸入我們的靈魂。南朝的石刻往往豎立在路旁,不依山傍水,不躲躲藏藏,它隱入叢生的雜草,隱入泥濘的農田,隱入人們的日常生活。
——草的喜劇是南朝石刻的悲劇嗎?還是它們只是靜默在這天地間,不悲不喜?
餘暉
出發時正烈的太陽,此刻也繳納了它的餘暉。我們坐上了歸程的大巴。
我想:無論是劉宋武帝消滅南燕、後秦,收復洛陽、長安時的“氣吞萬里如虎”,還是普通年間暢想北伐的梁武帝的雄心勃勃,那不正如烈日般皎皎璀璨嗎?——然而侯景之亂,然而陳後主唱著《玉樹後庭花》的時候,那南朝的太陽,終究是落下去了。
於是我又想:南朝的風流便如南朝的石刻一般,也許永遠在那兒,在某個烈日之下為人們講述它們的故事,那太陽,是永遠都不會落下的。
責任編輯:黃曉峰
校對:丁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