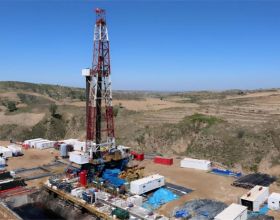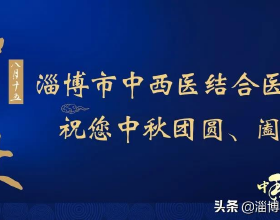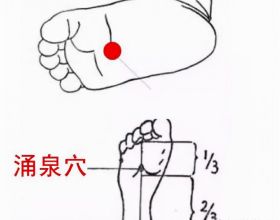杜衡原來住歆生路,那兒是蘇杭幫妓院的聚集地。老客們往那兒去多了不方便,杜衡也覺得原住處太逼仄喧鬧,這才有了這棟新宅。
劉松竹是心甘情願出這筆錢的。杜衡身邊雖有一大幫客人,可交情最厚的要算劉松竹。他錢多自不消說,還有點雅趣,筆墨金石、博弈笙簧都還談得來,更主要的是他有的是時間,藥店由帳房管著,只是在成藥下料時他才出面,那配方的劑量只有他一人知道,這是看家之本。有這三項,劉松竹可稱得上是消閒解悶的最佳角色。從劉松竹來講,時間一多人就無聊,自打結識杜衡,日子就過得快多了。
誰知姆媽這一病,攪得整棟新宅愁霧濛濛,看著形銷骨立的杜衡,劉松竹生出萬般惜香憐玉之情。
“杜衡,病慢慢治,總是能治好的嘛,何苦這般折磨自己?”
“邀梅,我的身世你不是不知道。我六歲時就被爹孃賣掉,是姆媽像親生女兒一樣將我撫養大,又請名師調教;有人打我的歪主意,她又捨棄蘇州家產,帶我來到此地。舒心的日子還沒過上幾天…… ”
“要說這病,也真是蹊蹺,好端端的,怎麼說啞就啞了。”
聽到這個“啞”字,杜衡的眼淚又往下掉。劉松竹慌得手足無措。“
“要不,我再去請位醫主來?”
“都是庸醫,我再也不相信了。”
“這棄愉可不一般,他是老佛爺的……”話未說完,他又後悔,打了自己一嘴巴:“哎,這張臭嘴!”
杜衡卻警覺起來:“邀梅,什麼事這麼神經兮兮的?”
“哎,到這一步,也只得走這最後一著棋了。”劉松竹似乎下了很大的決心,說出了這位醫生的來由:
“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慈禧太后腹瀉,太醫們什麼方子都用了,就是止不住,遂下旨徵召民間良醫。蘇州所薦者為王軫,年方三十。進京的一班人無不是工於岐黃之術、懸壺數十餘載的銀髯飄拂的老者,太醫院的院使、院判和御藥房的太監對他正眼都不瞧一下。可老先生們開的藥方全都不靈驗,只得讓王軫試一試。沒想到他僅僅請脈一次就探明病因,自己配製一劑湯藥,煎熟後分成兩小杯,自己喝一杯以示無毒,另一杯呈太后服用。幾個時辰後就見了效,第二天太后的飲食睡眠就恢復正常了,只是身體還很虛。
“太醫們自覺臉上無光,也不願讓王軫獨貪大功,便進了一個不痛不癢的補藥方子,以為只會強身不會有礙,哪知這劑藥一下去,太后上吐下瀉,通宵不息,只得又傳王軫。王軫又配製一方,才將這新症壓住。太后懲治了太醫,也不敢放王軫回南方,令他暫留京中侍奉。其時太后已完全康復,王軫已無事可做,無非每日進宮切脈後道聲平安吉祥,然後陪太后說上一會話,也就是民間趣聞、蘇杭風情。
固然恩寵無雙,可王軫的心早就飛回老家了,妻子懷孕七八個月就要臨產,他實在不放心。一天,他趁太后心情好就稟明自己想回家的意思,沒想到太后臉當時就冷下來:“女人生娃娃,你一個大老爺們能幫上什麼忙?”王軫再也不敢提,日子就這麼一天天挨下去了。太醫院的一幫庸醫對王軫恨得牙癢癢的,造出了太后與他關係暖昧的謠言,鬧得滿京城沸沸揚揚。王軫聞之氣得直打哆嗦,太后為人狠毒,喜怒無常,且年已七十二歲,齒落髮稀,避之唯恐不及呢。
“王軫終於獲准返家了,那是因為傳來了其妻難產而死的訊息,孩子根本沒生下來悶死在母腹中了。就這,太后還丟下一串話:“這女子也太沒福分了!得,去料理一下就趕緊回京吧。”
“據說王軫騎馬從正陽門出來後,回過頭朝皇城瞪了一眼,那雙目血紅血紅的,像要噴出火來。哎,就這一瞪,瞪去了他三十年的歲月,瞪去了他的滿懷志向、一腔熱腸。”
“他連老家也沒回,從此銷聲匿跡。兩年後,太后腹瀉的老病又犯,太醫束手,朝廷向各地下了加急文書尋他而不得。太后不治而死,死前坐在馬桶上還惡狠狠地念叨:“王軫該殺!”王軫隱姓埋名,東躲西藏,直到民國後,才敢露面,然而也得時時提防,皇族中的人和前清的遺老遺少想置他於死地的不少。他現在已不給人看病了,在這兒除幾位密友,別人都不認識他。”
“是條漢子!”聽完劉松竹的述說,杜衡露出神往之情,“你開頭提起他時稱什麼?是表字麼?”
“是的,字棄愉,出京後改的,原來字南星。”
“呵。真有情之士!”
“什麼?”劉松竹一下子明白不過來。杜衡也沒有細講。
“我能否請動他的大駕?”
“難就難在這裡,這傢伙死犟,不近女色,不貪錢財,不畏權勢,要知道是我漏了底,只怕要同我抹臉呢!”
“既然請不動,你提出來做什麼?”
“……罷了!我這張老臉不要了,去求他一次!”
“既懷這種心態,恐怕求不動。他住哪裡?”
“鬼知道!時而在洪山的寶通寺,時而在襄河邊的號棧,不過要找他也不難,只要姑蘇茶園裡開講彈詞,他一準到場。”
“就是秦老闆開的那家茶園麼?你去同他說,我過幾天在那裡開講《九松亭》。我唱單檔,叫他什麼也不用準備,只需在粉板上將預告寫得亮閃一點。”
“哎呀,我的小祖宗,你那麼樣一下子把天大的架子都坍了?這秦老闆怕要喜死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