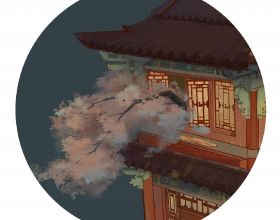山東省陽信縣有個老翁,家住在距離縣城五六里路的城郊,因為距離縣城有段距離,就和兒子兩個人在路邊開了家客棧,供來往的商旅休息住宿。其中有四個常年以幫人運送貨物為生的車伕,路過他家客棧會經常在這裡住宿。
有一天,太陽快要落山的時候,四個車伕又路過這裡,看馬上要黑天了就想在客棧住一晚明天在趕路,不巧的是今天客棧生意特別好,所有的房間都住滿了客人,沒有空餘的房間了。這個時候太陽已經落山了,天完全黑了下來沒法拉著車繼續趕路了,而且距離縣城還有五六里路呢。沒有辦法四個人就堅持懇求老翁幫著想辦法找個房間讓他們住一晚。因為是老主顧,天色也確實太晚了,於是老翁低頭想了一會,想到有這麼一個地方可以住,但又怕車伕們嫌棄住的不滿意。四個人說:“只要有個地方能住一晚不至於睡到大街上就行,什麼地方都無所謂。”原來老翁的兒媳婦剛剛去世了,兒子出去買棺材還沒有回來,所以兒媳婦的屍體停放在一個房子裡還沒有發喪。老翁覺得這個靈堂比較安靜,於是就帶著車伕能穿過巷子把他們安頓到了這裡。
進了房間,就看見靈堂的桌子上點著一盞昏暗的小油燈,桌子後面隔著靈堂的白布躺著一具用黃紙蓋著臉的屍體。又往裡走是間臥室,臥室裡有個能睡六七個人的大通鋪。四人奔波趕路一天已經很累了,挨著枕頭就睡著了。唯獨有一個車伕平時睡眠比較淺,迷迷糊糊的剛要睡著,忽然就聽見外屋靈堂的床上有察察的響聲,像有東西在動。一時間嚇的急忙睜開眼睛藉著靈堂前桌子上的油燈看的清清楚楚,就看見女屍已經揭開臉上蓋著的黃紙坐了起來,接著下了床,慢慢的向臥室走來。只見女屍面色金黃,頭上扎著生絲綢子樣子很是嚇人。就見她走到大通鋪前對著三個車伕的頭挨個吹了口氣,車伕嚇的大驚失色,急忙用被矇住腦袋,屏住呼吸豎著耳朵仔細聽著女屍的聲音。不一會,女屍果然走到他的面前象對其他三人那樣吹了口氣。然後感覺她走出臥室,就聽到抖動紙蓋臉的聲音。車伕慢慢的伸出頭偷偷的看向女屍,看見她還象原來一樣僵硬的躺在那裡。車伕更加害怕,又不敢發出聲音,只能悄悄的用腳踢旁邊的同伴。踢了幾腳旁邊的同伴卻一動也不動。車伕一看想著沒有別的辦法了,不如穿上衣服快跑出去。才坐起來拿起衣服剛要穿,就聽到外屋靈床上又響起了察察聲。車伕害怕嚇的趕緊又縮到了被子裡矇住了腦袋。就感覺女屍又走了過來,對著他的腦袋連續吹了幾口氣才離開。過了一會,聽到靈床上的聲音,知道女屍又躺下了。才從被子裡悄悄的伸出手摸著褲子穿上,光著腳跳起來就往外跑。這個時候女屍聽到聲音坐了起來,看樣子是要來追趕車伕。當她走到白布旁的時候,車伕已經拔開門栓跑了出去。女屍隨後就追。車伕邊跑邊大聲呼救,可是村子裡的人都睡得很熟沒有一個人驚醒出來救他。想去敲客棧老闆家的門,又怕這時候女屍追來來不及,於是就向村外縣城的路上極力跑去。跑到東郊,就看見路旁有個寺廟,聽到一陣陣的敲木魚的聲音傳來,於是急忙跑過去使勁的敲打寺廟的大門。廟裡的僧人聽到大半夜的有敲門聲不正常,不敢去開門。沒辦法車伕剛轉過身來,就見女屍已經追到離他不到一尺遠的地方了,車伕更加害怕。寺廟的門外有棵白楊樹,樹身有四五尺粗,於是跑過去以樹做屏障。女屍從左邊追來他往右邊跑,女屍從右邊追來他往左邊跑。抓不到他女屍非常生氣。就這麼左抓右躲的追趕著。漸漸的女屍和車伕都感覺很累了。女屍停了下來,這時候車伕也已經跑的汗流浹背氣喘吁吁的躲在樹後靠著大樹稍稍休息下。突然,就見女屍猛的一下跳過來,伸出兩隻胳膊,隔著樹抓了過來。車伕嚇的一下子躺倒地上,女屍沒抓到他,兩隻胳膊抱著大樹不動了。
這時,寺廟裡的僧人已經躲在門後偷偷的聽了很長時間了,聽見外面沒有聲音了,才慢慢的開啟門出來。看見車伕躺在地上。拿過蠟燭一照,已經死了,但是用手一摸在心口的地方還有一點點氣息。於是把車伕背到寺廟裡,過了一晚才甦醒過來。給他餵了些湯水問他怎麼會有女屍追他,於是車伕原原本本的把事情的經過和僧人講了一遍。這個時候天亮了,朦朦朧朧的能看見東西了,僧人來到樹旁一看,果然有具女屍抱著球僵硬的站在那呢,僧人嚇的大驚失色,趕緊派人去縣衙報案。縣官親自帶著人過來檢視,派衙役上前把女屍的手拔下來,可是女屍雙手牢牢的抱著樹身,衙役用了很大的力氣也沒把那手拔下來。縣官走上前去仔細一看,只看見女屍四個手指捲起來象鉤子一樣,沒過指甲深深地插到樹身裡了。又叫過來幾個衙役一起用力才把女屍雙手拔下來。就看她在樹身上扎的手指孔,就像用鑿子鑿的一樣深。派衙役到老翁家檢視,看見女屍不見了,那三個車伕都已經死了,周圍的鄰居正七嘴八舌議論紛紛呢。衙役向老翁說了緣故。於是老翁帶人來到廟前把女屍抬了回去。這時車伕痛哭流涕的對縣官說:“我們四個人一起從村子裡出來的,現在他們三人都死了,唯獨我一個人活著回去了,我怎麼和他們家人交代呀,鄉親們能相信我說的話嗎?”於是,縣官給他寫了一封證明信,又送了些銀子,送他回了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