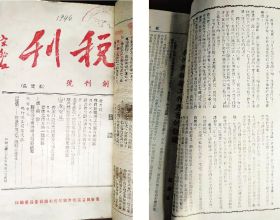包裹像流水一樣衝來。3 米間距,5 秒,張釗右手拿著巴槍,彎著腰,傳送帶速度很快,包裹一件趕著一件,只有 5 秒,掃描必須完成。而有的件還要翻個面,才能看到條碼。巴槍在每個面單上掃過,發出清脆的“嘀——”。
這是中轉場分揀出庫的最後一道程式,整個 6 月,張釗都在這裡做日結工。外面的虹橋航空區籠罩著濃重夜色,中轉場裡燈火通明,白晃晃的大燈刺目地照著張釗和他面前流水般的傳送帶。
最忙的時候,流水線上的包裹,橫衝直撞,張釗幾乎沒有抬頭的機會,他身形微胖,背心早已溼透,同時還有腳傷,用力很不方便。
“只能承受。”
“監工不時沿著滿場巡邏,正對著流水線上方,還有幾處紅外攝像頭,哪一個你都得罪不起!”
每天進場之前,勞務中介拿著大喇叭就說過,“一切細節都清清楚楚。”
張釗手裡的包裹來不及裝車,他隨手堆在傳送帶兩邊,“卡位上的件多到什麼程度?”
“超過 2 米。”
“托盤上堆的全是貨,老高了,能把我整個人給淹沒掉。”
倉庫內,五六米長的大風扇和繁忙的傳送帶,發出巨大的嗡嗡噪聲,張釗和整個流水線的工人都深陷在噪音的立體環繞包圍中,連說話都聽不清楚。唯一清楚的是機器的藍色警示燈,在巨大的噪音中突兀地以秒為頻率跳動著。
進場之前,兩道安檢,手機和手錶也被中介收走。張釗記得,第一次來這裡,完全沒有時間概念。又是晚上,常常根本不知道到了幾點幾分。有一次,汗水溼透,他很想知道多久可以下班,就去看牆上的電子鐘,好幾次後,張釗才恍然發現:不能一直總是 6 月 1 日 03 點 27 分。他估計那個鍾是壞掉了。
張釗穿著的藍色馬甲背心總透著汗溼,這份工作要求穿T恤、長褲以作保護。不同顏色的馬甲,顯示日結工屬於哪家勞動中介。張釗一直都是“軻通”的老客戶,每天傍晚他總是穿著那件藍色的馬甲進場。
張釗和倉庫
除了午夜一次放飯,整個夜班 12 小時,他不能停下手邊的活,沒有人接替的話,不能打水,也不能中途離開去上廁所。
一整月連軸轉的夜班,作為長期日結的老工,張釗最近也頻頻發錯件。下半夜的 1 點到 8 點,他要裝滿一整車加一個小車的上海同城。但上週,幾次架不住睏意襲來,“後半夜犯迷糊,發錯了好幾件。”
最近一次,高個子監工過來語氣平和地提醒張釗,“你老是發錯,我頂不住了,要不你別幹了。”
虹橋中轉場有兩個倉庫,與張釗同類的日結工,差不多 600 人,晝夜不停三班倒,他們承擔了物流自動化上的人工分揀。一個晚上,這裡需要完成 30 萬件包裹的週轉。
巴槍每掃描一個包裹,發出清脆的“嘀——”。張釗後來才知道,“嘀——”的一聲,系統會將資訊即時傳送到每一個寄件人和收件人的手機中。
“凌晨 3 點 14 分,快件已經到達【上海虹橋中轉場】,準備發往【上海黃浦區營業點】。”
有人收到這條資訊。那是因為在凌晨 3 點 14 分,張釗在上海虹橋中轉場的流水線上,剛完成了這件包裹的最後一道掃描和分揀。
包裹一件趕著一件,堆在一起,卡在傳輸帶上,隨後湧進的包裹,就噼裡啪啦地擠出了流水線。
阿柚慌了,這是她打日結工的第一個夜班。下午集合時,勞務中介把她和另外一個女孩分派在流水線上遊,工作是拉包,即把剛轉運過來的包裹,拉到另一條分揀線上。這裡是包裹進入中轉場的第一關口,經過層層分揀,末站分流到張釗那裡掃描,最後封車發往各個目的地。
此時流水線超載嚴重,一個被擠出傳輸帶的大包裹滾落下來,差點砸中了她。阿柚本能地躲了一下,急忙跳上更高一點的地方,向周圍大聲呼救。
瞭望塔觀測到了意外,廣播就突然在嘈雜的分揀車間內模糊不清地炸開:請xxx去 3 號線!請xxx去 3 號線!
穿著工作服的監工踩在 3 號傳輸帶上,迅速滑到事發地。他看了一眼坍塌下來的包裹,立即拿起傳呼機緊急叫停這條流水線。
第一次遇到這種情景,阿柚嚇得呆頭呆腦的。她穿著一件藍色馬甲,滑下來的一綹劉海貼著前額,眼神無助,監工掃了她一眼,然後就又粗聲粗氣地在對講機裡大聲呼叫:“這邊是女的在拉包!叫那邊打包的,不要打得太大!”
中轉場裡的女工很少。大概只佔 10%,其中做日結的更少。“雙十一”或 “6·18” 等旺季,快遞量成幾何倍數激增,中轉場人手需求巨大,日結工資也就水漲船高,這時中轉場也招一些女工,來補充缺口。
但 6·18 已過,日結的工資高峰轉眼跌落,男工都不願再幹。同時,暑期學生工大量湧進,市場供需翻轉,勞動力也變得極度廉價,13 小時的大夜班,僅僅 180 元。而之前 12 小時的夜班,有 220 元。
阿柚是河南人,今年 19 歲。半年前,她從老家來到吳江,想跟隨表哥在那裡找個工作。但整整半年,顆粒無收。後來,經人介紹,她覺得打日結工是個機會,做一天,工資秒結。
當天下午四點,阿柚跟著中介從 77 公里外的吳江上了大巴車,車子搖搖晃晃,阿柚睡得昏昏沉沉。
阿柚是第一次見到這種幾層的環形流水線,也第一次見到這麼空曠而繁忙的中轉場,3000 平米的空間,燈光如同白晝,機器轟鳴,包裹像流水一樣不停地飛速傳送。
起初,阿柚覺得很緊張,但還可以勝任,就是集中精力一刻不停地把傳輸帶上的包裹,拉到不同的分揀線上。
幾個小時之後,她發現自己的節奏漸漸地與傳輸帶上機器的節奏不一致。有的快遞件看上去很小,卻非常沉,她第一下沒搞定的時候,第二下再來搞,這時時間就跟不上了。
但緊張的節奏中,也有一些東西讓阿柚眼前一亮,一大串灰色的包裹箱子經過之後,晃晃蕩蕩地來了一個帶條紋的蛇皮袋,“畢業季的行李箱吧。”阿柚一看就很親切。甚至有時候還出現了一股香氣,三更半夜人困馬乏的情況下,就像穿著花哨的遊客一樣,接二連三出現一個又一個鮮豔的水果盒子。
“甜杏,葡萄,水蜜桃?應該還有芒果的味道?”阿柚拉包的時候,這些香味讓她感覺很愉悅。
後面來了一個藍色盒子,簡直讓她眼前一亮。她一眼就認出那是最近抖音上天天刷出的“得物”平臺的貨,阿柚刷到過多次,但一次也沒買過。
半夜 11 點,上半夜的最後一車貨物抵達,流水線上的工人們昏昏欲睡,卻又不得不打起精神來幹活。卸貨工人趕著休息放飯,動作飛快,從頭到尾不說一句話。
這是一車冷凍貨品,白色的塑膠泡沫盒,分量不重,件數卻很多,觸手光溜溜的。
幾分鐘,雪白的泡沫冷凍盒,從傳送帶的滑坡上瘋狂向阿柚這邊湧來。
“又要失控了。”她手忙腳亂。上半夜發生過一次過載事故,要是再發生一次,估計就麻煩了。
她想起小時候在河南農村,暴雨來時拼命往家趕的情景。阿柚身材嬌小,兩隻手拼盡力氣,從左邊搬到右邊。同時她還要牢記勞務中介的提醒:“不準摔件!”
擔心的事發生了。阿柚的力氣和速度抵不住包裹滑落的速度。大量的凍品盒子卡在一起,好幾個翻了下來。
阿柚旁邊的女孩趕忙叫人來救急,三個人一齊上陣,但還是砸壞了若干箱凍品。傳輸帶下,一大片白花花的泡沫碎屑。
發生兩次過載後,這條流水線需要換人。很快阿柚被調離崗位。同組的那個女孩也被叫走。
“媽的!怎麼還有個女的?!” 組長剋制不住怒火,好像他第一次發現,除了阿柚外,這班還有一個女工,當著面罵罵咧咧起來。
組長是快遞公司的正式員工,夜班的日結工是勞務中介公司安排好人頭的。他有些無可奈何,拉包這崗位,“原本派一個男的就夠用,女的就要用兩個。”
感覺很有些生氣,組長又掏出一支綠色的射線筆,朝著一旁屢出事故的阿柚的眼睛晃了幾下,把她叫到眼前,煩燥地問:“識字嗎?”
阿柚職高剛畢業,沒怎麼出過遠門。下午坐大巴到達時,阿柚一直都是迷迷糊糊的。她完全不清楚已到了上海。
“這裡是上海啊?”阿柚問。
在她眼裡,倉庫外長得和地方小縣城都一樣。灰撲撲的街道,狹小的蒼蠅餐廳,高架橋下貨車橫行,塵土飛楊。只有一點特別,巨大的飛機每隔幾分鐘就像墜落般擦著建築屋頂滑過,震耳欲聾的轟鳴聲,顯示這裡截然不同。
“是啊,你現在就在上海,旁邊就是虹橋機場。”
下半夜,張釗手上的掃描動作還在持續,但整個人像榨乾了水分一樣,輕飄飄的。後來,他想到一個方法來對抗流水線的噪音,或者提神。
包裹越來越快,張釗彎著腰,手拿巴槍掃描一件又一件的包裹,一邊從喉嚨裡發出最大分貝的聲音,“啊——啊——”。
胸腔共振,氣息從喉嚨裡衝出來,像那些唱歌的人練聲一樣,在轟鳴的機器中,張釗清晰地聽見了自己的聲音。有一次,監工從流水線另一頭滑過來,以為他有什麼事,結果張釗答沒什麼事。阿柚最開始也感到很奇怪,後來描述這個情景時,她只說,“那個人半夜三更的,中氣很足。”
最困的時候,張釗手上也不會出錯。他的腳因之前拉包時被砸傷過,但拿巴槍掃描面單,他說,“簡單到重複不會出錯”。
“意識有時處於睡覺狀態,事情都能靠身體做了。”
有時練聲唱完啊,張釗又接著數棗。他深吸一口氣,手上巴槍不停:“一顆棗,兩顆棗……”,最長一口氣,他數到 55 顆棗。
每3秒,巴槍掃描一件。後來,他做到了每 3 秒,數 3 顆棗。
所有人都知道,天亮時是整個夜班最困的時候。好幾次,張釗看到前面流水線上的同事的頭晃來晃去。他知道新手來的第一個夜班,這個時候是一道關口,最難熬。
凌晨五點四十分,似乎倉庫裡的暑氣也消散了許多,流水線上的包裹們也漸漸稀疏了下來,一分鐘,甚至三分鐘,才慢騰騰來一件。
這時候,一輛輛貨車,開到張釗身後,下來司機同樣一言未發,趕著將這些包裹封車。
前一批貨車塞滿,封車開走。新的貨車又開到張釗身後,司機同樣節省著哪怕張口說一句語言的力氣。第二批包裹載滿,這是晚班的最後一趟。
天已經大亮,上海的早晨,明亮的光線投射在牆壁上,鮮豔、強勁而刺目。張釗癱坐在工位旁邊,頭枕在流水線的機器邊,先騰下幾分鐘小憩。
八點,這個班的 100 名日結工走出倉庫大門,十二個小時夜班,此時他們感到身體很輕。
走到門口,先脫下身上的馬甲交給各自的中介,並從中介那裡取回手機和身份證,然後回到昨日下午打卡進來的安檢口,再刷臉離開。
易佰酒店就在中轉場倉庫的邊上,這裡是上班和下班的集合點。來自吳江、嘉善、平湖、崑山等地的日結工,在這裡坐上大巴,在頭頂早班飛機的轟鳴聲中,離開上海。
十點準時,阿柚收到一條微信,日結工資到賬:180 元。
而作為長期日結的老工,張釗一天工資 230 元,按月結付。
清晨氣息生動,坐在返回吳江的大巴上,阿柚記得最清楚,“這裡就是上海。”
前一日下午,她到達時看到易佰酒店門沿上,蹲坐著許許多多的年輕人。阿柚下車就被領著加入了他們。來這裡的人五花八門,有幹一天睡三天的“大神”;有忙碌者,同時打三份工,夜班日結是其中之一;也有因為父親生病,陪父住院的間隙,來這裡幹一天並轉移人生絕望情緒的零工……有人困在這裡,也有人在此熬過低谷期。
張釗來這裡也不尋常。2018 年,他從河南老家洛陽新安縣到了上海火車站,在那裡幹起了快手人力資源的招聘主播。火車站人潮洶湧,主播當了三個月,實在難以為繼。8 月 6 日的那個下午,張釗從火車站出發,徒步行走了 6 個小時,橫穿了大半個上海,來到虹橋中轉場。在易佰酒店的門沿上度過了後半夜之後,第二天,他就成了中轉場倉庫裡的一名日結工。
在上海讀大學的青海男生,面板黝黑,也蹲在路邊進食。這半年來,他已在虹橋中轉場斷斷續續幹了五六次。青海男生原本打算到上海兼職做家教,無奈這行太看重學歷,自己的學校不夠有名,只能被漏下來,在不同的日結工作裡流轉。放棄的原因很直接,有一次,他去面試有家教工作,現場候選的 300 多人,不是來自同濟就是復旦,他勉強躋身其中,輪到他時,那個面談的人一看簡歷,劈頭就問,“你有什麼底氣來?”
在易佰酒店門口,儘管大家擁在一起,但彼此很少交流。每個人都有經歷,誰會輕易說出自己的故事呢?
“每天換一批,也沒必要誰去認識誰,大多數都無聊,偶爾來一個大學生,則更像白紙一樣。” 張釗說。
每天下午,不僅前來做日結的年輕人,擠滿了易佰酒店的沿階,而且這裡也是勞務中介競爭的地盤。僅順豐快遞的虹橋中轉場,每天就有六七家不同的勞務派遣公司競相服務。早中晚三班倒,每班 12 小時,淡季的時薪 14 元,旺季稍高一點,而這裡的流水線永不眠。
這些勞務派遣以不同顏色的馬甲辨識各自的門派和來路:深藍色的是軻通供應鏈,葉綠色是上海半秋,藍色的是東科人力,熒光黃的是逸盛人力外包……
穿著不同的馬甲,胸前吊著卡牌的勞務中介,總會顯眼地出現易佰酒店門口下午日光的陰影中。他們拿著當日名單,逐一核實這些奔襲而來的年輕人,他們的注意的更少,無一不是直接略過他們臉上的表情,每天總重複著前一天的口吻。
“不許摔件,不許抽菸,不許帶手機,不許提前離開和盜竊,在流動崗位中服從安排,堅持到收工的最後一分鐘。”
講完紀律,同樣抑揚頓挫地補上前一天也講過的最後那句:“否則就會變成義務勞動。”
然後,給登記過的年輕人逐一發放一件馬甲,收走他們的手機和身份證。進場前,還有開完小會開大會的臨場培訓。
整個白天,張釗都需要睡覺。
早上八點夜班結束後,張釗離開易佰酒店那條道,騎行到附近河濱公園的綠茵道下,然後在一條長凳上一直睡到下午。
張釗有一頂帳篷。那是半年前,他在拼多多上買的,48 元,這個夏天它一直維持著使命,其間壞過兩次,他又花了 33 元,修補好後繼續維持使命。
張釗和帳篷
“非常累,經常一躺就睡。”張釗說。“只要簡單到鋪一個防潮墊,下雨就搭帳篷。”
進入三伏天后,張釗要忍受的不再是雨水或驅趕,而是上海白晝沒有極限的炎熱。
最早時他在倉庫附近的河邊綠道睡覺,但是飛機頻繁起降的轟鳴聲,就像一直在敲擊他的太陽穴。他又換去許浦公園睡,飛機的噪音依然尾隨而來,他就搬至稍遠一點商務區寫字樓下。
張釗從小喜歡仰著睡。臉朝天空,在許浦公園,他會看著飛機腆著銀白的大肚子,張開翅膀,笨拙地飛過頭頂。而在商務區樓下,他看到的只是“虹橋商務區”的五個大字。那裡少了些飛機噪音,但行人卻又是個干擾,有時在夢中,他感到有人圍著他一圈一圈的走,有時是男人,有時是女人。“蚊蟲叮咬和噪聲都沒關係的,有時累了還是躺下就能睡著,但感受到人走過,就警覺,驚慌。”張釗說。後來,他又搬到旁邊有幾棵樟樹的小綠地下,閉上眼睛恰好補眠。
“我想好了,他們趕我就出去,不趕就睡在那裡。”
之前張釗在華漕公園的一個亭子裡睡,長椅涼爽又舒服,前幾天沒事,但後來他剛躺下就不斷有人來趕他走。
搭帳篷的狀態起始於今年 4 月,那時,張釗同時在做順豐和閃送的騎手,住在定海街道,一天收入幾百塊,但不太穩定。固定的居住點對他來說卻是件麻煩事,每天得返程給電瓶車充電,“不管開到任何地方,我都要開回去”。有時長達50公里都沒有訂單派送,來回卻要花一兩個小時。
“後來我太煩了,就想把這個點拿掉。”
一直到 7 月,張釗決定出門就地睡覺,自己搭帳篷做飯,他認為這也是一種適應,靈活運用自己的資源。“我今天的樣子,就像水一樣,哪裡有坑,我就去到哪裡。”
就像在任何一個地方看見插孔,他會本能地拿出插頭給兩個手機充電。哪怕只有一分鐘。
好多次了。張釗已經忘記了曾睡過哪些地方,如果細數起來,那會是一長串有趣的地名,火車站北廣場是睡得最長的地方,接著是環龍商場門口,有一陣子是住在瑞金醫院的長廊裡,還有順豐快遞的休息室,因為他身穿著藍色馬甲……
一起幹活的大姐和他聊天,提議他不要再跑來跑去在公園睡了,找一個爛房子也好。張釗反應激烈,立刻駁回:“那不一樣,那是乞丐,我不是乞丐。”
就地睡覺後,張釗在楊浦區訂下一個幾平米的迷你倉,用來放他闖蕩社會多年的家當。
日常就是這樣的,他隨身一個黑色的雙肩包,然後提著那頂帳篷,每天傍晚在中轉場上班時,他把包和帳篷放在中介那邊,次日凌晨下班就取回。此外,他還有一輛電動車。34 歲的人生,這些是他在上海打拼的全部。
張釗和電瓶車
第一次到了人生必須要去做日結,是 2018 年 8 月 6 日。
那天下午,張釗從火車站北廣場,徒步 6 小時走到虹橋中轉場。而這裡從此之後,給了他數次一線生機。
駐紮在火車站三個月期間,他曾全心火拼快手的人力資源招聘主播。上海火車站是直播據點,人潮洶湧,大浪淘沙。那段時間,他使出渾身解數在快手上釋出了 768 個影片,但絕大多數的評論都是個位數,唯有一個影片登上熱門推薦,評論過了 2 萬,並帶來了 2000 多個粉絲。張釗視之若命,這些粉絲被他一一加上微信,隨後,他高頻給他們轉發和推薦工作。
那些日子,張釗理著淺淺的平頭,戴著金屬框眼鏡,操一口河南普通話。他住在上海火車站,而他的上海站,也因此成了這些粉絲來上海投奔的“第一站”。
但是潮水很快退去,他的影片瞬間又回到個位數評論。他在快手上的 768 個影片很快全部下架。
突然之間,“外面的錢回不來了,沒錢吃飯,也沒錢住宿,什麼事情都做不了。”
在火車站北廣場睡了幾天,他陷入了一個無法返回的絕境。
他曾向人演示的人生版本是創業 13 年,失敗 5、6 次。細數時,河南、甘肅、西藏、新疆、杭州、崑山、上海,人生在各地流轉,也在不同的行業裡反覆流動。真實的情況是,張釗也數不清自己多少次“垮掉”。
在快遞上夜班之外,張釗依然認為,“人可以同時做很多事情。”
“不管有錢沒錢,就算又一次身無分文依舊能活下來。”今年年初,處於最困難的經濟狀況,他去翻連鎖快餐店的垃圾桶找東西吃。
“錢不到賬沒有錢,但是我要生存。”
在小路上,張釗把電動車一橫,開始在馬路邊做飯,一群上海爺叔把他圍住,“說你這好稀奇,你要不去租個房子怎麼樣。”
他已經毫不在乎這些關心和評論了。相反,一群人看著他做飯,然後一口氣吃光,他覺得也不錯。
張釗準備好一週的菜
張釗從 2018 年 8 月 6 日起,到 2019 年 1 月,差不多半年時間,他一直在這裡做日結,幹一天歇三天。
而從 2021 年 6 月至今,一個多月時間,張釗在這裡又做起了長期日結。做六休一,一個月上 26 天班。
而這兩段日子,都是張釗人生的最低谷時期。母親在河南老家重病,直到此刻,醫療費花銷龐大,而他沒掙下什麼錢,還有五萬的債務。
“2019 年的時候我差一點點就自殺了。”他說。
那次 6 個小時的徒步,讓他在人生至暗時刻找到了在上海這座中國最繁華城市生存的一條的罅縫。只要生活動盪,搖搖欲墜,就要墮落到深淵時,他就立即回到虹橋中轉場。即使坐在易佰酒店的沿階上發呆也會心情反轉。
不做日結的時候,也就是這幾年的其餘時光,也是張釗夢想迸發的時候。他曾在崑山盒馬生鮮門店呆了半年,也混跡過上海的夜店保安,還當過中央空調的安裝學徒工,同樣也幹過房產中介和人力資源招聘,還當過駕校招生的銷售……每一個工作,他都拼盡全力去了解它的執行規則和賺錢機密,但幾乎每一次,都以“垮掉”終局。
去年來做日結之前,張釗看準了騎手事業,他同時在順豐和同城兩個平臺上做起了騎手,既送順豐,又送閃送。開初,他想也許可以就此開啟一個局面,意氣風發那時,他說 58 公里 58 分鐘不到就送到,無時無刻不在上海的大街小巷飛馳,有時,他在前面猛跑,警察就在後面猛追。
但是很快,現實就掣肘著他,那時他住在楊浦的定海街道,送順豐和閃送的時候,往往有一個問題,他需要不時地回楊浦住處給電動車充電,有時 50 公里路程,一兩個小時的來回,都不可能有一個單子。而他搬到任何一個地方住,都無法解決這個問題。更重要的是,那陣子母親再次生病,他不得不回河南去一次。很快,現實就徹底終結了他的騎手之夢。
而每一次夢想被現實擊碎後,他都又回到了虹橋中轉場。
有一次,推開新營業的理髮店,他對著鏡子凝視。
“我要一個成熟穩重有壓迫感的髮型。”
理髮師熱情地迎上來,後來訕訕問起他的職業,很疑惑他像傳銷講師。張釗信心十足地介紹說,“我的微信名叫張老師,但我不是講師,我也是一個打工”,停頓一下,“一個創業者”。隨即他講起自己創業 13 年的失敗故事,他說有一次坐計程車時這些故事還“把人家講哭了”。
那次理髮很愉快。不僅髮型成熟穩重而有壓迫感,更重要的還有相互間的尊重與交流。19.9 元的理髮開業優惠,他主動打賞到 28 元。輕鬆贏回一句:“謝謝老闆!”
張釗是 2005 年信仰基督教的。那年他 18 歲,在河南老家輟學不久。早年,他四處闖蕩,而那時最愛看《深圳青年》裡的創業故事。張釗至今還記得有一期講述了一個做面料的人怎麼歷盡艱辛最後飛黃騰達。
但是現在,事情不同了。張釗說,“現在,聽’得到‘我很激動。付費 299 元,聽的是劉瀾的《領導力 30 講》。
張釗可能是虹橋中轉場裡做日結工中,唯一付費聽“得到”的人。當他給那裡的同事提起這件事,“要花費 299 元,” 朋友驚歎那是一天多的日結工資。
“我的媽,你怎麼能這麼想?”張釗也很驚歎。
然後,他講述了他感觸最深的一個事例,最近一期價值 16800 元的高研班裡,有一位北京學員,“自己做團購一年賺了 5000 萬這麼多。”
2018 年底,當時他還兼著駕校招生的銷售,卻每天沒有業績。當時的一個很曖昧的女生打電話暗示他,“你掙的又不多,幹嘛不去找正式工作做呢?”
張釗掛掉電話,半個月都不再聯絡對方,他的失意大爆發:“我活著即為創業,如果你把我的創業拿掉,那我什麼都沒有了。”
在上海火車站做快手人力資源招聘主播的時候,他做過一個夢:似乎在半睡半醒間,我躺在那裡,看到了我的大拇指,它斷掉了,然後中間開花,裡面黑乎乎,後來飛出了一個黑色的大馬蜂,最後看到裡面全是空的。
好長一陣子,張釗被這個夢纏住了,不知什麼寓意,也不好對外人講。後來過了很久,他才明白,“我是有信仰的。”果然,後面在中轉場發生了事故,在裝卸包裹時,傷了腳。從此,他不能幹重活了。
在虹橋中轉場,夜班結束於每天早晨八點。他從流水線下班後,去中介那裡提溜自己的帳篷行李時,張釗總會買幾瓶飲料,好好做人情,面對著他熬紅了的真誠的眼睛,對方會靠近他,用手輕拍一下他的肩膀,“你和其他人不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