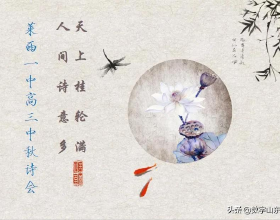從西漢元封四年(公元前107年)到北齊武平元年(公元570年)設臨河郡的677年中,山西永和一直叫狐讘。
當地傳說,當年西漢修建狐讘城的時候,“在選定的地址選好一個木樁作記號,晚上下了一場雪,到了第二天,木樁不見了,厚厚的雪地上留下一串狐狸來過的腳印。人們順著腳印追尋,終於找到木樁,大家認為這是狐仙的點化,就把城址挪在這裡了。”因此,這座縣城被稱之為狐讘城。
這種說法似乎有點道理。原因就在於,當地曾經有很多狐狸。先秦時,這一代可能是狐氏狄人所居,縣中有座捕狐山,傳說晉獻公曾經在此地狩獵狐狸。不過,“讘”又是什麼意思?讘音聶,即便在古代漢語中,“讘”也是一個使用比較少的字,《康熙字典》說,這個字通常用在人名或者地名中,而舉出的例子,就是“河東狐讘城”。這個字使用的頻率之小可想而知。
宋代的《太平寰宇記》說,“永和縣,說北一百里,依舊三鄉。本漢狐讘縣之地,屬河東郡,後漢省。今縣西南三十五里狐讘故城,是漢理所。曹魏初別置狐讘縣,屬河東郡。”又《水經注疏》上面記載與此基本相同。
這說明,永和縣的命名源頭應是在漢代,好在《史記》給了我們答案。
永和縣
漢代武帝時,在永和縣設定侯國。
在《史記·建元以來侯者年表》中,司馬遷說:
瓡讘,以小月氏王將眾千騎降侯。
這是說,一位小月氏王在漢兵到來時率領千名騎兵歸降,所以被封為瓡讘。同樣的情況還有騠茲,在瓡讘之前,“小月氏右苴王將眾降侯,千九百戶”。這位小月氏王名稽谷姑,被封騠茲侯,至今在山東琅琊還有一個叫騠茲的地方。
元封四年(公元前107年)正月乙酉,侯扜者元年。
六年,侯勝元年。
第一任瓡讘侯是一名叫扜者的小月氏人。這個扜先生,曾經是小月氏王。同時,《史記》還提到了瓡讘侯食“七百六十戶”,這大概就是永和當時的人口數:約七百六十戶。史書中還說到:兩年之後,扜者去世,他的兒子扜勝繼承狐讘侯的位置,扜勝在位6年,國除。
扜,音於,作為姓氏,現在已經不復存在。不過漢代在西域,這可能是比較顯赫的姓氏,《史記·大宛列傳》說:“(大宛)]東則扜罙 、 於窴 。”
《集解》說:“瓡讘在河東。瓡音胡。讘,之涉反。”《索隱》曰:縣名。案:《表》在河東,《志》亦同。即狐字。
歷代都把瓡讘讀為“狐執”。
不過清代文字大家段玉裁卻有不同看法,他在《說文解字注》中認為,這是一個疊音詞,瓡應當的執,讀為支,而非狐。這個詞應當讀為“執折”,狐讘是一個錯誤的說法,這個縣的命名跟狐狸沒多大關係。
“讘,多言也。從言。讘,聶聲。之涉切。七部。河東有狐讘縣。見地理志。按史,漢表皆有瓡讘侯。徐廣,小顏瓡皆音狐。考漢志北海有瓡縣。小顏雲瓡卽執字。疑瓡讘二字疊韻。瓡當從爪作瓡。執之或體。不音狐。漢志,説文作狐讘。皆偽字也。”
西域多疊字韻字,漢代從西域傳來了大量的疊韻字,瓡讘或許只是其中之一。情況可能是這樣的,扜者來到長安後,未央宮酒罷,賓主盡歡,武帝說道:“這樣吧,我把你封到河東,考慮到你們故鄉的習慣,這個地方就改名叫瓡讘。”於是,瓡讘的名字就傳了下來。
這批小月氏人,在西漢為屬國騎。所謂屬國騎,是當時在一些邊郡設定屬國以管理歸順的少數民族,各依其本俗而屬於漢,由屬國都尉統轄。
永和有龍吞泉村,在龍吞泉村東邊,永和縣城北約3公里處,芝河在蜿蜒南流中,形成一塊小臺地,這裡就是漢代的侯國。2002年的考古中發現這一遺址,發掘中發現十多處用來做飯的紅燒土地面和灶址,紅燒土是小月氏人點燃篝火留下的,社址是當年放置鐵鍋用的,考古學家推斷:“這個灶當是一個人數可觀的群體使用過的大型爐灶”。此外,人們還發現一處陶窖遺址,數件陶罐下腹近底處有小孔的現象。最後的結論就是:這是漢武帝以來由祁連山區內遷到永和的小月氏遺存。
這批小月氏人可能一直到隋代都活動在山西西部和關中一帶,不過,山西一支較為沉寂,倒是山東的一支較為活躍,後趙石勒起事,召集十八騎,其中有支雄、支屈六等人。支雄尤其有名,支雄後人的墓誌銘有不少被發現,證明他確實是琅琊小月氏人。這些墓誌銘表明,支姓後人支光曾經在唐代江州尋陽縣丞,不知道和白居易的江州司馬是不是同一個時代;還有一位曾任鴻臚卿、致仕贈工部尚書。
支光墓誌銘
《支光墓誌銘》說:“其先琅邪人,後趙司空始安郡公曰雄七世孫也。永嘉之亂,衣冠違難,鱗萃江表,時則支氏浮江南遷。”一句“永嘉之亂,衣冠違難……浮江南遷”,證明在這個時候,這些小月氏人已經高度融入華夏民族中。
(圖片來源於網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