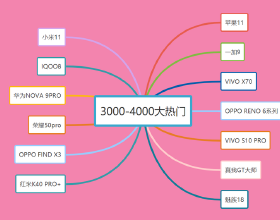#尋找故事家#說實話,年歲逐增才知道什麼叫做人生無常。那天下午下班後,我還在辦公室,走得比往常更晚一些。敲完了最後一個字,在退出微信的時候,突然看到堂哥發來的資訊,白屏黑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地告訴我:大伯去世了。我愣在那裡,好長時間都沒有說出話來……
在我家老房子不遠的地方,就是大伯家的一塊田。如果說要算距離的話,不過二三十米。大伯隔三差五的就來田裡面勞作,他來的時候總會在我家待上一會兒。在父輩中,我對大伯是比較熟悉的。因為他會說很多的謎語,來的時候總會出謎語給我猜,那些謎語都是生活中一些常見的東西。記得當時很有趣,但現在卻慢慢淡忘了內容,但他出謎語給我猜的場景一直都記得。大伯家有很多的線裝古書,不知道他的謎語是不是從那些古書上看來的。有很多次,天氣晴好的時候,他便把那些書搬到院子裡曬太陽,我翻過,都是繁體字,不認識。
我記得冬天的時候,大伯還養鴨子。那個時候他很強壯,輕而易舉地就把那些到處亂跑亂飛的鴨子吆喝在了一起。他還送給我綠殼的鴨蛋。有時他也給我們講,我們這個家族是從四川搬過來的,當年我們的老祖宗,用一挑籮筐擔著兩兄弟,到了我們現在住的這個小山村,然後在這裡繁衍勞作。他甚至計劃著如果有時間,大家應該到四川去尋根。大伯還會剃頭髮,他剃頭髮只會剃“壇缽蓋”,那種髮型就是頭頂圓圓的,四周都是齊整的,活像蓋罈子的蓋子……
有一年的春節,我回去祭祖,正好碰見了大伯。我叫他的時候,他沒有認出我——他看著我穿開襠褲到處亂跑,看著我離家到外面讀書,看著我走出寨子出去工作,他看著我結了婚,有了大兒子。隨著我慢慢離小山村越來越遠,我離他也越來越遠,時間會改變一切,包括人的顏容,記憶裡,他好像已經有很多年沒有見到過我了,歲月無非是在他的臉上開鑿出了一條道的溝壑,但對我而言,我變得大腹便便的、頭髮掉了,已經成了標準的中年油膩男。他的記憶力還停留在我二十來歲時候的模樣……大伯告訴我說,他馬上就要滿80了,我聽了大吃一驚,仔細想了想,我離開這個小山村已經有20多年了。每年僅是在春節或者是遇到寨子上有紅白喜事而恰好又能請假的時候才回來,寨子上的很多事情、很多人對我而言都已經變得陌生了。我對很多寨子上年輕的人而言,也僅僅是一個符號,他們知道寨子上曾經有過我,但是卻從未看見過我。故鄉慢慢就成了我生命中的一個符號,在我的記憶裡漸行漸遠,慢慢變得陌生。
我站在大伯生前居住的老房子前,不時有鞭炮和煙花響起,硝煙瀰漫中,我又想起了一些關於他的往事來。他那些書,今後還有沒有人在晴朗的日子翻曬?現在不會像30多年前那樣,再有人給我綠殼的鴨蛋?就算給我,也沒有那個時候的快樂了!我們寫符包,“符包”的書名究竟是怎樣的?我不知道,好像大家口耳相傳,說的都是這個音。我仔細推敲了一番,覺得“符包”比較貼切。寫符包要追溯到很多已故的親戚,這就是所謂的慎終追遠。寫符包的過程也是理清一個人家族關係的過程。父輩中好像也沒有人提起要到四川尋根問祖的事情了,不過此次他與世長辭,或許可以魂歸四川,到那裡尋找我們的祖輩、祖輩的祖輩……大伯出謎語給我猜,但我卻再也沒有機會出個謎語給他猜了。在我心目中,他也是一個謎。
父親和我寫了最後一封符包,他對我說,一會兒我打電話給你楊大伯,我們一起去看一下田地裡種的那些柏木和梓木。我很不解,為什麼突然就要看那些樹木呢?父親說母親在催他回去砍木料做棺木——母親說我姨母、姨父等都已經做好了棺木,他們比母親年紀還要小,都已經準備好了百年之後的歸宿,她不斷催促父親,甚至還認為父親在這件事情上很怠慢,為此而有點生氣。還過幾年,父母親就70歲了,他們已經逼近古稀之年,眼神已經開始渾濁。不僅我父母這樣,我的父輩他們差不多都一樣。只不過,大伯這次離世,更讓人感覺到了生命的無常,在自然規律面前我們無處可逃,無路可走,只有選擇投降。
父親和我,還有楊大伯,我們一起去自留地,看那些數十年前父親栽種的柏木和梓木。父親一邊走一邊對我說:“你母親要杉木或者是柏木,梓木的她不要,我覺得梓木的還是可以!”父親一邊揮舞著手裡面的鐮刀,一邊砍著荊棘——是的,這些地方以前都是土,父親和母親辛辛苦苦開荒開出來的土——只不過在我家的土地證上,這些土變成了合法的土,不再是山林。現在這些早就荒蕪了,慢慢的迴歸了山林,迴歸了這片土地最初的模樣。
站在土裡我還在想著原來的土裡哪個地方有塊大石頭,我曾經在放牛的時候,在那塊石頭上休息過。我還在努力搜尋著心裡面記憶的殘片,努力回憶著哪一片土曾經被我用鋤頭挖過。我還在努力回憶著那塊土曾經種過煙,種過玉米,種過葵花,種過花生,種過洋芋,種過紅苕,種過小麥,種過蘿蔔白菜等等。這些貧瘠的土地支撐起了父母親全部的希望——烤煙是經濟作物,至於玉米花生,洋芋紅苕,小麥等等是為了填飽肚子,解決最基本的生存需要。我一直都認為這些土只是承載著我們最基本的溫飽。
父親帶著楊大伯,先是看了梓木,兩顆梓木,很粗很大。然後又去看了柏樹,兩棵又大又粗的柏樹——他們就是父母最後的家。父親和楊大伯談論著梓木砍倒後,其中的哪一截做棺木的什麼部位。他們倆談得風輕雲淡,好像訴說著別人的故事。給我的感覺就是,他們都覺得這個年紀應該做棺木了——不知道什麼時候開始,他們對生死如此淡定。我又想起了史鐵生說過:“一個人,出生了,這就不再是一個可以辯論的問題,而只是上帝交給他的一個事實;上帝在交給我們這件事實的時候,已經順便保證了它的結果,所以死是一件不必急於求成的事,死是一個必然會降臨的節日。”他們就在我的身後用手在樹木上比劃著,我在一旁心有慼慼。
看好了樹後,我以為我們會回去,但父親又帶著楊大伯往前面走,我不知道他要幹什麼。狹窄的田埂被白雪覆蓋著,在兒時的記憶裡,那田埂下面的坎是很高很高的,我牽著牛在田埂上走的時候,心裡面是充滿了恐懼的。那個時候的恐懼,純粹是害怕人和牛跌下高高的田坎。但現在,我走在那裡,心裡面還是充滿了恐懼,這種恐懼是一種對生離死別的恐懼。有些人一別之後就再也不見了……
父親帶著楊大伯在一片荊棘叢生的土上站了下來。他們抽的煙,一邊抽一邊談論著山勢走向,父親說那塊土埋雙墳是沒有問題的——我算是聽明白了,父親不但計劃著做棺木,還計劃著百年之後,他在哪個地方長眠。現在我才知道這片土地不僅承載著我們的溫飽,可能今後還是父母最後的歸宿。父親又帶著楊大伯看了另一塊土——沒事的時候他就回老家了,我們不知道他回來幹什麼。現在總算知道一點點了,這一切似乎都是早有預謀的。父親還對我說,還是把家裡的老房子修繕一下——父親說的那兩塊做最後歸宿的土,都能夠看得見老房子。哪怕隨著我們住到縣城,已經有好多年了。但父親依然魂牽夢繞著這片土地。這片土地上有父親的父母親,父親父母親的父母親。在這片土地上,有父親的過去,有父親的現在,還有父親的未來……說實話,父親在看那兩塊土的時候,我竟然想到了另外的問題。就在前不久,我還在和衛哥說,問一下醫學院哪裡可以接受遺體的捐贈,我可以做遺體捐贈的志願者。對最後的歸宿,我和父親有著不同的處理方式,或許這樣的歸宿只是形式上的差別,冥冥之中我們還會再次重逢。
很多年的一天,上課的時候,我和學生說,我們永遠不知道明天和意外誰先會到來,說不定老師上午還站在大家面前,下午就離開了……坐在前面的小鄧瞪了我兩眼:“呸!呸!呸!老師不要烏鴉嘴”。其實,這不是烏鴉嘴不烏鴉嘴的問題,這就是一個事實,一個我們都不願意面對,又不得不面對的事實。
天上的雪又開始零星的飄落,四周白茫茫的一片,這片大地熟悉而又陌生,陌生而又神秘,雪落無聲,無聲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