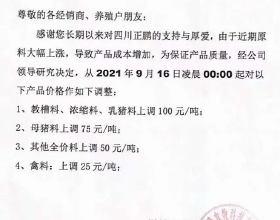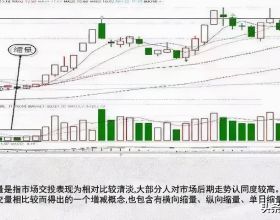人定勝天,這是曾經非常流行的一個詞語。
在機械化程度很低的年代,人為了在惡劣的環境下生存,就必須戰天鬥地。
比如河南深山裡的人為了走出深山,他們仿照神話故事“愚公移山”的做法,在懸崖峭壁上開山修路,在怪石嶙峋間挖溝修渠。現在成為旅遊景典的掛壁公路和紅旗渠,都是當年戰勝自然的證據。
其實,當年也不僅河南如此,很多地方都有這樣的經歷。“農業學大寨,工業學大慶”,這是當年隨處可見的口號。農業學習大寨的修築梯田,大寨人多地少,多山少雨,大寨人在陳永貴大叔的帶領下,將荒山變成了梯田,大寨經驗在全國推廣。
我故鄉所在的鄉叫白沙鄉。地名的由來跟當地的地質有關。地面上覆蓋一層白白的細沙,也許早年間是這樣的。
我出生後,大圩裡都已經是硬土地,沙地不是很多。可我們磨盤州里依然是白沙覆蓋。
磨盤州是經過長江水千百年的衝擊形成的,泥漿和著沙被江水席捲,在江北打了一個灣,由是泥沙沉積,在水退去之後,白沙堆成的磨盤州就形成了。
這原本是無主之地,對面江西人看中了這塊地方,由是,他們春天划船過江到江北沙灘上灑下種子,秋天的時候再次划船過來收穫。
很快,這塊土地上就來了一群群逃荒的人,他們有一家老小肩扛手提過來的,有順江而上因船擱淺而住下的,還有被逃荒的人招引過來逃荒的。等等。
一戶、兩戶、三戶,......,窩棚連成了村,連成了片。
在廣種薄收的年頭,沒有人在意收成,只要能收回種子就是勝利。可隨著人口的增加,先前的收入漸漸入不敷出。
村人發現,沙子地有很多問題,一是存不住水,水大就澇了,水小又旱了,最要命的是,沙子不容易穩固植物的根系,一陣風來,種子或根莖就露在外面。冬天沙子沒有溫度,夏天沙子熱得燙人。
有聰明人發現,一尺多深的沙下,就是黏土。
由是,村裡農閒時就多了一項勞作——翻沙。
即用鍬將地翻一遍,將沙子埋在黏土下面。這是非常辛苦又不見成效的一項活動。一天也翻不了幾十米,勞作下來手上不是起泡就是生繭。
隊長敲著上工的鐵,從村頭到村尾,人們懶洋洋地從家裡出來。
男人戴著草帽,脖子上搭著一條毛巾。女人扎著頭巾,頭巾前面與劉海齊平,後面一直披到肩上。翻沙的時候,稍微有點風,就會沙舞飛揚,毛巾和頭巾既可以擦汗,又可以用來捂住口鼻。中間休息,還可以拿著毛巾到河溝裡漂洗一下,既可以洗毛巾,又可以洗臉。
沙土地唯一適合種植的莊稼是花生,也許是容易紮根的緣故,沙地的花生結的籽非常多,拔花生也是比較輕鬆的事,拎著花生的秧子一提,根鬚上的花生差不多都起來了,且花生非常乾淨。這時候將拔起的花生秧扔在沙地上,很快就能烤乾。不到半天,就可以將花生秧堆在一起點把火,等花生秧燒完,灰燼裡留下的就是香甜軟糯的燒花生了。
一年之中,也就這麼一個時令,人們對沙是喜歡的。餘下的時間,都是在戰天鬥地,翻土壓沙。尤其是颳風的日子,早晨乾乾淨淨出門的大人,回來滿身滿臉的灰塵。
有那麼一年,不再有人說翻沙的事了,因為小圩破了,長江水帶著厚厚的淤泥蓋在沙地上,徹底地解決了沙地不易種植的問題。大自然在毀壞房屋的後續幾個年頭,跟村裡帶來幾個豐收年,也許這是一條自然法則,大自然透過自己的法則來控制著世界。
沙地給我帶來的最大快樂是,秋水廖縮後,江邊會呈現幾十米寬的沙灘,秋冬之際,我們這些放牛的孩子,在牛吃得差不多的時候,我們會騎著牛到沙灘上賽牛。
當鞭子抽打著牛的屁股,牛的四腳騰空,帶出來的細白沙漫天飛舞,我們也不再是放牛娃,而是天地間的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