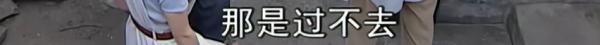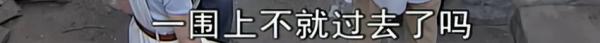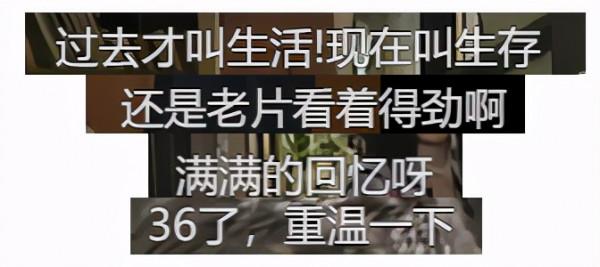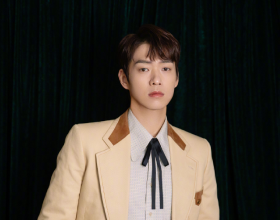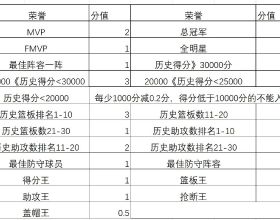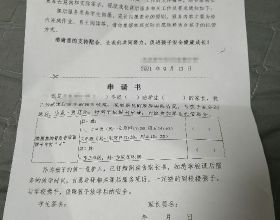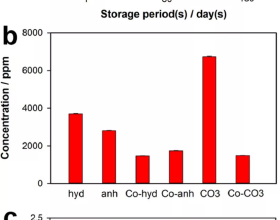現在國產劇沒幾部能擺脫這毛病:
懸浮。
人均中產往上,看不到工薪階層普通人。
就算是所謂的“都市窮人”,月入3000,依然在上海住著精裝望江公寓。
當國產劇的濾鏡越來越細膩,房子越來越豪華,佈景越來越精緻。
彷彿這是必不可少的“賣相”時。
你再也看不到熒幕裡的煙火氣,平常人家的喜怒哀樂。
也格外懷念曾經有個這樣的家:
促狹,破舊,摩擦不斷。
卻又被現在觀眾親切稱為“世界上最完美的家”。
完美?
其實是這個破樓不迭的屋簷下。
完美詮釋了無數家庭最真實的樣子。
《貧嘴張大民的幸福生活》
2000年,《張大民》在北京電視臺開播,便成了電視屆一個經久不衰的傳奇。
這部當時沒有大明星主演的家長裡短日常劇,沒有人想過會大火。
但結果收視率70%,幾乎摘獲國內所有電視劇獎項。
我們或許沒有機會見證它的火爆。
但一個個青蔥而熟悉的臉龐還是喚起了我們對舊歲月的懷念。
那時候。
霍思燕18歲,潘粵明當年剛剛24歲,張涵予還是小鮮肉。
“大民子”梁冠華為拿下這部戲減肥30斤。
朱媛媛25歲,剛進入演藝圈。
一切好像看上去都很美好。
一群青澀的演員為我們講述過去的日子。
21年後,我們懷念《張大民》的究竟是什麼?
僅僅是同行襯托嗎?
我們懷念的,是那時候的人啊,還是個人。
01
才過去20年,我們幾乎不敢相信
那個時候電視上的普通人,怎麼活得這麼貧。
不是忙著“鬥小三”,更不是糾結什麼時候可以和名媛喝上一頓下午茶。
大家的煩惱,無非是奔波忙碌,應付捉襟見肘的生活。
《貧嘴張大民的幸福生活》撲面而來的,就是一股:
逼仄感。
窮,是真的窮。
苦,也是真的苦。
逢下雨屋裡就漏水。
拿個盆子接著是常事,大雨把家裡給淹了,就拿著鏟子一次一次地把水舀出去。
一家人圍著吃飯,腳都伸不直,旁邊就是兩張床。
每頓飯都是青椒炒土豆絲,番茄炒蛋。
錙銖必較。
張大民給媳婦雲芳下奶的魚被貓叼走了,他上房揭瓦也要把魚從貓嘴裡搶回來。
十幾平方米的大平房,是張大民一家最大的煩惱。
中年喪夫的母親,三個兒子,兩個女兒,一家六口,只有兩個房間。
後來大民和大軍娶了媳婦,這個問題就更棘手了。
張大民先是想著把兩張雙人床壘起來放,一對夫妻住上鋪,一對夫妻住下鋪。
但床實在搖搖晃晃咿咿呀呀,只好放棄。
上下鋪不行,那就來大通鋪。
兩張床合併在一起,中間用一個簾子隔開,就是兩個房間。
但大軍莎莎新婚夫婦行床時毫不忌諱,每晚把張大民和雲芳吵得興致全無。
大民讓大軍夫婦倆晚上小點聲,只見大軍委屈地說:“我覺得那不算叫喚。”
張大民的貧嘴又上場了:
“那算打噴嚏,算詩朗誦啊。”
要說懸浮,《張大民》也是真懸浮。
只不過這讓人看得又心酸又好笑。
因為裡屋要騰出來做婚房,外屋擺了兩張上下鋪,外加一個箱子壘的單人床,原來的電視櫃放不下了,咋辦?
大民用鐵絲吊著電視。
看著是夠懸的
逼仄是生存的環境。
而生活,是在逼仄中一樁接一樁的無奈與伎倆。
能化解貧的還是一個字——“貧”。
02
哪怕日子有這麼多的苦惱,《張大民》還是用喜劇的形式,向我們娓娓道來。
劇裡一大半的京片子段子,都是張大民貢獻的。
大民違規建房,對面屋的古三說要揭發他,大民反而這時候嘲笑他媽媽的腰圍。
大民不知道這些貧嘴話會激怒古三嗎?
他就是故意用貧嘴戳中古三的要害,腦袋捱了古三一個搬磚頭。
因為只有捱了古三的磚頭,他才能拿捏住資本家古三的要害,一碼換一碼。
全劇最動人的一幕,來自張大民的母親,一個將四個孩子含辛茹苦拉扯大的母親。
患老年痴呆的母親,將大民的孩子認成了小時候的大民。
短短几句話,讓我們明白了張大民這個人。
媽站不住了你扶著媽
媽走到哪你跟到哪兒
你給媽當柺杖使
張大民整天貧嘴,樂呵樂呵的。
但他知道,父親自他小時候去世後,他就要擔起整個家,做母親的柺杖。
作為長子,上有老母親,下有4個弟弟妹妹還有一個兒子,一家大小所有事,都由他來操心。
張大民用他的貧嘴,捆綁了自己,縫補了整個家。
記者過去採訪《張大民》的編劇劉恆,問道:“張大民身上好像有濃濃的幽默感。”
劉恆說道:
“這齣戲的外在形態是喜劇,骨子裡有悲劇的成分,是以幽默的敘述語調講述一個無可奈何的、感傷的故事。”
Sir這就明白了。
因為貧嘴張大民的幸福生活,從物質的眼光考量可不是一襲華麗的袍子,那就是遮體寒衣,一個蝨子一個蝨子接著往上爬,爬出去,都不用掀開。
一個擠到不自在的家裡。
是各自走不出去的困境。
他們全都沒有“獨立”的條件
張大民自己最開始是暖瓶廠工人,後來為了漲點工資去做噴漆工,哪怕有長期吸入有害氣味的隱患,妻子李雲芳是毛巾廠工人。
二姐大雨是肉聯廠豬大腸清洗工。
最小的弟弟大國倒是考上大學,但他來不及高興,只想一吐多年的憋屈:
螞蟻窩憋死我了
再後來,張大民媽媽老年痴呆了,需要每一個人輪流看守,不小心就會走丟。
本來就是普通職工的家庭,過得更是昏天黑地。
那麼,面對這樣的生活境況,身陷其中的當事人要如何面對、消解呢?
張大民兩口子回答過,兩個答案在Sir看來是兩種“方法論”,但又互相依存,影射。
兒子問:
“媽,人活著有什麼意思?”
雲芳說:
“有時候覺得沒意思,剛覺得沒意思,又覺得特別有意思了。”
兒子又問大民:
大民的回答更樸素而有力量:
“沒意思,也活著。別找死。有人槍斃你,沒轍了,你再死,死就死了。沒人槍斃你,你就活著,好好活著。”
普通女性的隱忍和釋然是對苦難的懷柔;
普通男性的堅韌和豁達是對苦難的不服。
這一對夫妻,一對中年男女,幾乎代表了東方民族傳統文化裡女人和男人最質樸的精神面貌,像我們的父親母親。
這段在北京胡同屋頂上拍的“閒筆”是貧嘴下面的風骨,對於苦難的樂觀甚至是蔑視。
而貧嘴又是張大民這樣揹負太多的兒子、丈夫和父親的血氣:
生活,如果我不能贏你,但可以讓你笑起來。
03
為什麼我們現在一說起懸浮的國產劇,就想起《張大民》?
為什麼20年裡,我們越來越看不到那樣親切的煙火氣?
有人說是冷漠。
但在Sir看來,這更是怯懦。
最新一期的《十三邀》,學者錢理群以自己的人生閱歷給出了答案,面對苦難有兩種選擇。
一種是美化、掩飾;
另一種就是遺忘、割裂。
但還有一種方式,恰恰是很多人逃避的:
把苦難,化成精神資源。
然後我們在螢幕裡看到的就是這些因為貧苦而貧嘴,普通人的“過去時”被美化了,被割裂了。
《張大民》在今天看來,最讓人吃驚的是它沒有小人物的逆襲,沒有用happy ending給觀眾相當的治癒和滿足感。
想想看。
我們今天的國產劇,是否已經失去了消化苦難的能力?
《歡樂頌》安迪童年不幸,有精神病遺傳基因。
但她長大以後,便有了開掛人設,職場上呼風喚雨,成功男士個個拜倒在她裙下。
《都挺好》蘇明玉,從小母親重男輕女,被當成家庭犧牲品。
但轉眼,她又是獨立女強人。
有了財富的底氣,再去面對不公的家庭。
國產劇習慣性地讓主角成為美強慘
必須有了“美”和“強”,才能救贖“慘”。
一旦沒有這兩種開掛的超能力,國產劇便不知道如何讓主角們去面對自己的人生了。
但這,又是對觀眾的敷衍搪塞。
因為作為普通人的我們,沒有編劇可以為我們的生活動動金手指。
那麼終究,我們要如何生活那塊沉重的頑石呢?
《張大民》,恰恰體現了創作上最大的誠實與勇氣。
創作者沒有讓張大民一家富貴起來。
而是真正做到了尊重生活的真實,也貼合了時代變遷的脈絡。
1998年,該劇開機時,全年全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5425元,月均可支援收入不足500元。(據國家統計局1998年中國人口綜述資料)
大軍結婚時,想要單位儘快分一套房子。
大軍的房子被關係戶插隊,領導信心滿滿地對他說:“如果中間沒有加塞兒的,也許等到二十一世紀,你就能分到自己的房子了。”
但沒人告訴他。
世紀之交的2000,那一年,住房分配已經在全國停止,中國正式進入全面商品房時代。
他排隊也分不到自己房子了。
北京小衚衕的拆遷。
本根據人口和麵積換算的新房面積,拆遷公司卻偷偷修改合同。
雲芳和大民一個調崗,一個下崗。
雲芳本是坐辦公室的會計,一做就是十幾年,後來因為規定只有大專學歷才能坐辦公室,她被下放到車間。
大民在保溫瓶廠幹了十幾年,本來以為一輩子的鐵飯碗,也光榮下崗了。
最後一集,畫餅的領導自己也下崗了,他找到在飯店看廁所的大民商量著推銷積壓的熱水瓶,張大民挨家挨戶賣,發揮三寸不爛之舌,結果收效甚微。
雲芳的前男友(張涵予 飾)從國外衣錦還鄉,請前同事和雲芳吃飯,大民雖然酸還嘴硬要面子,讓媳婦去,自己喝悶酒到醉。
這一天,母親七十大壽,全家聚在一起。
大民也趁機把心裡的哭和委屈哭出來。
然後呢,沒有然後,第二天他還得推銷熱水瓶。
這是很不過癮的弱結局,與2021年很多觀眾的觀劇習慣背道而馳。
人們更期待看到的是,大女主、霸總或者平民英雄如何逆襲,走上人生巔峰。
劇的懸浮。
何嘗又是觀眾的觀念在被迫懸浮?
因為現實的鴻溝在擴大,階層的壁壘在抬升,人們越來越不相信那個理想的彼岸可以出現在自己身邊,只能夠遠遠眺望那些雲端上的人。
相信那就是幸福的模樣。
而《張大民》,可能是工人階層生活在熒幕上的最後一次高光。
那個時候,工人的自豪感尚未完全被時代洪流沖垮。
那個時候,人群的差距分化還不大,大家可以一起體會著差不多的生活。
比如吃的喜悅。
大民發工資那天,立即給雲芳買了她想吃了很久的雞腿。
吃雞腿,有什麼稀奇?
但云芳吃著雞腿,一臉的幸福,張大民也是。
因為張大民說,看兒子吃奶、看老婆吃雞腿、看媽媽吃冰,這才是他人生三大幸福之事。
一家人吃著粗茶淡飯,還拌嘴。
卻也顯得熱熱鬧鬧。
孤傲的大雨把她對愛情的美好想象都寄託在一個男人身上,當她被騙,懷孕打胎後,把辛酸都嚥下自己的肚子。
用微薄的工資買了很多的聖代,一口氣吃完,再一口氣放下。
將悲傷轉化成食慾,就是普通人沒有了辦法最後的辦法。
張大民們,如果是現在國產劇裡的主角。
他們都可以住在豪華的房子裡,隔著大大的落地窗,俯視望京、上海明珠。
而裝點他們生活的。
是那些隔靴搔癢虛無縹緲的痛苦。
張大民們或許不理解的是:
住上大房子,年薪百萬,為什麼會不幸福呢?
或許因為。
他們從來沒有面對過真實的自己。
一個個非人的假人,他們的所謂幸福和悲痛,都假得沒有形狀。
值得一再回味的一個情節。
《張大民》裡雲芳快要生孩子了,大民覺得這日子還得再想想辦法,於是違規把院子門口的牆給砸了,擴建了一間屋子。
問題來了
綠化部門不讓把門口的樹砍掉。
得,那就把樹留著,把屋頂和床鋸個洞。
妹夫來家裡拜訪,實在住不下了,三個男人擠在張大民的小屋裡,妹夫一宿都不知道兩腿往哪放。
這棵挪不走也砍不掉,穿堂而過的樹。
不就是許許多多平凡的人,改變不了,一生都要與之周旋的難題嗎?
而在這棵樹底下度日的大民雲芳夫婦,乾脆為將要出生的孩子取名為:
張樹。
屋子裡的樹在生長著,另一個“樹”也在人間誕生。
一個本來很平凡的名字。
因這個有樹的小屋,而充滿了一種樸素的希望。
生活從來沒有什麼捷徑,可以抹除痛苦,脫離煩惱。
只有相伴而生,相互較量,是圍繞著它無休無止地做功。
好的劇不是無視它。
而是讓你相信,我們做的總會是有用功。
本文圖片來自網路
編輯助理:小津安4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