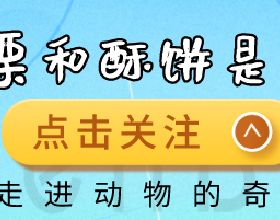轉載自斐君思享匯
從許多角度看,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都是一個教科書般的金融戰案例。對研究從那時至今,以及未來的金融攻擊,都非常有參考價值。
更重要的是,它絕不僅僅是金融戰,而是在金融戰的表象下,融合了生物戰、政治顛覆戰、資訊輿論戰、心理戰、文明戰等多種戰爭形態,而且是天衣無縫的融合在一起。
現在,這種天衣無縫的融合似乎又上演了。但由於西方自身也受到病毒衝擊,這種“融合”及其效應,遠遠不如1997年顯著。
未來,1997年的一幕是否會再次上演,我們如何未雨綢繆、有備無患?回答這些問題,需要對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作一個系統性的覆盤。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究竟如何爆發的?究竟什麼力量在國際金融舞臺幕後翻雲覆雨?是市場這隻看不見的手嗎?是金融大鱷嗎?是某個或數個政府嗎?一系列國際組織在這些危機中又扮演了什麼角色?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橫掃一個又一個亞洲主權國家,在那之前,在數個世紀的漫長時期,主宰東南亞經濟的是華商。而在1997年金融危機中,主流媒體與學者鮮有提及的一大重要事實是,在這次金融風暴中,華商遭到沉重打擊、成為財富流失最多、最大的無形受害群體之一。
值得深究的問題是:華商僅僅是此次危機的“附帶犧牲品”嗎?這場危機究竟是場財富洗劫與蠶食大宴,還是別有所圖?
1997年亞洲金融轟炸被正式引爆是在7月2日,“恰逢”香港迴歸的第二天,並由此上演了一場財富洗劫與財富轉移大戲。
比起五百年前歐洲殖民者透過明目張膽的搶劫與屠殺進行的全球財富大搬運,1997年的這場財富洗劫與轉移更加無形、規模更大。
不僅如此,彷彿“老天”也有意與香港迴歸作對。在金融風暴橫掃亞洲的前夕,香港突然被一種致命流行性病毒襲擊——高度傳染性的致命性禽流感病毒H5N1。
H5N1於1996年首次在廣東一個農場飼養的鵝身上發現,及至1997年4月,香港有大批活雞相繼染感染病毒並迅速死亡。
醫學界許多人對此感到不可思議,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禽流感是由病毒引發的動物傳染病,具有高度的特定物種針對性,在此之前,從未有過這類病毒從鳥類直接傳染到人類、甚至人傳人的先例。
然而,1997年5月,就在香港迴歸前夕,這個病毒突然發生不可思議的變異,首次感染人類,一名三歲男童感染後身亡。
更加引發醫學界警覺的是,通常人類的流感病毒感染的是上呼吸道,但H5N1病毒卻可直接深入肺部,不僅引發嚴重肺炎,還可引發腦炎、腦膜炎、急性呼吸窘迫、內出血等病症……
及至11月,也就是香港迴歸4個多月時,全港已被恐懼籠罩……
這一切使剛在金融風暴中躲過第一輪金融襲擊的香港,面臨雙重考驗。
香港迴歸數天,亞洲就被金融風暴襲擊,華人主導的東南亞經濟遭遇史無前例的大浩劫,史上規模最大的無形財富大轉移也在“金融危機”表象下,在西方媒體大力推銷的“亞洲文化是罪魁禍首”的文化戰下,從華商手中流向華爾街、倫敦金融城的口袋中……
一切都是巧合嗎?
如同任何歷史事件的發生,總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總有人會以陰謀論看一切,也總有人把一切看做巧合。如此,世界迴圈往復地旋轉,人類歷史的悲喜劇也週而復始地重演。
此後,有關亞洲金融危機的詳情,各路金融專家、研究學者都著書立說、向公眾進行各種解釋……但這場金融風暴的實質究竟是什麼,卻遠非蓋棺定論之事。
這只是一場金融戰嗎?還是融合生物戰的金融戰?抑或是融合了金融戰與生物戰的文明戰?現代一體化戰爭在悄無聲息中露出了它猙獰的面目……
究竟是否存在一隻無形的手,在揮舞指揮棒,導演這些歷史性的大戲?為什麼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與2008年的華爾街金融危機中,西方政府、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國際組織都步調一致地採取了恰恰相反的態度與行為?“市場”那“看不見的手”是如何、又與誰的戰略利益天衣無縫地完美吻合?
從許多角度看,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是個教科書般的典型範例。對研究從那時至今、以及未來的金融衝擊都非常有參考價值。危機發生的細節已被數不勝數的媒體、學者所描述,這裡不再浪費筆墨,而要著重說說:究竟是誰?到底為什麼?有何黑幕?
拋開其它的不說,先看一下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前後一些主要人物、組織及國家的行動,這些問題就會不解自答。
比如,從90年代中期開始,亞洲多個國家被步步緊逼,被急迫地要求開放金融市場。
1997年11月,在加拿大溫哥華舉行的亞太峰會上,當東亞、東南亞正陷入金融危機的陷阱時,美國繼續一如既往地施加壓力,甚至比以往更加迫不及待地要求亞洲受害國開放。
華盛頓國際經濟研究所理事弗雷德·伯格斯坦就稱:“自由化與金融業的放松管制,對整個亞太的經濟發展至關重要。”
一個現象很值得深思:雖然美國以非同尋常的強硬態度與急不可耐的迫切感在全球推動 “自由化”,拆除對資金流動的管制,但它並沒有針對全世界提出這些要求,而是專門針對東亞、東南亞國家。
從90年代開始,美國不惜一切代價與手段,步步加大壓力,軟硬兼施地讓東亞、東南亞各國開放金融和資本賬戶管制,而且可以說是將全副注意力傾注在這個區域。
美國沒有對智利、沒有對印度、沒有對巴西、沒有對歐洲哪個國家施加如此壓力,而是全副精力、一門心思地向東亞、東南亞國家施加壓力。可以說,美國的打擊目標此時已十分明確、深思熟慮、一心一意。
從危機一開始,“管理”這場危機的兩大領銜者——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與美國政府就軟硬兼施地輪番施加壓力,落井下石般地要求亞洲各受害國完全開放金融市場。
這些舉動讓人匪夷所思,甚至讓世行的首席經濟學家約瑟夫·斯蒂格利茨也深感震驚。他忍不住記下了自己的感受:
“我很震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美國財政部要以如此的勁頭推動東南亞在危機中開放金融,儘管實際上並不存在一個理論與證據指出,這樣做有益於其經濟穩定,倒是有恰恰相反的事實。”
國際金融市場業內人都明白:在這個“危機”時刻,滾滾資金通常會傾瀉湧入美國金融市場,從而帶來廉價的信貸,並推動美國股市,拉動美國的經濟增長;與此同時,來自東亞、東南亞的龐大財富也會在這些國家被打得屈膝下跪後,被易如反掌地收進美國的口袋中。而且,這次金融風暴似乎是專門為東亞、東南亞國家設計的。
亞洲國家擁有高儲蓄率,相對穩定的政治、社會,幾十年突飛猛進的發展也使這些國家擁有相對較強的經濟應對能力,因而80年代拉美被債務陷阱襲擊的一幕,很難在亞洲國家上演。
但亞洲國家卻有一個容易被襲擊的短板:二戰後數十年間,亞洲國家採取“出口增長”的經濟發展模式,不僅嚴重依賴出口,而且面對貨幣急劇波動具有致命性的脆弱,尤其是這些國家的貨幣都主要與美元掛鉤。
實際上,及至克林頓政府入主白宮,各種花樣翻新的金融、貨幣危機技藝早已爐火純青,並屢試不爽。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不僅沉重打擊了亞洲諸多國家,也如同一場傳染病,蔓延至俄羅斯、巴西等國。這些國家的共同點,是資本市場對外開放。
亞洲金融危機清晰顯示了,允許外資輕易地、突如其來地自由進出一個主權國家,無疑是在埋下一個個定時炸彈,對於任何主權國來說,這都是一場遲早要爆發、難以控制的危機。
危機被引爆後,歐美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設計制訂了所謂“一攬子救援計劃”。
這些“救援計劃”附帶的條件是如此苛刻,是十足的“落井下石”,是一副副毒藥偏方,會讓亞洲國家在金融危機的同時,引發社會衝突與政治動盪。但“施救者”卻異常寧靜地坐觀這些國家社會動盪、戰火遍地燃燒蔓延。
泰國成為此次金融襲擊的首選目標,恰恰是因為它當時是這個區域最開放的經濟。經過多年的軟硬兼施,泰國當時被成功誘導進入“開放型”金融體制,而“開放” 則為泰國引入了一枚枚定時炸彈。
不僅僅是泰國,在多個國家,伴隨房地產價格飛漲的,是虛擬式繁榮泡沫,這些泡沫遲早要被捅破,而一旦被捅破,其經濟也必然會崩潰、社會必發生動盪。
當一個國家迫於壓力或被忽悠,而開放資本賬戶等金融領域時,實際上是在把國家推入一個致命陷阱:滾滾湧入的熱錢及短期信貸會如同天上掉餡餅一樣落到自己的門前,送到自己的嘴邊。
但這一切不過是一個個劇毒的致命誘餌:當目標國的金融業牢牢咬住這些誘餌後,就不可避免地會被死死釣住,隨即被拋入一個被事先埋好的災難性陷阱、被置於菜板上,等候屠夫們的血洗大屠殺。
為主人埋設陷阱、扮演屠夫的,是國際對沖基金、私募基金這些早已伺機待命出發的特洛伊木馬、定時炸彈大軍……
當襲擊來臨時,那些信貸、熱錢會被一聲令下,統一協調地紛紛撤回倫敦、紐約,留下受害者被置於案板上,等候他們的,是西方的血盆大口……
特別說明:截止到目前,中國只對外完全開放了經常性賬戶(也就是貿易和服務等),沒有完全開放資本和金融賬戶(也就是實體投資和股票、債券和外匯等),外國資本想要進入中國需要得到中國政府的稽核。中國還有外匯管制,沒有非常正當的理由,不是外資想離開就能離開的。
再回到1997年。
當時,緊隨泰國之後被置於屠宰板上的是印尼。
在西方“救援”和“指導”下,1997年印尼GDP急劇下降了20%,而這一切成為另一場社會危機的前奏……
再來說說亞洲金融風暴中的韓國。
當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為韓國設計了“一攬子救援計劃”,為韓國提供的“救援計劃”究竟是何神藥?
在“一攬子救援計劃”規定下,韓國強大的民族企業被迫股份化,轉製為西方式的股份公司,從而不得不依賴於發行股票、接受西方資本大鱷們的控制,不得不求助被歐美掌控的資本市場!
如此一來,便陷入國際資本、貨幣、證券市場的輕易操縱與控制之下。
經濟上的打擊僅是第一步。
針對這些民族企業,還有一個被西方廣泛傳播的妖魔化形象:這些大型企業與政府關係太密切,不利於自由競爭,這正是“亞洲文化的弊端”、是此次金融危機爆發的“文化與社會根源”等等。
在亞洲金融危機被引爆後,這正是西方主流媒體、政府幾乎異口同聲強調的結論。
這分明是黑白顛倒,美國自己的大型企業、跨國公司巨頭無一不是靠政府扶持起來的。但輪到韓國,輪到亞洲,則成了“文化弊端”,成了必須被拋棄的發展模式。這就是隻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
這也是為什麼中國的國企同樣成為他們的攻擊目標的原因,在他們的既定戰略中,與韓國的民族企業一樣,中國的國企也必須被瓦解、削弱、根除。
實際上,開啟東亞的金融大門,從內部滲透、左右東亞的命脈,早在20世紀80年代就正式開始了,其聚焦點就是——開放資本賬戶管制、金融市場自由化。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要求韓國採取全方位“門戶開放”措施,允許外國資本自由進出——包括銀行業及商業領域。從1997年12月15日開始,將外資對韓國公司擁有股份的上限從26% 提升到50%等等。
被迫“開放”,進行“自由化”改革後,韓國損失慘重。
至2004年 6月,“韓國”企業中,西方資本擁有三星電子58.1%的股份,現代汽車公司的55.3%,浦項制鐵公司70.1%……
金融領域的外資控制尤為顯著。
1998年東南亞經濟危機以後,美國資本大量參股韓國銀行:目前韓國九大行中的住宅銀行、國民銀行、第一銀行、新韓銀行和韓美銀行的外資持股比例均超過了51%。
1997年後,對韓國的外國直接投資也急劇增長,從1990年的8億美元急劇增加到1999年的155億美元。
這些“投資”的絕大多數,是用於吞併韓國戰略性企業與金融資產,其中許多是透過資產剝離的方式廉價出售的,足以引發政府與法律部門進行犯罪調查。
當然,這種調查是絕對不被允許的。
毫不誇張地說,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對於西方公司來說,是一場規模難以想像的金融大宴,它們也如狼似虎一般地貪婪吞食、無情宰殺、獵捕一個又一個亞洲龐大的財富庫。
無論從何種角度看,這都是場史無前例的財富大掠奪,其難以想像的龐大規模,可從一些數字中窺見冰山一角。如:僅1998年前五個月,美國公司收購的亞洲企業數量,是它們此前一年全年收購總數的兩倍。
歐洲也加入了分餐大宴,尤其是來自英國、德國、法國、荷蘭等公司,近乎瘋狂地對亞洲獵物進行屠宰。位於美國的證券資料公司 Securities Data將這場針對亞洲資產與財富的大掠奪興奮地稱為“歷史性的時刻”。
1997年西方金融戰成功實施的前後始末到底是什麼?
20世紀90年代中期,蘇聯及東歐共產黨勢力徹底瓦解崩潰,對於歐美“自由世界”戰略大師們來說,要獲取對世界的全方位主宰,還有兩大潛在對手與路障——伊斯蘭與華夏,必須不惜一切手段清除這兩大路障。
當克林頓入主白宮時,這正是美國戰略者面臨的最急迫的任務:如何不惜一切手段打擊、消除這兩大潛在路障?
正在這時,適應新一代戰爭的一體化作戰手段、在新一代軍事大革命中崛起的一系列秘密殺手鐧武器也趨於成熟完備:融合生物基因生態戰-地球物理戰-腦意識控制戰-心理戰-政治顛覆戰-經濟戰-文明戰於一體的現代無形戰爭的時代,靜悄悄地拉開了帷幕。
在這場以“文明戰”為核心的終極大戰中,亞洲發展模式是絕對不允許主導地球的。歸根結底,金融、財富等都不過是工具,民族之間最核心的博弈是文明。
這裡要說一說亞洲的“特殊性”。
對於西方“自由世界”來說,來自東亞、東南亞的威脅與挑戰格外緊迫的原因是:
儘管由於歷史的因素,該地區長期被“分而治之”謀略製造出支離破碎的政治版圖,但整個區域的經濟、資本日益整合成強大的、生命力極強的互補性網路。這個網路雖然被日本力量滲透,但除了日韓,該區域所有國家和經濟體,都是華人主導經濟,這一切又將整個地區與中國大陸聯結成不可分割、日益整合為一體的文化、經濟統一網路。在這個網路中,華夏文明長期佔優勢,並向世界提供了一個非基督教西方的替代選擇——華夏文明影響下的文化、價值觀、思維方式、生活方式。而這是整個基督教西方世界最為恐懼的惡夢,必須不惜一切代價與手段終結之、根除之。
海外華人的龐大財富、他們在各種逆境中靈活而頑強生存發展的非凡生命活力,構築了一個獨特的無形帝國,透過一個盤根錯節的關係網維繫著。這一切提供了一種獨特的個人關係網與金融紐帶網,使這無形帝國成為一股強大的力量,一個沒有國界、也沒有炫耀張揚國旗的帝國。
二戰結束後,數百個大型聯合企業從東南亞悄然崛起,幾乎所有都被華商擁有或掌控著。歷史學家斯特林·西格雷夫曾在其《環太平洋的主人》一書中,將華商冠以如此殊榮的稱號。
對於西方“自由世界”來說,華夏文明的威脅在於:不僅東亞、東南亞地區幾乎都是由華人主導經濟,即使韓國日本也與華夏文明有著一衣帶水的關聯。
因此,在這個地區引發任何大規模的金融危機,不僅會打擊當時正如日中升的 “亞洲價值觀”“亞洲文化”“儒家文化傳統”以及隨之而來的民族自信心,為21世紀的文明決戰鋪路,而且也會對中國予以重擊,最大程度地減少、摧毀海外華人的財富庫,窒息向中國輸送投資源泉的財富咽喉,遏制這個區域以華夏文明為中心迴歸世界主導的傳統地位。
由此,我們看到,亞洲金融危機之後,海外華商的龐大財富流向西方,流向大西洋兩岸,集中於大西洋兩岸的控制下。西格雷夫筆下“環太平洋的主人”,儘管擁有數千年優秀的資訊傳遞體系、聰明過人的才智與技藝、吃苦耐勞的性格、靈活機敏的應變能力,最後還是成為大西洋捕食者們肆意屠宰的獵物。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中,不被主流媒體提及的最大無形受害者群體之一,是雄居東南亞數個世紀的海外華商。危機後,華商基於互信與家族紐帶的傳統被嚴重削弱。
可以說,對於基督教大一統西方的千年大業來說,這次危機不僅沉重打擊了基督教西方世界的頭號威脅,更重要的是在政治、經濟、文化、心理上都改變著整個華夏文明圈乃至整個世界。
只有從這個大背景下,才能更好地理解危機中及危機後,西方主流媒體、學術界那難以掩飾的欣喜與一片興奮。一場宣傳公關大戰也似乎早已準備好劇本臺詞,把此次亞洲危機描述成“亞洲人的文化與社會根源”、亞洲人的“經濟管理無能”、亞洲國家的“外匯管理無能”、亞洲“不透明的腐敗政府“、亞洲文化的“裙帶主義”……
一場步調一致的妖魔化宣傳戰,繪聲繪色地向全世界強化著一個形象:以華夏文明為核心的亞洲文明與價值觀、亞洲的經濟與社會發展模式破產了,以英美為核心的發展與“新自由主義”模式才具有普世性。
在構建全球無形帝國之路上,在一場場戰爭的設計、製造中,被歐美主導的全球主流媒體與學術教育網路作為戰爭同謀,扮演了西方戰爭機器上不可缺少的角色。在現代金融戰、生物基因戰中,媒體的角色更加重要。
西方一體化戰爭模式出現後,每個戰場、每個前線無論以何種面目出現,文化戰、文明戰、資訊輿論戰、心理戰無一不天衣無縫地融為一體。
這也是為什麼表面上看似乎僅僅是金融戰,改變的卻是被襲擊國家整個的社會、政治、文化結構及民族自信心與自我意識。這種戰爭以控制整個國民的身心、意志,最終“不戰而屈人之兵”為終極目標,這才是一切戰爭的核心所在,是一切戰略設計與實施的重中之重。
結語:
當前,大國博弈已進入白熱化狀態,表面上看是國與國之間的博弈,實則是西方資本聯盟與他們最畏懼的對手——華夏文明之間的終極對決。
他們的殺手鐧,不光是常規的軍事手段,不光是病毒與農業災害,不光是極端氣候與地震海嘯,也不光是洗腦,而是這所有手段的一體化,並配備一張覆蓋全球各個角落的龐大網路。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完美驗證”了這一點。
我們必須時刻警惕、枕戈待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