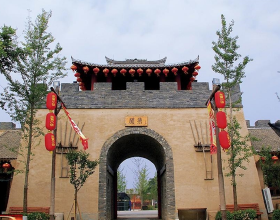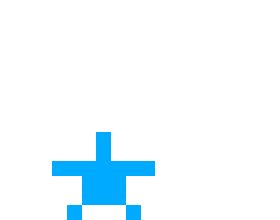有兩個字一直伴隨著我,一個是“死”,一個是“苦”
孫清湘
1950年11月,我隨部隊奔赴朝鮮戰場。那時,我是一名剛剛入黨一年多的新黨員。從踏上朝鮮戰場那一天起,就一直有兩個字伴隨著我:一個字是“死”,一個字是“苦”。
死,主要來自敵方飛機的空襲。
剛入朝鮮不久,我就差點丟了性命。那天,有兩架敵機朝我軍駐紮的地方飛過來。他們飛越一座山峰,再調過頭來,各朝我們丟了一枚炸彈。我清清楚楚地看到兩枚炸彈朝地面飛來,趕緊找了一個地方臥倒。兩枚炸彈在距我不到十米的地方先後爆炸,山石泥沙像暴雨一般朝我身上砸來,整個身體有一半都被掩埋了。幸好我臥倒的地方地勢比較低,所以才毫髮無損。
還有一次差點丟了性命,發生在半年之後。當時我護送一車傷員轉往後方醫院,中途因公路被敵機攔腰炸斷而無法前行,於是司機將汽車駛離公路,沿著一條羊腸小道緩緩前進,想找個防空洞躲藏,第二天再走。途中因小路難行,司機開起了大燈。大燈剛亮,天空中就來了一梭子機槍子彈。山坡上頓時濺起了一片火花。我坐在汽車的最後面,左側挎包上拴茶缸的繩子竟被打斷了。
苦,主要來自冰雪和嚴寒。
我所在的兵站醫院,每天都會送來大批傷員。戰士們換下來的敷料都是血跡斑斑的,需要我們洗乾淨後消毒,以備再用。洗敷料的小河結著厚厚的冰層,砸開冰層伸進這樣的水中,兩隻手的感覺開始是冷,後來是疼,再後來是木,接下來就什麼感覺也沒有了。對於這樣的苦差事,我總是搶在前頭,因為我是新黨員,應當經受這樣的鍛鍊。
在戰場上,我還接到過意想不到的任務——讓我到手術室搞麻醉。因為當時需要做手術的傷員太多,但是卻沒有足夠的麻醉醫生。領導要我頂上去。
經過麻醉醫生一分鐘的培訓,我上崗了。我拿起金屬網罩,遮住傷員的口鼻,在網罩上鋪幾層紗布,再拿起滴瓶把麻藥緩緩滴在紗布上,就這樣一面滴,一面要求傷員跟我一起數數,當傷員不再跟著數的時候,醫生就可以給傷員做手術了。在麻醉過程中,我當然還要隨時觀察傷員的情況,並向醫生報告。在隨後較長的一段時間裡,我一直在手術室工作。人們戲稱我是“一分鐘培養出來的麻醉師”。
資料來源:上海市軍隊離休退休幹部活動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