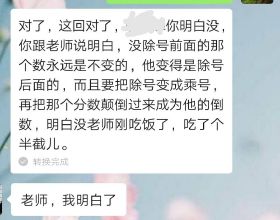在金軍第一輪大掃蕩結束後不久,宗澤就去世了。群龍無首之際,不少人希望宗澤的兒子宗穎站出來主持大局。
自宗澤卒,數日間將士去者十五,都人憂之,相與請於朝,言澤子宣教郎穎嘗居戎幕,得士卒心,請以繼其父任。
宗穎對此自然是意動的,但對於趙構而言,這可不是什麼好訊息。
宗澤活著的時候,就一直與南宋中央政府分庭抗禮,現在好不容易盼來轉機,再弄個父死子繼的局面那還了得?
因為這個原因,所以趙構很快頒佈了新的人事任命。讓杜充接替宗澤的位置,宗穎則擔任杜充的助手。
會充已除留守,詔以穎直秘閣,起復,充留守判官。
對此宗穎老大不樂意,但他既沒有宗澤的霸氣,也沒有宗澤的實力,自然無力反抗趙構,只能接受這個任命。
後來,宗穎一度與杜充分庭抗禮,但是總處於劣勢,最後只好回家給宗澤守孝去了。
起復留守判官宗穎,屢爭不從,力請歸持服。
看到這段歷史時,我總是忍不住在想,如果宗澤把北方的抗金力量整合得再充分一些,趙構還能空降一個人取代宗穎嗎?估計很難。
一切是顯然的,只要宗澤把北方抗金力量充分整合了,看到有人敢在汴梁城內坐在宗穎前面,就算宗穎沒意見,廣大的愛國軍民也不會接受啊。
此前不久,趙構曾空降一個官員到某地當老大,這個官員拿著趙構的委任狀卻無法赴任,因為當地老百姓都紛紛表示,他們還想讓從前的老大繼續管理這個地方。
面對此情此景,趙構當然是怒不可遏,於是就把那個從前的地頭蛇貶官三級,讓他繼續留任,又給那個空降的官員另尋了一個地方。
對此,高階文職官員就提出了意見:那個地頭蛇算怎麼回事?
如果他做得對,我們就應該大力表彰,因為一個地頭蛇離任時,被當地老百姓紛紛挽留,這證明他是一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好官員啊。這樣的官員,我們為什麼要貶他三級呢?
如果說他做的不對,貶他三級就能了事?因為一個地頭蛇煽動老百姓鬧事,讓官員拿著中央政府委任狀都無法赴任,這該砍他的頭啊。
對此,趙構也只能顧左右而言它。
在那種兵荒馬亂的年代裡,哪有什麼道理可講呢?杜充能越過宗穎,是因為北方各勢力比較複雜,而且杜充也是牛氣沖天的人物,否則就算拿著趙構頒發的委任狀,杜充也無法取代宗穎的地位。
杜充風光無限時,可謂南宋軍界第一人,連岳飛都是他的下屬。
杜充南渡時,劉光世、韓世忠也明確劃歸到了杜充屬下。
張俊保持著獨立地位,那是因為張俊由趙構直接指揮,而張俊當時的軍界地位顯然比杜充低多了。
問題是,杜充後來越混越差勁,實在讓人難以想象當年的風光了。在金軍深入江南時,杜充突然對前途喪失希望,於是在關鍵時候投敵了。
而在勸降杜充的時候,完顏宗弼開出的條件是:“你可以當中原皇帝。”
可是在日後的競爭過程中,杜充沒能爭過劉豫、張孝純,所以越混越差,慢慢地被人所遺忘。
因為杜充蓋棺定論,是一個可恥的漢奸,而且還不是坐頭把交椅的大漢奸,所以歷史書常常把他寫得極為不堪。
可實際上,當時的杜充顯然是一個名望很高的人,否則他怎能接替宗澤的位置呢?又怎能在率軍南撤後,依然成為了劉光世、韓世忠等人的上司呢?
杜充接替了宗澤的位置之後,北方局勢越來越惡化。很多人總認為,這是杜充能力太差。實際上,北方局勢不斷惡化,幾乎是一種必然的趨勢。
在宗澤坐鎮汴梁的一年時間裡,整個北方已讓金軍從北到南、從東到西徹底打穿了,宋國失守的重要城池,伸出兩把手也數不過來。
宗澤死後,這種趨勢自然還會繼續,只要金軍再發動一輪大掃蕩,整個北方地區還會有更多城池淪陷。
在這種背景下,就算宗澤活著,與杜充相比也不過是五十步與百步之別罷了。
而且,對汴梁留守而言,當時還有一個危機。那就是經過一年多時間的整合,北方的義軍、流寇變得越來越強大,所以開封留守的直屬軍隊想駕馭他們,自然是越來越困難了。
在這種背景下,以杜充為代表的政府軍與地方武裝的矛盾,自然是越來越難以調和。事實上,就算宗澤活著,這種矛盾也是難以避免的。
在接替宗澤後不久,杜充就與張用、王善等義軍首腦發生了大火併,結果就是張用、王善變成流寇了。
據說,張用、王善變成流寇,是因為杜充打擊他們愛國的熱情。實際上,這是因為他們勢力越來越大,所以不想受大宋政府的約束了。
在面對杜充時,張用、王善還算比較團結;可在與杜充翻臉之後,張用、王善之間也有產生了分歧。
張用認為,我們雖然脫離了東京留守的控制,但我們也是義軍啊。既然是義軍,我們就應該到宋奸控制的地區尋找落腳處,如果我們到宋軍控制的地方尋找落腳處,那我們就成流寇了。
王善認為,現在天下大亂,咱們倆合作好了,誰敢說,咱們一定不能稱王稱霸、成佛成祖呢?換而言之,這種兵荒馬亂的年代,咱們放手幹吧。
於是善整兵欲攻淮寧,用不可,曰:“吾徒所以來,為乏糧耳,安可攻國家之郡縣?”善曰:“天下大亂,乃貴賤、貧富更變之時,豈止於求糧而已!況京城已出兵來擊我,事豈無名乎!”
後來,張用被王善說服,雙方一起南下,準備在宋軍控制的地區分一杯羹。
問題是,宋軍控制的地區也不容易奪取啊。所以,張用、王善在攻打淮寧時,被杜充派軍趕跑了。在這種背景下,張用、王善只能繼續向南轉進。
善圍淮寧久之,東京留守杜充遣都統制陳淬來援,善乃退。
許多人總喜歡說,南下的人很多,所以證明這些人都心向大宋。可事實上,眾多南下的人懷著怎樣的想法,恐怕只有他們自己知道。
所以,李成、張用、曹成、李宏、馬友等人南下後,那是大有席捲江南的架式。
事實上,北方的許多義軍、流寇,都是想著成佛成祖、稱王稱霸,或是曲線上位。
先趁亂拉起一支隊伍,能變大變強自然最好,退一步,被誰招安也得給他一個大官當啊。再退一步,就算死了也是風風光光地活過一場呀。
在我看來,張用等人一個勁兒地向南轉進,絕不是因為他們深愛大宋,而是因為北面的金國太強大,想在金國的空隙中變大變強太難。南面的大宋相對較弱,在大宋的空隙中尋找變大變強的機會,應該比較容易。
這些軍隊為什麼要脫離杜充呢?因為杜充最後投降金國,所以通常的說法自然是杜充太壞,所以大家都不跟他混了。總而言之,如果宗澤活著,大家肯定不會這樣做的。
其實,主要是因為在金軍的掃蕩下,大家的生存空間越來越窄,引發了一個重要的問題,那就是後勤的問題如何解決?
最簡單而言,大家一說北方抗金形勢大好,有一百多萬義軍。問題是,這一百萬義軍吃的喝的都從哪裡來呢?
在金軍接連大掃蕩前,北方地區的官府、老百姓面對這些手持槍桿子的大爺,自然都得供他們吃,供他們喝。
問題是,隨著宋奸越來越多,他們再想吃喝,地方就越來越窄了。
一切是顯然的,宋奸越來越多,而且又有金國保護,義軍想到他們的地盤上混吃混喝,難度就會變得越來越大。
所以,從表面上看,汴梁附近的軍隊越來越多,這是一件好事。問題是,他顯然也是一個麻煩事,那就是這樣多的義軍,聚集在一個狹小的空間裡,吃什麼、喝什麼?
我前面分析過,宋軍的後勤是透過文官系統籌集的,義軍的後勤則是透過自己籌集的。
開始,金國對北方的控制力很弱,義軍找那些與金軍關係曖昧,甚至是掛起金軍大旗的地方籌糧很容易。在這種背景下,他們雖然是自行籌糧,也可以說自己是義軍。
問題是,隨著宋奸越來越多,抱團的規模也越來越大,義軍自然不敢隨便搶他們的糧了。
在這種背景下,大宋政府的文官系統在自己的控制範圍內籌集到了糧草,應該先保證誰的需要呢?自然是先保證宋軍啊。
對於大宋政府這種做法,其實是無可厚非的。可這樣一來,義軍自然要生氣了。因為,大家都是抗金的隊伍,憑什麼政府軍就吃得好、穿得好、裝備好,我們卻連基本的後勤補給也無法保障?
在生存壓力下,這些義軍難免會想把手伸進大宋政府控制的地區。問題是,這種事不僅是杜充不允許,就是宗澤活著也不可能允許啊。
許多地方,到底是國統區還是敵戰區,實在難以說清楚。因為北方廣闊的地區,常常就是宋軍、金軍、偽軍、義軍、流寇你來我往的地區,這些地區到底算誰的?本身就難以說清楚。
但有一點可以肯定,在南宋政府看來,許多地方就是國軍控制的地區,所謂的義軍敢到這種地方自行籌糧,本身就是如同造反。
問題是,眾多義軍首腦都領著幾萬小弟在道上混,總得管他們吃飯吧?
更難處理的問題是,到金國保護地區籌糧,常常會受到報復,到南宋保護地區籌糧就等於造反,你叫他們怎麼辦?
張用、王善叛亂的結果,就是他們以後可以肆無忌憚地到南宋保護地區搶糧了。眾多義軍與杜充的矛盾,以及脫離杜充的主要原因,其實就在這裡。
因為,繼續跟著杜充混,籌集後勤就受到了約束。在這種背景下,用各種高大上的理由與杜充脫離關係,再做一些無法無天的事,相對就容易許多。
只要和杜充脫離了關係,以後想到哪裡籌糧,就可以到哪裡籌糧。
在這種背景下,各種軍隊所過之處如同蝗蟲過境,就算他們不放縱軍隊搶劫,所過之處管他們吃飯,也是一種驚人的負擔。
於是用駐於確山,連亙數州,上自確山,下徹光、壽,號“張莽蕩”,鈔掠糧食,所至一空。
甲午,張用與馬友分軍屯確山,麥且盡,眾皆乏食,乃議復往山東。
杜充壓制打擊義軍的行為,顯然是得到了南宋中央政府授意與認同,否則杜充南渡後,就不會受到南宋中央政府的空前重用。
要知道,杜充南渡後,既是地位最高的軍事統帥,又是南宋執政官。在南宋初年,這種地位可以說是獨一無二的。
只是杜充後來投降了金國,所以這種問題的是是非非,自然都歸到了他的頭上。
其實呢,在當時的大背景下,無論誰坐鎮汴梁,也會無法阻止非政府武裝越來越大,也無法阻止非政府武裝蠢蠢欲動地向南轉進。
面對北方金國的壓力,眾多非政府武裝就是一個勁兒地想向南轉進並轉變為流寇,原因非常簡單。
首先,南方的經濟相對完好;其次,就如韓世忠圍剿苗劉兵變時所說,面對金軍我不敢誇海口,但是打個宋軍,我還是非常有自信的。
勝非退,見光世已下於都堂,世忠曰:“金人固難敵,若苗傅,但有少許漢兒,何足畏者!”
都把南宋當軟柿子捏,南下自然是順理成章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