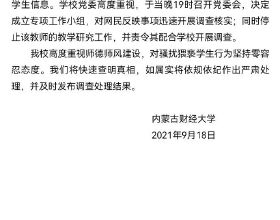記者 | 林子人
編輯 | 黃月 姜妍
著名歷史學家、耶魯大學榮譽教授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於當地時間2021年12月26日逝世,享年85歲。據美聯社報道,史景遷在位於康涅狄格州西漢文市的家中去世,史景遷的夫人、耶魯大學教授金安平(Annping Chin)稱其死於帕金森病的併發症。
史景遷生於英國,在劍橋大學獲得學士學位後前往耶魯大學求學,師從芮瑪麗(Mary C. Wright),於1965年獲得博士學位。期間中國史學前輩房兆楹取了他姓氏的首字母贈予他中文名“史景遷”,寓意為景仰司馬遷,以之為楷模。博士畢業後史景遷留校任教,這位以“擅長講故事”聞名的歷史學家在半個多世紀時間裡已是享譽全球的中國史巨擘之一,他主攻清代以後的文化與政治史,對中西文化交流有濃厚興趣,一個貫穿於多部作品中的主題是西方人如何看待中國,試圖“改變中國”,但又不可避免地遭遇挫敗。
自1974年以來,他完成了14部有關中國的歷史著作,其中12部已於2019年由理想國引進簡體中文版,包括《前朝夢憶》《康熙》《雍正王朝之大義覺迷》《太平天國》《王氏之死》《大汗之國》《改變中國》《胡若望的疑問》《曹寅與康熙》《利瑪竇的記憶宮殿》《中國縱橫》《追尋現代中國》。1974年,《康熙》首次出版在美國引起轟動,其兼顧知識性和趣味性的敘事手法深受讀者歡迎。他寫作的《追尋現代中國》從晚明(1600年)開始追溯中國進入現代的歷史程序,被費正清譽為“不世出的著作,下一代裡難有出其右者。”
歷史學家王元崇表示,《追尋現代中國》當年衝上《紐約時報》閱讀榜單是此前沒有任何一位歷史學家達到過的成績。這種面向公眾的歷史寫作雖然在歷史學界引起了一些爭議,但的確成功激發了大批非專業讀者對中國史的興趣。迄今為止,《追尋現代中國》依然時被美國大學廣泛使用的中國史教科書。史景遷的第一位博士生鄭培凱稱,“1980年以後,美國人、西方人想要了解中國,一個很主要的來源,就是看史景遷寫的書。”
列文森:他永遠改變了清史研究,他像天使一樣寫作
2004年,當史景遷當選美國曆史學會(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會長時,他的摯友兼同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中國史教授魏斐德(Frederic E. Wakeman Jr.)曾以《史景遷的誕生》(The Making of Jonathan Spence)為題發表演講,講述史景遷的人生經歷與職業道路。
1936年8月11日,史景遷生於英國一個知識分子家庭。他的父親畢業於牛津大學和海德堡大學,德語流利,在出版社和畫廊工作,曾為約瑟夫·康拉德的圖書編輯。他的母親熟讀法國文學。他的兩個哥哥分別是古典學者和化學工程師。他的姐姐不僅擔任電影製片工作,而且是法語、德語和義大利語專業譯者。
13歲時,史景遷進入溫切斯特學院(Winchester College),在中學時代他閱讀面廣泛,喜好創作詩歌,但認為比起創意寫作者自己更適合當一個文學評論家。在進入劍橋大學卡萊爾學院後,史景遷在知識分子圈中如魚得水,他不僅是文學雜誌《格蘭塔》(Granta)的聯合編輯,而且從大學二年級開始擔任劍橋大學學生報紙《大學》(Varsity)的編輯。年輕的史景遷曾想當一位小說家,但在意識到自己“無甚可說”時,他轉向寫作滑稽模仿作品。直到他於1959年獲得學士學位,這位未來的歷史學家都對自己的志向沒有明晰的想法。
在梅隆獎(Mellon Fellowship)的資助下,史景遷以卡萊爾學院最優生的身份前往耶魯大學交流,一門芮瑪麗(Mary C. Wright)的課改變了他的學術道路,讓他決定投身中國研究。當時芮瑪麗和她的丈夫、同樣是中國史學者的芮沃壽(Arthur F. Wright)剛剛從斯坦福大學跳槽至耶魯大學。據費正清回憶,芮瑪麗很快發現這個畢業於溫切斯特學院和劍橋大學的英國年輕人具有無以倫比的學術天分。透過芮瑪麗的介紹,史景遷前往澳大利亞跟隨房兆楹學習。在房兆楹的介紹下,史景遷成為最早進入臺北故宮接觸檔案資料的西方學者,他利用這些檔案完成了博士論文,該論文以《曹寅與康熙》為標題於1966年由耶魯大學出版社出版。據魏斐德回憶,他的導師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在讀到這本書時興奮不已,“(史景遷)永遠改變了清史研究,而且他像天使一樣寫作。”
《曹寅與康熙》出版當年,史景遷成為耶魯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1968年,他升任副教授。1971年,在出版了第二部作品《改變中國》後,他升任教授。1974年和1978年,史景遷前後出版了兩部引起巨大反響的作品《康熙》與《王氏之死》。在《康熙》中,史景遷梳理了眾多不同來源的史料,以第一人稱的口吻,將康熙的一生娓娓道來。因為這一生動且不拘一格的敘述方式,《康熙》在普通讀者當中也引起了廣泛好評。在《王氏之死》中,史景遷以山東郯城地方誌、黃六鴻的《福惠全書》、蒲松齡的《聊齋志異》為史料基礎,探討清初農民的生活環境與想象空間。這本書甫一出版就登上了多數美國大學的中國史閱讀書單。在魏斐德看來,《王氏之死》讓讀者難得地獲得了一種瞭解清代底層社會的視角,向讀者介紹了一個更加生動豐富的中國。
魏斐德對史景遷研究史料的眼光和歷史寫作的風格讚歎有加,他認為史景遷在捕捉歷史細節方面目光如炬,很特別的是,往往是某個影象先抓住了他的想象力,然後他能用紮實的史料把那個在他腦海中揮之不去的景象付諸筆端。據魏斐德回憶,他曾有一次與史景遷散步的途中問起對話正在寫什麼,史景遷眯起眼睛,眼神彷彿投擲到了某個遙遠的地方,喃喃道,“我發現了一個很棒的資料來源,關於一位王氏女子的謀殺案,一具蜷縮在雪中的屍體……”魏斐德還指出,史景遷特別關注新發現的檔案材料的使用,在這一方面《太平天國》是一個絕佳案例。在該書前言,史景遷特別指出這本書的寫作基於長期被埋沒在大英圖書館、最新發現的太平天國相關材料。
鄭培凱認為,得益於史景遷自己的歐洲文化和語言背景,他從學術生涯早期開始就特別善於在中國史研究中運用西方史料。比如在撰寫《利瑪竇的記憶宮殿》時,他會閱讀義大利語和法語史料;在撰寫《王氏之死》時,他會閱讀法語和義大利語的蒲松齡著作譯本,在使用原始中文材料的同時也參考各種歐洲譯本;在撰寫《胡若望的疑問》時他查閱了法國國家圖書館和梵蒂岡的資料。關於史景遷的多國語言能力,鄭培凱講述了一則趣事:1980年,錢鍾書隨中國社會科學代表團到美國訪問,在耶魯大學見到了史景遷。“他們兩個相會,都是才子型的嘛,這怎麼辦呢?兩人見面,用什麼語言對話呢?中文還是英文?最後講的是法文。”
韓書瑞:他很會培養學生,給予學生充分的自由
至2008年從耶魯大學退休,史景遷為海外中國研究領域培養了大批知名學者,包括彭慕蘭(Kenneth Pomeranz)、魯樂漢(John Delury)、柯嬌燕(Pamela Kyle Crossley)、韓書瑞(Susan Naquin)、高家龍(Sherman Cochran)等。
1970年,芮瑪麗因癌症去世,史景遷代替自己的老師,帶領韓書瑞、高家龍等一大批研究明清近代史的師弟師妹攻讀博士學位。鄭培凱說,“他們都覺得史景遷實在了不起,在指導他們發展自己的學術上有很大幫助。”
據韓書瑞回憶,她到耶魯報道的第一天就有人告訴她要去上史景遷的近代史課,上課一週後,韓書瑞就改變了研究方向,從中國古代史轉向中國近代史。韓書瑞現任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系主任、歷史系教授,在清史研究方面成就斐然,她的著作《千禧年之亂:1813 年的八卦教起義》、《山東叛亂1774 年的王倫起義》、 《北京:廟宇與城市生活》等在學術界均有著廣泛的影響。
韓書瑞表示,雖然在擔任自己的導師時史景遷還很年輕,但他很會培養學生,給予學生充分的自由度。據她回憶,在她攻讀博士學位的時候,中國史圈內最有權勢的兩位教授之一就是芮沃壽,他們手頭掌握了大量的研究經費,韓書瑞笑稱和他們的學生比起來史景遷的學生都是“窮親戚”,但日後是史景遷的學生們取得了更大的學術成就。史景遷的文筆和對歷史中的人的關注深深感染了韓書瑞:
“(史景遷)的英文很棒,雖然我不會跟他一樣,可是願意看他寫的漂亮的英文,並試著寫好……他對歷史中的人那種持久的關注,他的書裡面寫的都是人,你翻開他的書,馬上會碰到人。他覺得人是最有意思的。”
除了輔導博士生之外,史景遷還曾是耶魯大學最受本科生歡迎的老師之一。根據耶魯大學的規定,所有教授都必須給低年級本科生開設通識課。此類通識課通常就是每週一次的面向背景多元、專業知識有限的學生的講座,要求兼顧知識性和趣味性。鄭培凱回憶稱,在他擔任史景遷助教的時候,一個通識課班上還只有60多個學生。十年後當他回校探望史景遷,導師向他“抱怨”稱選課的學生多達700多個,恐怕要20個助教才來得及批改卷子。
當史景遷於1990年出版《追尋現代中國》,廣大美國讀者得以一窺他的課堂風格——直至今日,這本書都是是美國大學最常用的中國歷史教科書,而它同時也是一本在美國普通書店都有售賣的暢銷書,向美國大眾介紹了一個更復雜多面的中國。
鄭培凱:他對中國人有一種歷史的同情,比別的所謂漢學家要多
史景遷的獨特治史風格在漢學界引起了不少爭議,他的作品幾乎部部暢銷,也讓一部分歷史學家不以為然。歷史學家王元崇曾在接受介面文化採訪時將史景遷和通俗歷史小說家二月河比較,“雖然他對清史的理解可能和二月河都沒法比較,但中國國內有大批的讀者追捧史景遷,另一方面我們很多人又不太看得起二月河,這個問題發生在哪呢?”
鄭培凱在接受“上海書評”採訪時回應過史景遷是否會誤讀文言文的問題。他認為,或許和中國學者相比,史景遷的文言文水平是沒有那麼好,但他的優勢在於他能夠使用多國史料相互參照。一些漢學家聲稱史景遷不會中文更是無稽之談。鄭培凱認為,史景遷雖然會運用想象去彌補歷史的縫隙,但他的每一個“想象”或者文學性描述都是有紮實的歷史依據的,他非常清楚自己從事的是歷史創作而非文學創作。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他對沒有紮實史料支撐卻提出突破性觀點的歷史作品的批評是非常嚴厲的。“比如有兩本書,一本是《黃金之城》,一本是《1421》。像這種時候,他謹慎當中還蠻決斷的,‘根本是胡說’,他就敢這樣講。”
“他的學術地位我想可以這樣定:他作為一個歷史學家,把一些涉及中國歷史學的研究探索重新提出來,以明暢的文字敘述清楚,探討近代中國的歷程該如何認識,”鄭培凱說,“有人批評他偶爾會誤讀了中文材料,我看也難免,人非聖賢,不是說什麼都百分之百對的。他處理的歷史題材,一般都透過具體的個人或事件,涉及如何理解中國傳統的歷史環境,而比較不太進行特定的專題探索。他也會爬梳史料,找出過去史家不太注意的材料,但總是為了說清楚具體歷史事件發展的關鍵,而不是專為了從事歷史考據。”
在鄭培凱看來,史景遷“對中國人有一種歷史的同情,比別的所謂漢學家要多”。他在《追尋現代中國》第一版序中的一段話溫柔地流露出了他的憐憫,理解與共情之心:
“我們可以看到,中國尋常百姓在惡劣甚至瀕臨絕望的環境中,往往仍掌握自己的命運,,投身對抗國家力量。我們可以認識到,1644年、1911年,還有1949年,對現況的絕望和緬懷夙昔的情愫,是如何與展望未來的熱切之心彼此融匯,進而粉碎既存的秩序開啟了一條通往新時代的不確定之路。”
2014年,史景遷曾到訪北京。在接受《中國新聞週刊》採訪時,他說,“我想,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難題。這是一個無比複雜的時代,資訊傳播和分享變得如此迅速,環境汙染、資源短缺、恐怖主義興起,人類比任何時候都更加極端和躁動。我們整個人類需要克服這些。”
參考資料:
【美】史景遷.《追尋現代中國:1600-1949》.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
《講故事的歷史學家:史景遷的寫作、史觀與道德立場》,介面文化
https://www.jiemian.com/article/3414582.html
《【專訪】歷史學家王元崇:屈辱史觀會對新一代的集體記憶產生負面影響》,介面文化
https://www.jiemian.com/article/5574665.html
《美國漢學家史景遷:治理中國是件太複雜的事情》,中國新聞週刊
https://www.chinanews.com.cn/gn/2014/03-31/6011416.shtml
《用新材料講新故事——韓書瑞教授訪談錄》,《史林》2005年06期
《紀念史景遷先生|鄭培凱談史景遷和美國漢學》,上海書評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5MDE1NzAwNg==&mid=2650808041&idx=3&sn=787f58614f1917af133c6ef119835e9b&chksm=8bfb4448bc8ccd5e44b680fcf6ab31fb0173ca110c620c5ad70c6213c5bcf5d8bf9c41a89248#rd
“The Making of Jonathan Spence,” HUMANITIES, May/June 2010, Volume 31, Number 3.
https://www.neh.gov/humanities/2010/mayjune/feature/the-making-jonathan-sp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