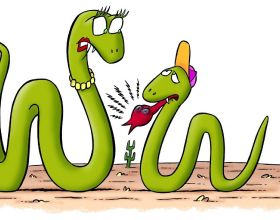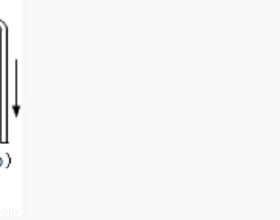我的父親楊守沫(1917——1994),原籍雲南省陸良縣馬街鎮,1937年參加革命,1939年加入中共,經組織派遣在國民黨滇軍中10年地下工作。1948年在錦州解放時作過重要貢獻。1950年參加抗美援朝戰爭,曾以中國人民志願軍代表身份參加開城談判。1962年任黑龍江省軍區政治部秘書處處長。1964年轉業到黑龍江省圖書館任黨支部書記、副館長。文革後在東北烈士紀念館任10年館長。1994年8月因車禍逝世,享年78歲。
父親在1981年口述家族史和參加革命的心路歷程之後,又於80年代末90年代初親自動筆撰寫了一些回憶文章,如他寫抗戰勝利後直到爆發國共內戰前的系列文章《從贛北到錦州》,又撰寫了在東北錦州秘密工作的文章,曾在《雲南黨史資料》等刊物發表。父親去世後,我把原文進行了整理,分篇加了小標題,作為父親回憶的第三部。文中第一人稱“我”仍是父親自稱。願以此係列文章紀念敬愛的父親。
父親回憶第三部 在滇軍中秘密工作
奔赴東北擔重任
1945年8月,日本帝國主義宣佈無條件投降後,我隨第一集團軍副總部留守處從江西上高乘船到達九江。一個月後,總部又進駐安慶(當時的安徽省會),這時我接到雲南方正同志的回信,告知我楊重、張士明、寧堅等同志均已隨60軍、93軍部隊到越南受降,他獨自留在昆明,同意我再次返滇和他面商今後的去向和行動方針。
由於種種原因,我沒能馬上行動,一直到1946年2月初,第一集團軍副總部將開往上海待命之前,我才得以脫身,由安慶取道武漢、重慶輾轉到達昆明。
按照事前的約定,我先到《雲南日報》社找張子齋同志聯絡,張對我說:“方正久等你不至已到重慶去了,我們在途中錯過,他不會再回來了,你也不能和張士明同志他們直接見面了。60軍、93軍都要開往東北打內戰,他們也許已在去東北的海運途中。你今後或者利用同孫渡的關係,仍然回到第一集團軍總部去,或者留在雲南工作,我可以把你的組織關係設法轉到雲南地方黨。”
我當時猶豫不決,對他說:“待我考慮一下吧,我這次返滇,是以回家奔喪的名義請假,未經孫渡批示就自行離隊的,所以得回家去料理老人的喪事,還要了解第一集團軍總部的動向和60軍、93軍到東北後的情況,而且必須在家裡籌措足夠的旅費,才好行動。" 於是,我和張子齋約定,等我從家鄉返回昆明時,再作決定。
1946年3月,我回到家鄉陸良縣後不久即收到好友孫彬(孫一今)從錦州的來信,這是我們事前約定按照我留給他的幾個地址寫來的。從信中得知第一集團軍總部已由上海吳淞海運東北葫蘆島登陸,進駐錦州市。原屬孫渡總部建制的第58軍被留在江西,已脫離隸屬關係,新三軍在江西受降後即被整編,都沒有來東北,單把孫渡總部調到東北,名義上是指揮由越南海運來東北的滇軍,也即將在葫蘆島登陸。
這封信帶來的訊息,使我及早下定去東北的決心。想起當年龍雲藉機要求把60軍調回雲南,就是不放心他的主力部隊長期被遠隔在外邊,盧漢一手經營起來的93軍,也是出於他自己的需要。誰知道蔣介石把龍雲整下臺,換上盧漢掌權之後,卻把龍、盧視之為籌碼的這兩個軍,一下子從中國的西南角調到遙遠的東北,還美其名曰仍舊歸滇軍將領孫渡指揮。
但這變動對我卻提供了一個和黨組織靠近一起工作的機會,我回到孫渡總部,過去和黨支部相距4000多里的特殊情況就可以結束了。既然決定,在給孫一今覆信的同時,我立即寫信給孫渡,表明我擬返回總部工作,請示他是否可行;旋即接到孫渡的來信,要我返回總部。我據此向家鄉親友宣佈我要到東北去,重返孫渡總部工作,並以長途遠行,需要大筆旅費為由,變賣家產,理直氣壯地排除了家族中長輩們對我變賣“祖業”的干擾。
1946年夏,當我從家鄉陸良抵達昆明時,恰逢國民黨特務以搜捕殺害李公樸、聞一多的兇手為藉口,製造白色恐怖。張子齋同志已轉入地下,到外縣山區搞武裝鬥爭,找不到他了。我即四處設法買直飛上海的機票,一直等到8月間,才從昆明飛抵上海市,正好碰上駐寶山縣的孫渡總部留守處人員,包括許多軍官家屬,即將搭乘一艘美軍登陸艇到天津。這些人員在上海已呆了半年多,現在認為東北局勢已為國民黨所控制,非常之安全了,都忙著儘快到錦州去。
我在上海只停留了3個夜晚,就同大家航行到天津登陸,改乘火車駛往錦州。當時車很慢,夜間還不敢開車。第一天只能在山海關過夜。黃昏時分,我和幾個同行者登上萬里長城,這裡是河北與遼西的分界線。遙望北方,不禁心潮起伏,痛感內戰的烽火就在不遠的地方燃燒,那就是我要投身之處。我的工作和生活都將翻開新的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