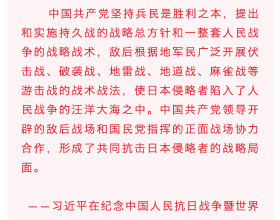1
我們接手的第一個案子,有些奇葩。
老何說,一個禮拜前,有人在他的偵探事務所網站留言板留了言。
因為事務所新開,百廢待興,所以很多事情一個人忙得有些焦頭爛額,當時並沒有關注到這條留言,等到一個禮拜之後,他上網瀏覽的時候,才看到了這條留言。
只有四個字——
老何用他那雙充滿審視目光的眼睛看著我,問我怎麼看。
“沒有了?比如姓甚名誰,家住哪裡,什麼事情等等……”
老何緩緩搖頭:“除了終端顯示是用手機上網留言的……正是因為什麼都沒有,所以我才會越想越不對。”
我嘆口氣:“這應該是惡作劇,可能是某個無聊的人拿著手機上網,看到你的事務所廣告連結點進來,然後隨便打了這四個字——最重要的是,不是正式的委託,沒有委託費,難道要義務為了這件莫須有的事情費神費力?老何,咱們是私家偵探,又不是慈善機構!”
我語重心長地說著,以為能讓老何放棄這個無厘頭的案子,可是老何看我的眼神依舊銳利。
我只好舉雙手投降:“得!我知道了,你丫一開始就不是想徵求我的意見,你已經打定主意要查這件事了,是吧?”
何林眼中的凌厲光芒淡去,他把細邊眼鏡摘下來,用眼鏡布擦了擦又重新戴上,點點頭:“蟲子,你的思維比較活,就這四個字你能想到什麼?”
我想了想:“如果確有其事,那麼首先從字面上看,留言的應該是個孩子,只有孩子才會下意識地喊大人叫叔叔或者阿姨,換了我倆這歲數的,叫聲大哥頂天了不是?”
老何點點頭,“繼續。”
“再者,對方是用遊客身份進入網站,沒有註冊,是不能註冊,還是不會註冊,或者是沒有時間註冊?留言只有四個字:“叔叔救我”,簡明扼要,顯然在心中盤繞了很久,但我有個疑問,既然都能用手機上網了,幹嘛不打110報警來的迅速?”
“我想過這個問題,有兩種可能,一是手機沒有SIM卡,但有WIFI,所以沒法撥出去,二是對方不敢出聲,只能透過按鍵打字來傳遞自己的資訊。”
說到這裡,老何看了我一眼,我下意識地嚥了口口水。如果真如老何猜測,那麼這件事就不是一般的惡作劇了,也許在某個黑暗的角落,一個孩子正在生與死的邊緣掙扎。
“問題來了……”
我攤開雙手:“即便我們在這裡推理的不錯,可是僅憑這四個字,怎麼找?咱又不是神!”
“我已經拜託了槍神,透過這個留言帖反查對方的IP,應該很快就能給我訊息了。”
槍神就是老何以前讀警校的死黨,現在在公安系統內部工作,上次尋找許晴也是他幫了忙,據說槍法超神,所以得此外號。
這年頭,有人好辦事,果然一個多小時後,槍神來了訊息。
這位神不但查出來那位遊客的手機號、連同它的主人姓甚名誰,家庭住址也給順帶揪出來了。
當我看到老何QQ上的這些資訊時,就差跪拜了。
“這也行?連註冊都沒有註冊,隨便留了四個字都能被扒出來?!”我問。
“當然,任何上網的裝置,無論是電腦還是手機,都需要有公網IP,不然無法連線網路。雖然每次手機上網分配的是動態IP,但是運營商那裡會有記錄,一般人當然沒法查到,但若是公安系統介入就另當別論了。”
我聽著老何這麼一解釋,瞬間感覺Get新技能了,想著以後上網說話得小心點。
手機號的主人叫孫國奎,四十二歲,待業,老婆早年跟人私奔了,至今杳無音訊,有一個兒子,在十年前得了不治之症身亡,可以說是光棍一條,命運有些悽慘。
我們沒有過多浪費時間,按照資料上的地址直接趕了過去。
2
孫國奎的家在句容市,就在南京周邊,老何開著那輛淘來的二手現代載著我一個多小時就到了。
我們跟著地址導航,在華陽西路停下來,這裡有很多廠房,大多比較老舊,類似機電、建築材料公司很多,民房則隱藏在這些公司後面,有些是隸屬於某公司的職工宿舍。
孫國奎家所在的華陽新村是一個老小區,建造於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我們找到的時候,裡面已經一片狼藉。
時值初夏,小區裡垃圾成山,空氣裡的酸臭味道讓人不得不捂住鼻子。
乍看一下,這裡七八成住戶已經人去樓空,有的樓房牆壁都已經被挖掘機鑿穿,大大的“拆”字到處都是。
這裡原是上世紀的老小區,而今因城市改造被拆得面目全非
很明顯,這裡已經是被規劃拆遷的區域,但仍然有一些住戶還在堅挺,沒有搬走。
“這就是傳說中的釘子戶啊!”
我忍不住感嘆一聲,“這年頭為了多掙點錢真不容易!”
老何白了我一眼,“看不出來啊蟲子,你還挺憂民的。”
我嘿嘿一笑,跟著老何走進了一棟看起來隨時可能倒塌的居民樓裡。
孫國奎的家在五樓,這種老式小區最高也就五層,等我們喘著氣上了五樓,按照門牌號找到的時候,房門大開。
室內的佈局一覽無遺,除了一些沒用的臉盆罐罐之外,竟然全部搬空了。
原來孫國奎在一個禮拜前已經和拆遷辦的人談好,搬了出去。這是我們打電話,透過這片區域的拆遷辦公室瞭解才知道的。
說原來孫國奎是個讓人頭疼的釘子戶,堅持了大半年了,咬住100萬賠償款不鬆口,少一分都不行,態度也極其惡劣。
可是一個禮拜前竟然主動來談,也在賠償款方面做出了很大讓步,這讓他們又驚又喜。
“會不會太巧了?一個禮拜前,他的手機在事務所網站留了言,之後就忽然來了個一百八十度大轉彎,這裡面肯定有貓膩!搞不好這傢伙拐騙了什麼兒童,發現那孩子趁自己不注意用手機上網求救,害怕事情敗露,所以降低要求提前從這裡搬走!”
我忍不住把心中所想說了出來。
“推理得不錯,就是太過主觀了,但是有一點我倒是很贊同,他在賠償款上的態度前後反差之大,而且急於搬走,這裡面的確有文章……”
何林沉默了一下,手指輕敲手背,這是他在思考時候的一個習慣動作,然後他對我說:“打電話給孫國奎,用拆遷辦的名義,就說合同簽訂還有個小問題,希望他過來一趟。”
我連忙點頭撥通了孫國奎的手機,然而電話卻已經變成了空號。
事情的發展正在脫離我們的掌控,我看著老何:“這傢伙不是畏罪潛逃了吧?”
老何微微皺眉:“看起來對方可能察覺了手機上網留言的事情,害怕引來不必要的麻煩,所以銷號了。我們走一趟拆遷辦,打聽一下孫國奎搬去了哪裡,有沒有什麼新的聯絡方式。”
我點點頭,轉身跟在老何後面準備下樓的時候,看到對面那棟樓的陽臺,有個男人正在鬼鬼祟祟地站在半開的玻璃門裡看著這裡,見我望過去,立刻又把半個身體縮了進去。
“怎麼了?”
老何問我,我皺了皺眉,搖搖頭。
3
我們假扮孫國奎的債主找到了拆遷辦,之所以假扮債主,何林說,這年頭人們最先急著撇清關係的,一個是死人,一個就是債主。
為了避免麻煩,儘快讓我們離開,他們也不會花時間來稽核我們的身份真假,只會把他們知道的儘快告訴我們。
這個方法果然很奏效,拆遷辦的人知道我們是放貸的後,一臉嫌棄,同時又有些緊張,很快就說了我們想知道的事情。
孫國奎在合同簽訂上的號碼,依舊是那個已經空號的手機號,至於搬去哪裡,這個孫國奎沒有說,他們也不需要問,反正發錢和拿房子的時候會通知的。
“可是他手機號空號了,你們到時候怎麼通知?”
我好奇地問。
“這麼大筆賠償款和一套房子,傻子才會放棄,多半對方隔一段時間會重新弄個號碼,然後打電話過來這裡詢問最新進展,這種事情我們以前也遇過。”
我們見在這裡沒法得到有用的資訊,只好離開。
上車系好安全帶,老何一臉凝重,我知道,現在我們失去了孫國奎的動向,意味著這個案子可能沒法繼續跟進了。
“老何,我覺得我們還是得去一趟華陽新村,資料顯示他在那住了很多年,沒準有些熟人什麼的,會知道他搬去了哪裡。”
我把之前看到對面那個鬼鬼祟祟的人的事情說了一下,“現在最重要的,是要弄清楚一個禮拜前,到底什麼人用他的手機留了那四個字,知情的,也許不一定只有孫國奎。”
老何點點頭,說也只能如此了。
我們再次來到華陽新村是第二天的上午,天色陰鬱,風有些大,把小區裡無人收拾的垃圾袋颳得到處都是。也讓這座接近廢棄的老小區顯得有些陰森。
成堆的垃圾映襯著小區的荒廢與破敗
由於孫國奎那棟樓的住戶基本上都搬空了,我們直接去了那天一直在鬼鬼祟祟看我們的對面那棟樓的住戶。直覺告訴我,可能會知道些什麼。
開門的是一個四十多歲的男人,頭髮很亂,臉色蠟黃,身上穿了一件皺巴巴的襯衣和一條牛仔褲。
明明是上午,卻有一身濃烈的酒味,看到我們後,他一臉的警戒,然後用句容方言問我們是誰。
句容話和南京方言其實有些異曲同工,所以並不難懂,我剛想自告奮勇說自己是孫國奎的債主,就被老何在後面用腳踹了一下。
“打擾了,我們是華陽街道拆遷辦公室的,我們來呢,主要是來了解一下你們這些不肯搬走的住戶,是不是確實有什麼困難,我們會如實和上面反映,爭取給你們謀取最大的福利,讓雙方最後都能滿意……”
老何本來就長得白淨,戴著一副細邊眼鏡,很有一種書生的感覺,所以那人開始就信了七八分,臉上的戒備也鬆懈了不少,擠出一個笑容,說讓我們進去坐。
我白了一眼老何的背影,心想你換角色也不提前說一下!
老何說會對訪談住戶的實際情況做個筆錄,只是個形式,不用多想,然後套出了對方的姓名、年齡等等,我不得不佩服這種滴水不漏的招數。
男人叫吳正,祖籍安徽,後來和現在的老婆好上了,就入贅了進來。
“那你現在做什麼工作呢?”
老何一邊問,一邊煞有介事地握著筆在記錄。
“我沒啥本事,年輕時為了活下去賣了一個腎,所以身體不太好,一些重體力的活也幹不了,就一直打些零工。正好現在這裡不是拆遷了嗎,我就乾脆呆在家裡,等著熬到最後,能多得一些拆遷補償款……那個拆遷辦的同志啊,你們可得幫我多說些好話,你看我這身體,下半輩子還得靠這個活著呢。”
說到這裡,吳正臉上又擠出一絲笑意。
“好的,那麼你老婆做什麼工作,家裡有孩子麼,幾歲了?”
我看到,吳正在聽到孩子幾歲了的時候,放在桌上的手明顯動了一下,這是下意識的反應。老何也看到了,但是他不動聲色。
吳正說自己老婆在一家工廠做採購,長期出差,孩子則因為老婆的原因一直沒懷上。
我心中不由鬆了一下,原來如此,怪不得聽到孩子的時候會有些過激反應。
“好,你的情況我們基本也都清楚了,還有個題外話,對面那棟樓有個叫孫國奎的,你認識麼?”
“認識,大奎麼,這裡拆遷之後,人很少了,他經常來我這串門,怎麼了?”
老何擺擺手,“沒事,我們就是好奇,孫國奎之前一直咬著100萬的拆遷補償款不鬆口,忽然間40萬就同意搬走了,有些在意,要是知道了啥原因,那這裡的釘子戶不是一下子都談妥了麼?”
老何哈哈一笑,吳正也跟著乾笑。
“對了,一個禮拜前,也就是四月二十五號的晚上九點到十點吧,孫國奎家有什麼動靜你知道麼,比如,有沒有什麼孩子?”
聽到這個,吳正的手慢慢從桌上移了下去,兩隻手攢在了一起,他搖搖頭說不知道,說那時候已經睡了。
我們起身正打算離開,忽然從房門緊閉的臥室裡傳來了“嘭”的一個聲音,好像是什麼東西掉在了地上。
我和老何對視一眼,然後看著吳正,吳正的喉頭滾動了幾下,然後擠出一個難看的笑容:“是風吧,今天風大,我臥室窗戶沒關……”
我其實想進去看看的,但被老何阻止,說了些不痛不癢的話,就從吳正家退了出來。
4
“這個吳正很可疑,剛才那一個聲音,明顯臥室裡有人!”
一邊下樓,我一邊對老何說。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隱私,不要妄下判斷。也許吳正在房間裡藏了個情婦呢?咱們管不著。”
“就他?一副半死不活的樣子,還情婦,能舉得起來麼?”
我冷嘲起來。
老何笑了一下,拍了拍我的肩膀,“少扯淡,走,去吃點東西,剛才門口的那個小超市好像生意不錯,我看這個小區裡的人都在那裡買東西,順便打聽打聽。”
“7—111”
當我看到這個山寨超市的名字時,差點沒笑出來,就連門頭的顏色也幾乎和7-11相差無幾,不注意看,還真容易混淆。
超市裡面還蠻大的,一排排的商品琳琅滿目,在朝陽的地方有落地窗,落地窗前還有橫桌和高腳椅,供人買泡麵和速食品的時候可以有地方吃,這一點和7-11倒是很像。
除了附近的居民,一些公司廠房的人也會來這裡買東西,所以生意還不錯,老闆是一個四十多歲的中年婦女,短頭髮,化了妝,看起來很精明的樣子。
我們等到這一波客流高峰過去,才拿了兩盒速食飯走過去結賬,老何是牛肉土豆飯,我則是雞肉飯,只需要微波加熱幾分鐘就能吃了,比泡麵要好點。
“美女老闆,生意挺好的啊!”
交際花這種事照例還是我來做,我違心地恭維起老闆娘來,這個年紀的女人最在乎容顏老去,聽我喊她美女,頓時笑容滿面起來,然後說她姓顧,又說聽我們口音好像不是當地人。
我把老何編的拆遷辦工作人員的身份說了一下,說來這裡和這些釘子戶溝通溝通,老闆娘“哦”了一聲,表示明白了,然後眼神第三次瞟了一下沉默裝酷的何林。
“顧姐,問你個事情,你知道孫國奎麼?”
“知道啊,禿頭那個,以前常來我這買紅星二鍋頭和雞肉飯,上個禮拜搬走了,走的時候還欠我一百多塊錢呢!”
顧姐有點憤慨的樣子,掃完我們手裡的東西,用力敲擊了一下結算器,“一共三十一塊八。”
老何主動掏了錢包,我則好奇地問:“你這不是超市麼,還能賒賬?”
顧姐說,因為是熟客,加上家又在附近,所以孫國奎有時候是直接打電話來超市,讓顧姐送幾包煙過去,或者一紮啤酒什麼的,有時候孫國奎會說下次一起算,這樣就能多見她一面這樣的調情話,顧姐也不好說什麼。
“孫國奎家沒有小孩吧?”
老何忽然問道,拿起牛肉飯示意給加熱一下。
“小孩?沒有,他一直都獨居一個人,這裡的人都知道。”
“嗯,那上個月,也就是四月二十五日那天,你有沒有見過有什麼小孩去過孫國奎家?”
老何問得太職業了,連我這一聽都覺得有些很正式,這人果然是不會聊天啊。
顧姐愣了一下,然後思考片刻,搖搖頭:“沒有吧,那天孫國奎打了個電話,讓我送幾瓶酒加上兩包煙過去,差不多一百多塊錢吧。我稍晚時候過去,敲了半天他家門都沒反應,然後我就給他打電話,結果孫國奎說在老吳家玩,讓我送那去,我當時就有些不高興,但還是跑了過去。”
“老吳,吳正麼?”
老何看了我一眼,我原本很不在意的心態也一下子就被提了起來。
“對對,就是吳正家,他也經常打電話叫我送東西過去,我這裡都是五十起才送,主要這年頭生意也不好做,不好推掉的。”
“那天你送東西過去的時候,是幾點,還記得麼?”
老吳推了推眼鏡架,眼睛裡閃爍著什麼東西,我知道,他一定是嗅到了什麼。
我看到顧姐臉色有些不耐煩了,但很顯然不好對何林發作,大概是覺得何林比較帥吧。
“幾點……我想想啊,應該是九點多的樣子,九點半不到,開門的是吳正,說大奎喝高了起不來,東西我先放下,改天讓他把錢送過去,開門的時候我看了下里面,沒見過什麼孩子。”
顧姐說著,這時候微波爐發出“叮”的聲音,我們的速食飯熱好了,新的客人也已經在後面排隊等著結賬了,我和老何只好先謝過顧姐,然後端著飯去到那邊桌子。
超市專賣的速食加熱飯
“蟲子,我疏忽了很重要的一點。”
老何開啟熱騰騰的包裝時,忽然很嚴肅地對我說道,我本來被雞肉香味勾引起來的食慾一下子消減大半。
“我主觀意識認為,是孫國奎的手機上網留的言,所以理所應當是在孫國奎家裡,但是——”
“但是,手機是可以移動的。”
我接著說道。
老何愣愣的看了我一眼,然後點點頭,“沒錯,那麼那個有可能用他手機發求救留言的孩子,就可以在任意他去過的地方,比如,吳正家。而且時間上,也和留言的時間段吻合。”
“可是,吳正也沒有孩子啊?”
我攤手,老何一下子就卡住了,我們面面相覷,都感覺事情變得很無頭緒。
“那如果吳正說謊了呢?”
我剛吃了一口雞肉飯,立刻就被老何突如其來的一句話差點嗆死,我咳嗽了幾聲,飯也從嘴裡噴了出來。
“他幹嘛要說謊,沒道理嘛!再說了,吳正到底有沒有孩子,這小區附近的人應該都知道吧,稍微打聽一下立刻就會戳破謊言。”
“你說的對,吃完飯,我們再打聽打聽。”
5
吃完飯,又喝了點咖啡,時間是下午的兩點四十分,7-111超市明顯沒什麼人了,多是一些過路的人來買些礦泉水,顧姐無聊的在收銀臺後面用手機刷抖音,一個人咯咯笑個不停。
“顧姐,你這飯味道不錯。”
我走過去再次打招呼,顧姐對我點點頭,眼睛又被手機螢幕牢牢吸引。
“那個,顧姐,問你個事情,吳正他家到底有沒有小孩啊?”
顧姐聽我問這個,臉色明顯很不好看,眼睛盯著螢幕,“你們怎麼老問人家有沒有孩子?”
“不是,這不是拆遷辦需要麼,多一個孩子和少一個孩子這拆遷補償款能一樣麼?對吧?”
我笑嘻嘻地湊過去,拿起一包口香糖給她結賬,可能是看在我買東西的份上,她才稍微緩和了一下:“我不是小區裡面的人,我不是很清楚,反正我沒有看到過吳正家有孩子,但是有一次送東西去他家時,聽到了有女孩子的哭聲。”
“女孩子哭聲?”
我和老何同時喊道,可能聲音有點大,嚇到顧姐了。
“你確定?”
顧姐又搖搖頭,“當時吳正開門,見我有疑惑,就笑著說看電影呢,電影裡面的,但是事後想想,電視機裡傳出來的聲音和真實的哭聲是兩回事,那個哭聲很真實。”
我和老何對視一眼,我想到了今天離開吳正家時,那個忽然“嘭”地一聲的片段。
“那後來呢,你沒有追問麼,或者進去看看?”老何問。
“沒有,人家的事情,我多管閒事幹嘛。”
顧姐很明顯在敷衍我們了,她的眼睛已經看向其他地方,我知道再問下去也問不出來什麼,但是顧姐透露的這個資訊對於我們來說,實在是很重要。
老何中途又拜託了槍神查了一下吳正的底,資料顯示他的確是入贅過來,也的確沒有子嗣的記錄。
“會不會是我們想多了,沒準就是電視機裡的哭聲,有些高品質的環繞音響,聲音很逼真的!而且我覺得,那四個字,肯定是孫國奎這個王八的惡作劇!”
我表達自己此刻的觀點。
“吳正家用的還是老式的大屁股彩電,我看了,是熊貓牌的,這種內建揚聲器的彩電,聲音很渣。”
老式“熊貓牌”彩電, 一代人的回憶。
我明白老何的意思。
“走,這小區還有些住戶,挨個去問,應該會有知情的。”
隨後我們在一下午走訪了這個小區剩餘的一些人家,事情有了突破性的發現。
有一個叫梅芳的單親媽媽,她和吳正的老婆周蓮以前在同一個工廠,周蓮做採購,她則是負責流水線,因為同在一個小區,所以經常一起上下班什麼的,關係不錯。
“吳正對外說是周蓮的原因沒懷上,實際上是他自己的原因,這是周蓮私底下悄悄跟我說的。”
我心中暗罵了一句,真是不要臉啊,自己不行還怪別人。
“不過,大概一年前吧,周蓮從遠方親戚家領回了一個孩子,是個小女孩,有一次在路上買菜的時候,我看到過,說是家裡遭了變故,父母都死了,那邊的太奶奶千般萬般求她收留這孩子,她一心軟就答應了。”
梅芳一邊揉著面,準備晚上包餃子,旁邊是他她的兒子小石頭,正在很乖的配合她。他們不知道,這個訊息對於我們來說無疑是驚天的。
“也就是說,雖然吳正的確是沒孩子,但是一年前,有一個親戚家的小女孩過繼到他們家,對麼?”老何追問道。
梅芳點點頭,有些狐疑,“你們不用這麼緊張吧,那孩子和他們沒什麼血緣,拆遷補償不需要多補償的吧?”
我連忙笑著說是,就是想多瞭解下。
“那,您最近有見過那孩子麼?”
何林推了推鏡架,他眼睛裡的光讓人有些不敢直視,周梅芳似乎察覺到了一些什麼,說話開始猶猶豫豫。
“最近……應該有好長時間沒看到過了,而且周蓮長期出差,我總不能跑到吳正家去問吧?”
她擠出一個笑容,然後雙手快速的將揉好的麵皮和調好的餡料捏合在一起,手把手教小石頭怎麼包餃子,無視我們的存在,我知道對方已經有了些提防。
我和老何對視一眼,說了些會把你們家的情況和上面如實反映的話,然後就退了出去。
然而沒等我們走出幾步,防盜門又開了,一個小腦袋探了出來。
“叔叔,我和你們說件事。”
6
我們站在幾乎沒有遮掩的樓道口,初夏的風讓人感覺微涼,而我的後背正在發涼。
老何抽著煙,菸頭明明滅滅,在黑暗裡閃爍不停,我們都很默契的沒有說話,直到菸蒂已經開始燙手。
小石頭剛才對我們說,經常有小區男人去吳正家聚眾看黃色影片。
我問你怎麼知道他們是去看黃色影片,他說聽他媽媽講的,她媽媽平常會念叨人家的事情,說那些壞人一個個不要臉,喪盡天良。
老何問:“這是你媽媽的原話?”
小石頭點點頭,說叔叔你們看起來像警察,去把壞人抓起來吧。
這是我和老何一直沉默到現在的原因。
什麼叫喪盡天良?總之,聚眾看黃色錄影,絕對不至於,簡單的四個字,好像包藏了很多很多東西,一些讓我們有些難以接受的。
“留言的,很有可能就是那個過繼到吳正家的小女孩,在四月二十五日晚上九點四十七分左右,用孫國奎的手機上網求救。至於為什麼,我想你應該也能猜到一些了吧?”
老何問我,眼睛像是一把刀,似要撕裂黑暗。
“要不要報警?”
我把菸頭狠狠的丟在地上,踩滅,老何還沒說話,但是手機忽然響了起來。
他前後一共只說了一個字,“好”,然後就掛了電話。
“吳正請我們去一趟,說有些重要的事情忘記告訴我們了。”
說完,老何看著我,我深吸口氣:“去!鴻門宴也得去!媽的就不信了,邪不壓正!”
儘管如此,在路上的時候,我還是順手抄起來一個小石塊,握在手裡,以防萬一。
吳正家的門提前半開著,從裡面流淌出冷色的光影,我們在虛掩的門口往裡面看了一眼,吳正正在客廳飯桌上坐著,一個人在喝酒吃菜。
我和老何前後腳走了進去。
“兩位辛苦了,這麼晚還在加班,我這一桌酒菜聊表敬意!”
吳正笑的眯縫起眼睛來,請我們坐下,然後主動拿過一瓶夢之藍給我們滿上。
“請!”
說著,他依舊笑容滿面的看著我們,在等我們喝。我猜這酒裡會不會有毒,或者迷藥。
於是我看了老何一眼,想問他是喝還是不喝,結果老何看都不看我,第一個仰頭喝了下去。
隨後吳正望向我,我心一橫,也仰頭喝掉,烈酒灼心,我直接就問:“吳正,你想說什麼?”
“兩位偵探同志,角色扮演的累不累?”
吳正眯縫起眼睛,臉上笑意森然。
“你知道我們不是拆遷辦的?”
我驚撥出來,一隻手已經伸到褲子口袋裡,握住那枚小石塊,只等一個情況不對,先把這老小子敲暈了再說。
吳正說,老何早上問他四月二十五日晚上九點到十點,有沒有孩子去過大奎家時候,他就已經知道我們不是拆遷辦的了,隨後他就透過老何留下的手機號查了一下,和事務所網站上的號碼一致。
“所以,那個在事務所網站報警求救的孩子,在你家裡對不對?你老婆長期在外出差,你飢渴難耐,就強姦了那個過繼來你們家的小女孩,還不止一次!這樣也就算了,你還召集孫國奎等人來你家裡,強迫小女孩和他們發生關係,然後你從中牟利對不對?!”
我把心中所推斷的大聲喊了出來。
吳正的臉皮抽搐了一下,他沒想到我們已經知道了這麼多,眼神裡的殺意非常明顯,就在這時,老何忽然“咚”的一聲趴在了桌上,昏了過去。
我一驚,想著那杯酒裡果然下了藥,我剛起身去看老何的時候,就感覺腦袋一陣暈眩,立刻就跌了下去。
我感覺一瞬間天旋地轉,握在手裡的石頭沒有機會拍出去了,心裡一陣淒涼,出師未捷身先死。
我的視線開始模糊,模糊中看到吳正喊了一聲什麼,然後房門開了,一個禿頭的中年人手裡拿著刀走了出來。
他蹲下來,揪住我的頭髮,眼神兇惡,鋒利的刀鋒對著我,然後就朝著我刺來!
說實話,那一刻我嚇尿了,我甚至後悔要答應老何做他的助理。
但就在這時,身後有人忽然暴起,一腳踢飛了禿頭手裡的刀,除了老何還能有誰?
吳正大概也愣了,反應過來抄起酒瓶就要砸向老何,老何迅速捏住他的手腕,用力一扭,吳正整個人就像是小雞一樣被提了起來。
之後的事情,我想不用我再描述了,過程有些無聊,老何一個人吊打。
不愧是前警校精英,我在心裡感嘆道。
“蟲子?要不要緊?”
我掙扎著在老何的幫助下從地上爬起來,一隻胳膊搭在他的肩膀上,我使勁搖搖頭,想要驅趕那種從大腦意識裡傳來的倦意,然後跟著老何一起走進了臥室。
臥室不大,約莫二十個平方,一張大床,兩個床頭櫃,一臺電視,還有一個衣櫃。
直覺告訴我,如果藏人,衣櫃是不二選擇,我們同時走過去,拉開門。
當我們發現小女孩時,她已經被折磨得不成人形
衣櫃裡,一個被封住嘴巴的小女孩正瞪著一雙驚恐的大眼睛看著我們,赤裸的身體蜷縮成一團在顫抖著,雙手和雙腳被鎖住,還沒完全發育的身體上,有很多被虐待的傷痕,有的是菸頭燙的,有的是皮鞭抽的。
看到小女孩的一瞬間,我的眼淚掉了下來,然後眼前一黑,不省人事。
7
大約一年前,名叫森森的10歲小女孩被周蓮領了回來,她原以為會是新的開始,卻沒想到是一場噩夢。
一開始吳正很不高興,說替人養孩子做什麼,但周蓮堅持要養,兩人為此吵了幾次。
周蓮的工作註定了要長期在外出差,一個人慾火難耐的吳正,在半年前的一個夜晚,趁森森洗澡的時候強姦了她,為了怕她說出去,從那天開始便將她軟禁在家裡,學校那邊則以森森回老家生活為藉口退掉了。
在這之後長達半年的時間裡,吳正先後數十次強姦了森森,不但如此,還招來孫國奎等人,以每次100塊的價格迫其與別人發生關係。
有一次周蓮出差回來,看到森森被人強姦的一幕,她驚呼著試圖阻止,但在吳正的拉扯下最終沒能成行,原本打算離婚,但為了拆遷補償款,她選擇沉默。
4月25日晚,孫國奎再次去到吳正家,在臥室裡把森森強姦了。
事後他趴在床上睡覺,手機在旁邊,森森用他的手機上網求救,無意中看到網頁跳出了何林偵探事務所的廣告連結,然後點進去留了言。
之所以不敢打電話報警,是因為距離孫國奎太近了,出聲怕被知道,但還是被忽然進來的吳正看到了,奪了她的手機,毒打了一頓。
第二天,心思縝密的吳正害怕事情暴露,逼迫孫國奎去拆遷辦談條件,立刻搬走,孫國奎也害怕事情敗露,降低了要求,把手機銷號,並搬離小區。
第三天,我們第一次去吳正家的時候,因為聽到了我們的聲音,被封住嘴巴捆住雙手的森森踢翻了一個菸灰缸,試圖引起我們的注意,但沒成功,事後被吳正用菸頭燙。
還有很多她被性侵、被虐待的細節,我不忍再說。
“那孫國奎怎麼忽然在吳正家臥室裡出現?”
我問老何,事後才知道,那個禿頭大漢就是孫國奎。
“因為是吳正讓他過去的。我之所以裝暈,讓他們放鬆警惕,那杯酒我其實並沒喝下去。”
我苦笑,“所以就我傻逼,差點被人給宰了……好歹你事先和我說一下你的計劃啊!”
“我也是進去的時候發現地上有腳印,和吳正腳上的鞋子不對,想著臥室裡可能還有人,所以臨時裝暈,抱歉抱歉,待會兒買點營養品給你補補。”
老何說著,臉色迅速陰沉下來,煙一根接著一根抽。
我開著車,正在返回南京的途中,來時晴天回時雨。
“老何,你在想什麼?”
老何搖搖頭,把菸頭扔掉,深吸口氣,“吳正和孫國奎之流固然應該受到法律的審判,被制裁,但是還有一些人,他們更可惡,更應該被審判。”
“你是說周蓮?”
我看著他,問道。
“還有超市的顧姐、知情的梅芳,以及一些我們不知道但是心裡有數的人,他們明明可以說的,明明只要一個人報警,一個人說出來,森森就不會被性侵虐待這麼長時間!這些人或者為了自己的利益,或者不願意惹禍上身,選擇保持沉默,這才是讓我最痛心的地方……你知道我為什麼不怎麼喜歡上網上微博麼?”
我搖搖頭。
“因為每次一上網,看到的都是那些站在道德制高點的鍵盤俠,一個比一個慷慨激昂,正義感十足,好像自己當時若在,一定會怎麼怎麼滴,可是現實呢?也就是另一個梅芳、另一個顧姐,另一個選擇沉默的某某某。”
雨打在車窗玻璃上,外面的一切都那麼模糊
雨,越來越大了,砸在車窗上,遠方的天空,烏雲壓得低低的,我的心也沉了下去。
“小石頭也很了不起啊,並不是所有人都是這樣的,老何,我總覺得你挺悲觀的。是,人性確實是有陰暗面,但正如白天和黑夜。這個案子給我最大的感受是,我覺得我跟你幹,是對的,至少咱倆不選擇沉默。這是我們唯一能掌控的。”
我試圖緩和老何的情緒。
“換個字,幹聽起來不好。”
老何面無表情的說道,我看到他的嘴角微微扯起一個弧度。很淺。
那天后來,雨停了,車開到南京郊外的時候,看到了久違的彩虹。
雨過,總會天晴。
(文/蟲子,本文系“人間故事鋪”獨家首發,享有獨家版權授權,任何第三方不得擅自轉載,違者將依法追究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