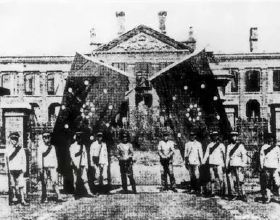昨天更文的時候,被老公嘲笑,他說,某些人啊,總以為自己文采不錯,其實根本沒幾個人看。
他總是這樣,說某些人啊,怎麼怎麼樣,我們也似乎習慣了用這種玩笑口吻,嘲笑對方或自嘲。
可總有那麼些時候,或者是心底有那麼一點地方,是不能觸碰的,那一瞬間的那句話,就像一把無情的大手,撕扯開你以為已經癒合多年的舊傷。
【一】
我出生在普通的農村家庭,若非要在這種普通中找出點與眾不同的話,那就是,我們家沒有男孩兒,我沒有哥哥或弟弟。
我爸說,不是沒有,是確實不該有兒子的命。他總是標榜無神論,卻又時常把“命”掛在嘴邊。他這麼說,是因為,生過兩個兒子,都夭折了。
於是最終,家裡還是三個女兒——我和兩個姐姐。
記憶中,父母說的最多的一句話便是,我們家沒有男孩,所以你們要好好上學,才能讓別人看得起。
兩個姐姐和我,這種督促和教導中,一直學習刻苦,成績優秀。我們不買零食,不鬧新衣服,直到青春期,讀了初中以後。
我入初中之前,在班裡和一個男生平分秋色,要不是他第一我第二,要不是我第一他第二。然而升初中“放榜”的時候,卻沒有我的名字!雖然那時說是“義務教育”,但成績不好的是要“蹲級”的。
雖然後來找人弄清了事實,是把我的名字漏掉了。但後來在我的腦中,這算是我人生中,一個記憶深刻的“跟頭”。
十幾歲的年紀,“自我”開始在心底復甦,我們雖然不知道將來幹什麼,但也開始規劃,讀一個好的大學,名牌的大學,成為一些人眼中的佼佼者。
具體到我自己身上也是,考上一個好的大學,才能被人“看得起”。
那時坐在前三排中間的,都是當時老師眼中升學有望的優等生,我和f和j還有幾個男生坐在這個位置,經常相互打氣鼓勵對方。我們的筆都放在一處,少了會有人自覺補充上去,f說,我們提前進入了共產主義。
那時我們知道的大學不多,清華北大似乎更是種象徵,象徵了一種“好大學”,而不是一個具體的大學。那時我們擊掌約定,都要考“清華北大”。
一個班裡,後幾排也有自己的天地,我卻無從知曉。只記得,放學晚自習路上,幾個少年躲在馬路的一邊,星星點點,忽明忽暗。看到有人過來,為首的吹聲口哨,再喊一聲:“哎……”
我害怕又害羞,逃也似地離開。
【二】
讀初中那幾年剛有了“減負”這個概念,很快,全國各地,都像雨後春筍般的,陸續提倡“減負”。我們以為看到了希望,可以不用再拼命往腦子裡塞東西,好像再多一點點腦子就會被撐開,炸裂。
事實“減負”肯定是不可能的。本就只是所鄉村學校,再優秀的孩子,拿到縣裡,市裡去比也是資質平平,不學,談何升學?
於是,有些人學到接近崩潰,也有些人用自己的方式宣洩,打架,群毆,層出不絕。直到中考前,班裡一個男生,打群架時失手捅死了另一個班的男生。
出人命的事,在當時還是很轟動的。可再轟動,也擋不了時間前進的步伐,時間邊走,邊掩埋,遺忘著過去的一切。
寫作的夢想,也是在那時被一名語文老師點燃,繼而又在那特殊的條件和環境下,被澆滅。
中考的失利,更加劇了我對生活的失望。一個在自己小小世界被捧大的孩子,好像徹底跌落神壇,自己表面那點驕傲被現實擊得粉碎,喚起的,是久埋於心的自卑。那時候,我說我不想學了,不想考大學了。而事實,自己也許只是怕被進一步證明,自己確實是一名失敗者。
那時沒有“抑鬱”這一說法,不過記憶中,我應該是“抑鬱”的。去復讀的前夕,我把自己關在一間小屋,將近一天,不吃不喝,不說話,
幾次把小刀放在自己手腕,卻又心有不甘,又屢次放下,而每次放下,都讓我淚如雨下,依然找不到更好的選擇。
最後走出小屋,我說難受,奶奶說,那是餓了——生活的本身,其實永遠逃不了衣食住行——奶奶說我只是餓了,餓了心裡就很難受,她跑到廚房,打了幾個雞蛋,放了蔥花,燉了給我端過來,我和著淚吃下。
第二天,走上了復讀的路。
走時,我聽見奶奶低聲地叨唸,學要真上不下去,就算了……
【二】
後來,和f和j都進了高中,週末見面,相互交流最近看過的書,那時都看韓寒,郭敬明,夢裡花開知多少,還是會相互打氣鼓勵。只是我沒有了f和j的心勁兒。
f還送我本厚厚的日記,我們說好,分享彼此的生活,於是一直,沒間斷過,記錄每天的失意,美好。
理科一直不是我的強項,高中以後,物理一度差到極點。於是和理科成績同樣不好的n結成死黨,從羨慕她逃課的勇氣,到跟著她偶爾逃次課。
期間,奶奶病了,很嚴重,癌症,我再次提出輟學,爸媽沒再說什麼,對外只是說,治病,讀書,讀不起了,不上學也方便照顧老人。
從暑假確診到年底寒假前,好像不到四個月,奶奶去世了。當時姐姐從大學放假回家,爸只是告訴她奶奶病了,臥床,當她急匆匆地趕到裡屋看奶奶時,看到的只是空蕩蕩的一張床。看著崩潰大哭的樣子,我忍不住跟著嚎啕大哭。從不後悔那段時間的輟學,雖然只是短短几個月,我便永遠失去了奶奶。
我說,奶奶是最疼我的人。直到後來結婚,老公的奶奶去世——那是個重男輕女的老太太,儘管相處中有諸多不快,但她去世時,我叫著不再應聲的她,依然傷心不已,我知道,以後可能再也沒有機會,去喊一聲“奶奶”了。
奶奶去世的第二年春天,我爸把我送去了一所偏遠的初中,接著考進了三二連讀的大專。
【三】
畢竟間隔兩年,讀的又是中專起點,周圍同學都比我小,感覺自己好像格格不入。於是我重拾起高中課本,隨後一年又隨高考直接跳到大專。一切似乎重新回到了正軌,然而一切又已不是最初的模樣。
f進入另一所大學而j落了榜。彼時,我們都天各一方。
那些個曾在街頭抽菸,吹口哨的男生,也相繼輟學,外出打工。為首的一個,被父親送去當了兵。
當了兵的男生,後來成了我的老公。
有人說緣分真奇妙,我們轉了一個大大的圈,最後卻又回到了原點。
他後來跟我說,到部隊以後,領導問他們,都為什麼來當兵,別人有的說小時候的理想,就是穿上綠軍裝,也有的說,為了以後能找到更好的出路。而他說,他也不知道,只是稀裡糊塗就被送來了部隊。
他的父親,我的公公,是個強勢的人,記得有次一家人圍坐在一起吃飯,爺倆都喝了兩杯,公公說,以前其實自己也不對,做生意沒時間管你,犯錯了就打。而我老公,一個大男人,居然紅了眼圈。
他說,長那麼大,爸從來沒說過那樣的話,從來沒說過,他不好,他不對……
【四】
畢業時,我們確定了關係,我隨他去北京找工作。偌大的北京,遍地是大學,也遍地大學生,所幸當時還有最初“共產主義”時的同學。
身在軍營的他,本就是幫不了多大忙的,若說有,那便是一種情感上的支援和寄託。但是這種支援和寄託也僅僅維持了兩三個月,他便又去了別的城市。
沒有經驗,沒有背景,就在親戚的介紹下去“跑廣告”。六七月的天,中午的太陽是個名副其實的大火球,照得人眩暈,沒有進展還捨不得吃飯。那天走了好久的路,接近虛脫,我好像又剛剛嚐到生活的苦。
我告訴自己不能倒下,周圍都是行色匆匆的人,倒在這個地方沒有人拉我,只會跌一身塵土和嘲笑。
親戚和朋友開始有意無意提起,我要找個男朋友。甚至我自己,也試想過多次,和另一個人重新開始一種可以相互扶持,齊頭並進的生活。可每每想及此處,心裡必有種無端的疼痛,你說不清道不明,可它確實存在。
我對他說,如果我們就那麼結束,無論以後生活是好是壞,想到你,我的心裡都會有一處空洞。
我到底還是忠於自己內心的,一年後,我們回老家結了婚。
老家的一切,早已物是人非。曾經打群架不慎捅死同學的男生,也已出獄,面對偶爾傳入耳中的風言風語,他也不再辯解。
後來再聯絡高中的死黨n,她已離婚,獨自撫養一歲的兒子。
至今,老公和公公仍偶有爭執,但他的妥協更多了體諒,而非畏懼。
我的父母還是習慣為了省一分一毛的錢,去超市買促銷的菜,也開始喜歡炫耀有女兒沒兒子的“幸福”,也許這是他們心裡永遠邁不過的一道坎。但重要的是我已坦然。
我們終於還是有了各自的生活。我知道,無論f還是j還有n,甚至還有身邊這個人,他們都曾是自己生活的一部分,他們身上,是我看到另一種生活的可能。
誰還不曾是個有夢的熱血少年?!
然而多年之後,我們還是選擇同生活,同父母,同曾經的自己和解。
羅曼.羅蘭說,這世上只有一種英雄主義,那就是,在看清了生活的真相後依然熱愛生活。
我們到底沒能做到理想中那個自己。
但我們每個人心底,都住著那麼一個孩子,他經歷挫折。但依然相信美好。
我們都是自己的英雄。
(文中配圖源於網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