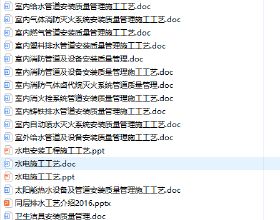第一次去地壇公園,與史鐵生的魂靈邂逅,結結實實地撞了個滿懷,我居然渾然不覺。那是幾年前的大年初五,地壇廟會期間。年節上的廟會,歷來是北京的傳統節慶的保留節目,尤以地壇、廠甸等文化廟會為重。廟會就是趕集,大家像是約好了似地潮湧般扎堆往一個地方湊熱鬧,一浪高過一浪,一波勝過一波。廟會有表演節目的,多為民間傳統節目,有練攤兒的,賣各樣物件、地方小吃,電視裡都見過,沒啥稀罕的,但大家還沒頭蒼蠅一樣往會一塊堆裡擠兌,人挨人,人盯人,小孩騎大人肩上,老人坐輪椅上駆行,姑娘小夥兒手裡拿著冰糖葫蘆,或各色肉串,年節上大傢伙都穿得花紅柳綠,姚黃紫魏,很是扎眼。本來麼,地壇公園是一片鬧中取靜的僻地,鋼筋水泥叢林中一塊自然休憩之地,泱泱大城給人喘息的一葉綠肺,有一片一片的松、杉、柏、檜的家園,間有桃紅梨白的果木,只不在季節,它們均悄無聲息的喑啞者,簇擁著一片一片的梅林,白梅、紅梅、紫梅、黃梅、絳色的梅……笑開了嘴,樂開了花,繽紛燦爛,好不熱鬧!
人人都擠著搶著過去觀梅,挪近了,看的真真的,居然是假梅,園林工人節前一朵一朵捆紮上去的,塑膠的、絹的,以假亂真,看得人目迷五色,以假當真,真沒枉費師傅們一片苦心真意。洩氣是自然的,但內裡還是隱約湧動些些的小感動。為了大家的眼睛,為了節日的觀賞,工人們煞費苦心,一下顛倒了時節啊!還有那滿樹懸掛著的燈籠、中國結,它們紮在一堆兒,擠成一團,晃眼耀目,持久的紅,猶如恆久熾烈的火焰,盯著看久了,你還真會覺得這世上也就紅色喜興、熱鬧、熱情似火,表達著中國人一種喧囂的、雀躍的、歡蹦的、嬉笑的、興奮的、欣怡的、張望的、渴慕的、燃燒著希望的情懷。
廟會不是觀景的,是看人的。除了樹木、古建築、牌坊,其餘都是人。遠遠近近都是人。近走,幾乎貼身,遠觀,烏泱烏泱,到處是攢動的人頭。我怕熱鬧,篤愛安靜,人一多,心就鬧,站不住,更坐不下。隨大流從西門行至東門,出門向南一望,大約一站地,就是雍和宮一片氣宇軒昂、紅牆碧瓦的古建築群。遠眺,延伸著人們的期望,更是人目光伸出的一條遙不可及的手臂,給人以無限的遙思與遐想。因而,對生活充滿期望的人,總要給自己留出一塊仰望星空的時間與空間。
我家距離地壇公園較近,坐124或108路電車,幾站地就到。因而,年節上不去地壇廟會逛逛,似乎就缺了一個節慶專案。可隨家人去了,往人堆裡一站,陡然心煩不已。每回去地壇公園,我幾乎忽略了這是史鐵生過去曾經時常躑躅的地方,他常搖著輪椅在此遙思遐想,仰望星空,叩問人生,更捫心慮己。實在遺憾,身在喧囂的地壇時,我一回也沒想到史鐵生,也沒記起他那篇著名散文《我與地壇》。年節上的地壇與史鐵生的地壇是相悖的。史鐵生說:“在滿園瀰漫沉靜的光芒中,一個人更容易看到時間,並看見自己的身影。”
我初看《我與地壇》是在《上海文學》雜誌,它是此文初發的刊物。初讀時,我被這篇散文驚到了,一篇錐心泣血的文章居然可以這樣不動聲色地娓娓道來。九十年代初,中國散文還桎梏在楊朔、秦牧等教條寫作的八股中,史鐵生的《我與地壇》不說石破天驚,至少讓人耳目一新,如沐春風的。那一年,文學界的重頭年評,有評論家指出,哪怕文學界一年歉收,《我與地壇》也標誌著中國散文的重要收穫。它的出現,是中國散文的一個豐年。的確,史鐵生地壇一文開拓了散文創作生命追問的疆域,尤其是個體生命意義追問的深度。他朝朝暮暮搖著輪椅在地壇公園追問了“十五年”,像一頭老牛將自己吃過的草在胃囊裡一遍遍咀嚼、反芻、研磨,才有了這篇文章,他是用十五年的生命時光作抵押,才換得了自己一生的憬悟與釋然。一個人徹悟的程度,等於他所受痛苦的深度。這篇散文真正承載了人整個生命的重量。
為了躲避喧囂,更為了能私下與史鐵生的魂靈有相晤的機緣,之後,我撇開了年節、假日,獨自一人去地壇。有一回,竟然自己有意走了幾站地,跑去地壇公園。實在遺憾,除了陸陸續續讀過他的書,並多次重讀《我與地壇》,我落在實處,站在地壇公園的靜寂之地,並未能於意念之中與史鐵生邂逅。倒是碰上了幾個寫地書的老人。他倆一個貓著腰寫,一個坐在輪椅上寫,手裡都拿著一種柺杖一樣的、特製的寫地書的筆。兩人都寫榜書,斗大的字,水漉漉的,一個寫顏體,一個寫歐體,一筆不苟。因水筆的溼燥,寫在地磚上面的字,居然也有了飛白。我不知他們在這兒寫了多少年,但按年齡推算,他們定然是與史鐵生相遇過,或許史鐵生於暗處曾經默默欣賞過他們作地書。也就是說,他們曾經與史鐵生的精神文字有過交匯、碰撞,只是他們不知而已。更或許,他們的地書曾給過史鐵生以安慰,亦未可知的。
史鐵生《我與地壇》中寫道:“我在園中讀書,聽見兩個散步的老人說:‘沒想到這園子有這麼大。’”他一定是漏記了,應該是這園子這般大,居然容得下人寫地書!寫地書真好,讓大大的中國字撐滿整個園子!
史鐵生之前一定這麼寫過,可他為什麼又刪去了呢?他寫了一輩子字,寫得太累太累了,不想再寫了。那就歇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