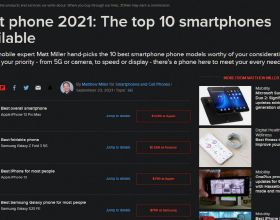來源: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
“侯官王綬琯,1923年生於福州,童年客寓上海,少年時負笈黔蜀間,青年時遊學英倫。始修造船而酷好天文。終以自學致天文為終身業。1953年以還,先後服務於寧、滬、京天文臺。於今歷40載。齒落髮童而意猶未止也。”
讀到這段半文半白的話,你可能覺得它是出自哪位文學家之手。其實,這是我國天文學家王綬琯在1993年寫的自述。彼時,這位大科學家已年至古稀,字裡行間卻頗具童趣,寥寥數語,道出了半世生涯和畢生追求。
從最早閱讀天文科普書籍開始,王綬琯與天文學已經交往了大半生。科學和赤誠的種子,在王綬琯心裡種下後,便長成大樹、開枝散葉。
科普啟蒙下踏入天文之門
王綬琯1923年出生於福建福州。“侯官”是舊縣名,現在的閩侯縣。1936年,在叔父的推薦下,13歲的王綬琯考入福州馬尾海軍學校。王綬琯最初學航海專業,後來因眼睛近視,便改學造船。
求學期間,王綬琯一有時間就跑到書店裡看書。在那裡,他看到了一本叫做《宇宙》的雜誌,這是我國近代的一份天文普及期刊。李珩、張鈺哲等老一輩天文學家在上面發表了大量科普性文章,張鈺哲用通俗的語言,說明什麼是時間、晝夜和四時的變化,還不時介紹中國古代對“宇宙”的描述。這些有趣的故事激發了王綬琯對天文的好奇心,在他心裡悄悄埋下一顆種子。
時光匆匆,造船一學就是9年。1945年,22歲的王綬琯考取公費留學,到英國格林尼治皇家海軍學院進修。
巧合的是,學院隔壁恰好是格林尼治天文臺。這對原本就愛好天文的王綬琯形成了強烈吸引。年少時在心底埋下的興趣的火苗,在這裡被點燃了。
有機會近距離接觸,王綬琯對天文學從業餘愛好,又更走近了一些。他在天文臺結交了很多朋友,還經常給英國的幾位天文學家寫信請教問題。對方看到是年輕人,又虛心求教,也都很歡迎。
後來,屢屢被問及為什麼轉行時,王綬琯說,“人對自然有很大的好奇心。同時你要看了前面的人能夠這樣發現,能夠那樣做一個事情,你也很想自己來試一試什麼的。”
不久,王綬琯給時任倫敦大學天文臺臺長格里高利寫了一封求職信。信順利到了格里高利手裡,1950年,格里高利接受王綬琯進入倫敦大學天文臺工作。
新的學科,在王綬琯面前打開了一道新的大門。當時,王綬琯主要進行晚上8點到早上4點的夜間實測。多年之後,他在《小記倫敦郊外的一個夜晚》一文中回憶往事:“那時我在倫敦大學天文臺,地處倫敦西北郊,四周的田野很平很闊,一條公路從倫敦伸過來,很寬很直……黃昏後,夜色罩下來,朦朦朧朧,路就像是一條筆直的運河,把岸兩旁脈脈的思緒送往天的另一邊……”
漫漫長夜,舉目望著滿天的繁星,王綬琯思緒萬千。他寫下了一首《歸路》:“獨客尋歸路,低天孤一星。步聲碎鳥語,返照媚山青。幽意流成唱,所思其或聆。鬱陶徒四顧,向晚風冷冷。”
梁園雖好,非久居之鄉。
一次次突破奠基射電天文建設
1952年,萬里之遙的祖國已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王綬琯收到時任紫金山天文臺臺長張鈺哲邀請,決定立即回國。
兒時書上的啟蒙者,轉眼間成為眼前的帶路人。王綬琯作為中年骨幹,和張鈺哲、李珩、陳遵媯等老一輩研究員一起工作,投入到了建設中國現代天體物理學的事業中。
50年代初期,“大地測量與繪圖”為國家建設所急需。為適應野外天文大地測量的要求,訊號精確度必須提高。紫金山天文臺受命承擔了提高授時訊號精確度的任務,並派王綬琯到上海主持這一工作。
當時我國唯一的授時機構就是徐家彙觀象臺。這裡儀器有限,技術陳舊。王綬琯以前沒有接觸過授時,但腦海中曾經讀到的關於時間的概念卻一直若隱若現,他夜以繼日,邊學邊幹,“其中之苦,甘之如飴”。
不到兩年時間,王綬琯和同事們改進測時、授時、播時的技術,將授時精度提高到百分之一秒。自此,“北京時間”更響亮了。
此後,王綬琯又承擔起了發展射電天文的任務。在他的提議下,在密雲建起了射電望遠鏡,用於脈衝星觀測。
“在黨的十一大,把實現我國四個現代化寫進黨章……作為一個科學工作者,我感到極大的鼓舞和鞭策,我決心要儘自己的一切力量,來報答黨對我們的期望。”這是1979年2月,王綬琯遞交的《入黨志願書》中的一段話。
王綬琯孜孜以求,一次次從零突破。這一次,他把目標瞄向了天文望遠鏡設計。
天文,是觀測的科學。要觀測就要有望遠鏡,這個望遠鏡越大越好。而在天文光學發展過程中,一直存在大口徑和大視場不可兼得的矛盾。王綬琯和蘇定強等合作解決了天文望遠鏡設計的這一難題。
20世紀80年代後期,王綬琯和蘇定強共同提出了“大天區面積多目標光纖光譜望遠鏡(LAMOST)”的攻關專案。其中關鍵性的“主動反射鏡”及“光纖定位”技術,起到了擴大視場的作用。LAMOST於2009年正式透過國家驗收鑑定,它從原理、設計到研製完全是由中國自主創新。
儘管作為我國射電天文的奠基者之一,王綬琯卻總是很謙虛。他說,“有很多人一起工作的,我只是其中的百分之零點一吧。”
“一個象牙圓頂漢,管中天我相窺\目成意會醉欲痴\星搖河漢近,心躍女牛知\富貴不淫貧不怵,生平居里皈依\浮沉科海勉相隨\人重才品節,學貴安鑽迷。”這是王綬琯作的一首《臨江仙·書懷》。
他是觀星星的人,卻把路鋪在腳下;他求索畢生,卻只說堅持“安”“鑽”“迷”。那浩瀚星河,在王綬琯手中發出了浪漫的對話,跳動著無盡的牽掛。
照亮後學之路
今年11月5日,王綬琯被授予第八屆全國道德模範榮譽稱號,他被表彰為“全國助人為樂模範”。
一位科學家,怎麼會成為助人為樂的模範呢?
王綬琯在回憶過往時曾感慨:“人一生要走很長的路,一路上就常常要有人拉一把。我自己年輕時候的路就走得很艱難,是遇到了幾雙‘大手’才有幸‘走進科學’。如今自己成了‘大手’,也想拉起奮鬥的‘小手’。”
1997年,王綬琯提筆給時任北京市科協青少年部部長周琳寫了一封信,信中的內容看似與自己科研工作並無直接關係,卻關乎後輩未來。他說,作為前輩的自己這一代人,應該反躬自問。在青少年培養科學興趣的關鍵期,“應該有一個組織,給他們領路”。
王綬琯認為,只有植根於一片深厚的土壤之中,科學之樹才能枝繁葉茂。科普,變成一種科學的養成,這是很重要的,這就需要很多人去做,不是靠幾個人就能做得成的。他聯合60多位中科院院士、科技專家,發出了《關於開展首都青少年科技俱樂部活動的倡議》。
在多方支援下,1999年,北京青少年科技俱樂部成立。
20多年來,王綬琯為了俱樂部的發展四處奔波。他堅持“去功利化”和“高度的科學性”的科學教育思想,要求俱樂部不以應賽為目標,要制定縝密嚴謹的人才培養方案。他還寄語青少年:“勤學而好問,務實以求真;敏思而篤志,溫故以創新。”
為了解決俱樂部的經費問題,王綬琯捐出了自己的全部稿費。後來,他年事漸高,身體虛弱,不能行走,還讓女兒推著輪椅帶他參加俱樂部活動。即使躺在病榻上,他仍說:“我總是忘記自己年紀已經這麼大了,時間不多,要乾的事卻還有很多!”
王綬琯認為,科學精神所體現的智慧和力量,屬於社會整體的一個部分,受哺於社會並應該反哺社會。
在王綬琯看來,科學作為社會分工中的一個行業,其任務是認識自然,屬於“求真”。科學精神就是一種求真精神。社會上其他行業雖然任務不同,但都要“求真”。
現代科技在推動社會進步的同時創造巨大社會財富,而作為這一鏈條始端的自然科學卻不以任何實際功利為目的。王綬琯認為,這種反差,往往會對“求真”產生壓力和誘惑。對抗種種干擾,更需要精神力量的支撐,需要淡泊明志、寧靜致遠。在這方面,中華傳統文化有著豐富的養料。從王綬琯的詩作中,我們大概可以窺見一斑。
今年1月28日,王綬琯走完了他98歲的人生歷程。這位給了我們望星空的眼睛的老人,自己化身成天上星辰。他的學生們稱他為“啟明星”。
種子早已長成參天大樹,身後,是一片枝繁葉茂。(鄭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