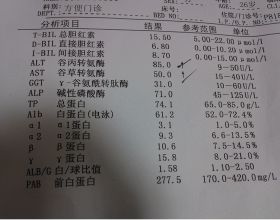1948年10月遼瀋戰役中,廖耀湘部戰敗被俘,1956年1月,被送到功德林監獄改造學習。1961年12月作為特赦戰犯被釋放。但這期間,廖耀湘的生活並非只有改造,他甚至還走上了解放軍軍事學院的講臺。
1951年1月,解放軍軍事學院正式成立,劉伯承任院長。軍事學院成立之初,教員非常缺乏。儘管從華東軍政大學選留了一部分教員,後又從機關和地方大專院校招聘一定數量的知識分子任教員,但仍不能滿足教學的需要。對此,劉伯承元帥大膽從起義投誠和解放過來的原國民黨軍官中,篩選了一部分留做教員,曾指名把廖耀湘請來講課,並非常謙虛地對廖耀湘說,有些問題我們只能當你的學生。(木青《劉伯承請廖耀湘講軍事課》,湘潮雜誌,2010年第5期)
被釋放後,考慮到廖耀湘一個人在大陸,我相關人員還為廖耀湘介紹了一位姓張的女士。廖耀湘為此寫信給自己在美國的兒子廖定一,問廖定一自己能不能再結婚,廖定一讓父親自己定,因為此時廖耀湘已經和在臺灣的妻子黃伯溶十五六年時間不見面了。但與張女士在一起時間不長,廖耀湘便受到文革的衝擊,於隨後的1968年12月2日,因心臟病突發在北京逝世。
廖耀湘1906生,湖南邵陽人。透過他的名字就能多少看到一些他的身世。他的爺爺是一位私塾先生,父親半耕半讀,雖算不上是有錢人,但家境也差不到哪裡去,用我們今天的話說即是當時農村社會的小康人家。耀為廖耀湘字輩名,爺爺和父親為他取這個名字是望其光大門楣、名耀三湘的期望,而他的表字“建楚”也正是名的引申,耀湘必定有建楚之才。廖耀湘6歲時在祖父的指導下,開蒙讀書。6年之後進縣城接受現代教育,1925年從軍,1926年考入黃埔軍校第六期騎兵科。1930年公費留學法國聖西爾軍校。
在留學前有過一個小插曲,是廖耀湘為自己爭取機會的故事,即:1930年他參加了留學考試,成績名列第三,他以為單憑成績自己就可以出國留學了,但結果卻讓他非常失望,他被刷了下來,理由多少有些荒唐,就是他長相一般,個子偏矮。年輕氣盛的他很想不通,決定要去找蔣介石當面說明情況。為此,他夜闖蔣介石公館,被警衛趕了出來,但他決心不見蔣校長,就不回去了。結果是他最終受到了蔣校長的接見。據說,他當時他對蔣校長說上軍校不是相姑娘,和長相關係不大,蔣校長看好他初生牛犢不怕虎的性格,並欽點他公費留學,而他也因此在日後對蔣校長格外忠誠。
農家子弟大約都有一些被清貧培養起來的優秀品質,當年為讓廖耀湘接受新式教育,廖家竭盡財力,甚至在廖耀湘去廣州時連路費也拿不出,而廖耀湘也一直想要透過學習改變自身的命運。正因為如此,廖耀湘的身上保留了一些農家子弟的優點,他不抽菸,不喝酒,不打牌,也不好色,正因為如此,蔣百里後來說他宅心仁厚,廉潔自律,不失君子風範,還說他是當時國軍將領中的“軍人第一人,誠非過譽也”。
留學法國,廖耀湘也迎來了自己的愛情。對方叫黃伯溶,和廖耀湘一樣都求學異國,他們經朋友介紹在法國認識,然後相愛、結婚。他們的兒子廖定一也是在法國出生的,據說有一個小名叫“毛毛”。黃伯溶是大家閨秀,是我國近代民主革命家黃興的侄女,有文化有知識,要長相有長相、要氣質有氣質,還能燒一手好菜。兩人一起在法國生活了幾年後,1936年帶著兒子回國,黃伯溶在軍事委員會新聞處任職,廖耀湘任國民革命軍中央軍校教導總隊騎兵隊少校連長。兩人相親相愛,相敬如賓,即使抗戰爆發後,廖耀湘需要外出作戰,黃伯溶也一直陪伴在廖耀湘的左右。如廖耀湘入印作戰也有黃伯溶的陪伴,扮演著從軍夫人的角色,在飽受異國寒暑風沙之苦的同時,也被稱為“軍中花木蘭”。在這辛苦也幸福的相伴裡,最有意思的是廖耀湘的岳父、黃伯溶的父親黃壽仁,因為對女婿非常滿意,他常以詩歌的形式來表達自己的情緒。比如,廖耀湘他就寫了這麼一首:
巴黎海外初歸國,一出風塵便不同。大地聲正急,九年飛躍五雲中。
最後一句是說廖耀湘九年之間由一個小連長升任為國軍新六軍軍長。再如:1939年11月,廖耀湘隨部參加崑崙關戰役,他又寫道:“崑崙關上早鷹揚,不讓平蠻狄武襄。元夕張燈除夕火,古今戰史並輝煌。”1942年3月,廖耀湘率第22師遠征緬甸,他又說:“其四徵緬軍從絕域過,居然振旅到恆河。一朝回馬真無敵,羽檄交馳捷報多。”言辭間盡是對女婿滿意和自豪,當然也從另一個側面對廖耀湘和黃伯溶婚後的生活進行了補充的說明。
然而,後來的情況就大不相同了:1946年1月,廖耀湘率新6軍於秦皇島登陸,進入東北,被任命為國民黨最精銳的第9兵團司令,下轄5個軍。這期間,黃伯溶大約來到東北和廖耀湘生活過一段時間,後來曾在他們身邊工作過一位護士回憶,黃伯溶因患有貧血需要每天打肝精針。但因“廖司令和廖太太都是歐美留學生,生活方式即使在血與火的戰爭期間,也保持著歐美的生活方式”。還專門送過這位護士一雙在跳舞時才穿的鞋,廖太太“經常會住瀋陽公館,也就經常會看到廖司令”,“廖司令他們很遲起床,大約要到11點左右。我就在大客廳裡看書看雜誌,等他們起床”。再後來隨著戰事的吃緊,便有了二人的分別,黃伯溶回到上海,後又返回湖南,廖耀湘讓下屬帶話給她,叮囑她務必排除萬難帶上兒子廖定一前往臺灣。其後,兩人再也沒有見過面。
黃伯溶到臺灣後,當局因為宣傳的需要,基本不再提廖耀湘的事情,乃至於後來的臺灣民眾都不知道廖耀湘是誰。同時,黃伯溶在物質生活方面也是一落千丈,很不好過,但她深深地明白只有含辛茹苦將兒子拉扯大,才是自己唯一的希望。為此,她把吃苦當作一種修煉,甘願清貧孤寂,也很少與外界交流,一門心思花在了廖定一的身上。廖定一很懂事,以優異的學習成績回報了母親的養育。1959年,他從臺灣大學畢業後,繼續到美國讀書深造,最後獲得了南加州大學的碩士學位,並在加州一家建築公司任職高階土木工程師。
其中也有一個小插曲,即廖定一和妻子是在臺灣大學相識的,那時候,他們都到了談戀愛的年紀,妻子也是臺灣大學的學生。兩人相處過一段時間,到了談婚論嫁的階段,妻子問廖定一身世向父親報告,廖定一這才告訴妻子自己是廖耀湘的兒子。妻子說:“當時,我也不完全知道廖耀湘是誰,但當我把這事告訴父親後,父親表示同意,還說出身於這種家庭的孩子可靠。其後,我就開始關注公公(廖耀湘)的歷史了,才知道他(廖耀湘)是抗日名將,但臺灣卻因為他(廖耀湘)戰敗被俘一直不願意提起他(廖耀湘)”。
廖定一的妻子叫歐陽蘅,她還說,後來,他和丈夫一起定居美國,就想把婆婆(黃伯溶)也接過來,但臺灣當局卻一直不讓走,原因是怕婆婆像杜聿明的曹秀清一樣,先是到達美國,後又透過美國回中國大陸。這件事一直到1972年,廖定一寫信給蔣經國先生,“蔣經國特批才讓她(黃伯溶)出來的”。這時候,廖耀湘去世已經4年時間了,歐陽蘅說,“大陸想讓她(黃伯溶)回去,也做了一些工作,但她怕回大陸勾起痛苦的記憶,就選擇了生活在美國”。
在歐陽蘅的印象裡,黃伯溶“從來不提從前的事情。但是她有非常多的照片,她就一本一本地歸類貼起來,常常看她的照片,是一個不多話的、非常有大家風範的一個女子,字也寫得很漂亮,待人也很親切。”黃伯溶和兒子廖定一、兒媳歐陽蘅一起生活至2008年去世,1905出生的她活了103歲。其後,廖耀湘後人將廖耀湘的骨灰從八寶山革命烈士公墓,移到美國跟黃伯溶葬在一起。這時,距廖耀湘去世已經整整40年,而距兩人最後分別的四十年代末期,已有60多年。
廖定一與歐陽蘅結婚育有一子一女,也都生活在美國,中美混血了。廖志宇,廖家第四代,聽名字像是個男孩,其實是一個漂亮的80後女孩。先後獲得了哥倫比亞大學的工商管理碩士(MBA)和計算機科學碩士學位,是廖家第四代中唯一一位能夠使用中文的人,曾任多家跨國企業中國區總裁。2005年,她和歐陽蘅一起接受大陸一家網站採訪時,曾說過這樣一段耐人尋味的話:
我們把他的骨灰從八寶山革命烈士公墓移到美國來跟太奶奶葬在一起,就算是他們最終又團圓了。因為臺灣方面一點都沒有解凍(指不願提及廖耀湘),完全就是絕口不提,我們反而一直覺得大陸對我們很尊重,從80年代其實就開始認可我們(指廖耀湘)在抗日戰爭的一些功勞,我奶奶(歐陽蘅)覺得很奇怪,大陸還知道太爺爺(廖耀湘),從臺灣那邊,她(歐陽蘅)覺得別人已經不會在乎他(廖耀湘),但每次到大陸,反而覺得很受人尊敬。尤其是我個人,就是很明顯的可以感覺到這種尊敬,因為我在做跨境的投資嘛,就是幫助中國企業走出去,跟各種企業家交流,就40歲以上的人,只要提出來廖耀湘他們都是知道的,而且都還是比較尊敬的,我自己也覺得很欣慰。
對此,歐陽蘅說:“來大陸後,我發現很多人都認識他(廖耀湘)。我覺得大陸對事情的看法更加客觀,認為對是對,錯是錯,不能因為他後來的事情而抹殺他(廖耀湘)以前抗日的貢獻,尤其我看到北京臺《檔案》的一期節目,主持人最後的結論就是我剛才這番話,然後出現了杜聿明、鄭洞國、廖耀湘的照片,我就很感動。”(周昂採訪整理《對話廖耀湘家人》鳳凰歷史,2015年06月04日)
歲月對於人們來說分明都是這樣的,陽光和暗淡往往是大片大片而來,如此就有了黑夜與白晝的反覆和交替,然而這樣卻使人不能完全認識到陽光的可愛、可貴。舉這樣一個例子:當一線或一束陽光穿過黑暗,人們看它時,它一定是屬於發光的金屬的,足以支撐起整個世界,是真正光芒萬丈的感覺。如此,人就有了與陽光融合在一起的心情和經歷——光束或光線某個變得粗或大一些的部位,那一定是遇見者感恩的心或眼淚,同陽光一起發亮,無聲勝有聲,並在最終融合在一起,成為一種安靜的幸福,一點也可以發光的個體,永不消失。廖耀湘的後人看到的正是這樣一種關於陽光的細節,融入了他們的感恩與感動,默默地,在他們的生命裡,不言不語,卻讓他們感受到了一股的強大力量,甚至能成為一條可以讓他們探尋的路,勝過了所有的言語,也把他們的心給照亮了、暖透了。
本文圖片來自網路,感謝原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