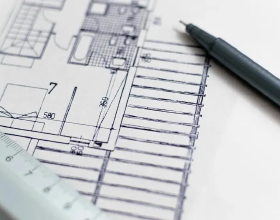來源:人民網-人民日報
那一年,中國作家協會創聯部通知我與幾位作家一起去青海深入生活,主要任務是採訪上世紀50年代末內地“援青”的郵電職工。
將近一個月,我們在地廣人稀的青海,白天行車,晚上訪談。我生長在繁華的江南城市,戈壁的空曠、遼闊、靜謐,令我震驚。
只有在戈壁上,才真正可以見到天似穹廬,才真正可以看到弧形的地平線。公路好像把地球劈成了兩個半圓,在陽光下閃閃發光,永無休止地伸展在我們的視野裡。寂然無聲的茫茫戈壁,除了風蝕和地殼運動之外,似乎沒有任何變化地存在了億萬斯年。寂寞似乎像時間一樣永恆。在這裡,最起碼的願望常常成為一種奢侈——哪怕需要的只是一片剛剛能遮住腦門的綠蔭。強烈的紫外線無情地扎進面部,留下血紅的烙印;戈壁風沙如同鋒利的雕刀在臉上刻下粗糙的皺紋。
這樣說,並不意味著我們的旅途只有蒼涼,也會有意外的驚喜。
那一天,夕陽在風沙裡沉浮。起先還不時地能見到駱駝草和紅柳叢。後來,遠遠近近就只有紅色的沙礫和鐵青的岩石了。茫茫天地間除了我們這輛車,連一絲生氣也聞不到。
忽然,遠遠的地方出現了一幢小屋,孤零零地立在戈壁上,就像是月球上的一個黑點。
這是一個郵電線務站。屋子裡,簡樸而整潔,電話交換臺竟是用石塊壘成的。屋子裡只有一個瘦削的年輕人,黝黑,但眉清目秀。
線務站不在預定的訪問日程裡。但這次偶然的相遇,卻帶來了一場讓我最難忘、心靈最受撼動的訪談。
這位瘦削的年輕人,給我們講起了他與這個線務站之間的故事……
在西寧搭的便車整整走了三天,終於把我留在去往縣城岔路口一片揚起的塵土裡。
我看到父親揹著郵包,迎面向我走過來。
“我代表我們全域性來迎接你。便車搞不好就出岔子,說不準時間,怕你到了見不到我,我昨天半夜就從局裡出發了,在這裡等了你一整天。”
之後,他把我的行李小心地放進一輛手扶拖拉機的拖斗裡。
“快點上車吧,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呢。”
我不知道是不是值得高興。幾天跑下來,我的心情壞透了。我有點想哭。我聽說過,有些像我一樣從郵校畢業分配到基層的人,從西寧出發兩天,就說什麼也不肯再往前走了,轉身搭便車返回。
我與父親在半夜以後到達了縣城。一條不足兩百米的街,兩邊都是輪廓硬朗的房子。有幾星昏黃的亮光從黑暗中透出來。
這個夜晚到達的並不是目的地。我們將要去的那個線務站,離縣城還有一百多公里。
縣境平均海拔四千米,年平均氣溫零下十五攝氏度。嚴寒使人望而卻步。父親之前的幾任局長,沒有一個在這裡幹到任滿。父親卻說,除非組織上另有需要,他會在這裡一直幹到退休。
父親來青海後,最初是鄉郵員。幾十年的時間,他在這裡的山地、草場和戈壁走瘸了兩條腿。但他喜歡這裡,說這裡空氣稀薄,但很清新;人煙稀少,但人很熱情;還有不常見到的野生動物,不怕人,跟人很親近。
兩天後,父親開著手扶拖拉機,把我送到了線務站。
父親出發前夜,曾向當地牧民買了一頭羊。我們到時,帳篷裡一隻大大的牛糞灶,燒得熱氣騰騰。幾個牧民正幫著宰羊,灌血腸,熬雜碎,煮手抓,揪面片。全域性十來個人都坐在地上,卻給我留了個馬紮。
我當然明白父親的苦心。他那張寫滿了期望的臉就像一面鏡子,照出了我的未來。他一口一句“老了”,他的樣子的確比內地七十歲的人還老,可他還不到五十歲。看著他那張臉,我不寒而慄:五十歲以前,我就會這樣老嗎?
這裡的每個線務站之間,相隔差不多上百公里。我常常對著空曠無邊的戈壁發怔。
有時候,我抓緊雙拳——似乎想要攥住什麼——聲嘶力竭地叫喊。聲音不管拖得怎樣長,都很快被戈壁吞沒,沒有回聲。
我同青海不可分離的命運,似乎在我父母結合時就註定了。他們來“援青”後就再沒有回過老家。我在西寧的郵電中專畢業後,按照父親的意願,也回到了縣裡。
到線務站後,除了局裡同事隔些日子給我送一趟糧食、煤和維修零件,大部分日子裡,我見不到一個人,看見的只能是太陽和月亮的換班。今天和明天完全一樣,就像珠串上的兩顆珠子。
在我之前,這個線務站連續九年一直是全省的模範線務站。上一位線務工出席過全國的先進表彰大會,他在這裡一待就是九年。人們在他留下的工作日誌上一再看到這樣的句子:“什麼時候有人來啊……我一定要堅持住……局裡人還有幾天就來了……”
有天早上,我忽然聽見了鳥叫。我疑疑惑惑地從床上爬起來,疑疑惑惑地推開窗子——
真的有一隻鳥,就在窗外不遠的線杆上做巢!
我慌慌張張地撲到門外,興奮得全身發抖。
以後的日子,我每天查完線路就是全神貫注地看著那隻鳥,飛出去,又飛回來,從不知什麼地方銜來了乾草,銜來了土塊。於是荒灘上,有了兩個巢:一個是鳥巢,一個是線務站;有兩個生命:一個是鳥,一個是我。
我們相依為命了。我把拌炒麵的曲拉和最新鮮的烤餅都留給了它。我一聲口哨,它就飛到我的窗子裡來,在屋子裡神氣地走來走去。我出去查線或是查線回來的路上,它會出其不意地從我身後一下子撲到我的肩膀上。
可是,卻從縣局裡來了電話:
“線路上是不是有鳥巢?”電話裡傳來父親沙啞的聲音:“得移掉它。鳥巢裡要是有鐵絲什麼的,可能會給線路造成短路。”
“不!”
我堅決掛掉了電話。
第二天,我卻被鳥淒厲的叫聲驚醒。我爬起床,看到那隻鳥正拼命地撲打著我的窗戶。
窗外站著父親,他已經把鳥巢從線杆上端下來了。
“要不,你會下不了手的。”
他滿臉慚愧地看著我。
父親退休的時候,省局在西寧市為第一代“援青”人蓋了宿舍。但父親不肯去住。一直到去世,他都住在縣裡……
直到他講完了,良久不再吭聲,我們這撥人還是一片靜默,甚至,有淚水滴落的聲音……
《 人民日報 》( 2022年01月08日 08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