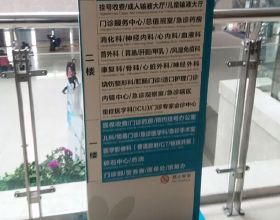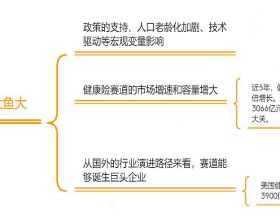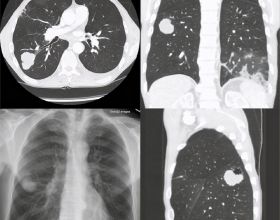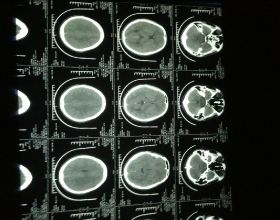在中國人的文化中,有一個“不怨天,不尤人” (《論語·憲問》)的人生信仰。這一人生信仰和信念,原是聖人孔子的一個重要觀點。後來傳承發展為“上不怨天,下不尤人”(《中庸》)以及“自知者不怨人,知命者不怨天”(《荀子·榮辱》)的價值觀念。
這一人生信仰的價值意旨在於:人生之事為,好的結果和效驗非是無故而致,往往是因人之努力而達成。人生的禍福在於自招,事為的善惡無不是自己求之者。為人做事,當求諸己而盡本分,不可怨於天和責備於人。
堅定這一人生信仰,就要求諸己而不責諸外,堅持以修身為本,強化主體意識,發揮主人翁作用,弘揚自強不息精神,在“獨善其身”之基礎上力爭達致“兼善天下”的人生境界。
堅定這一真理信念,就要“下學而上達”,自知而知性,知性而知命、知道;就要弘道以盡己,盡其忠而至於命,致命遂志;就要主忠信,盡心竭力,達致仁至義盡,無憾無悔。
一、知命者,不怨於天
“知命者不怨天”,既為“上不怨天”的價值意旨,又內涵“怨天者無志”的價值意蘊。“不怨天”的價值內涵,是反身而求的求諸己,發揮自身的主體作用和主觀能動性,立志而盡己人生之能為。
(一)下學,自能上達天命之性。
聖人孔子之所以能“不怨天,不尤人”,就在於擁有“下學而上達”的人生修為之樂,自得其樂。“知我者,其天乎!”(《論語·憲問》)在博學於文中,通達天命之性的人生意義和生命價值。
這一“不怨天”的價值意旨,乃是“求仁而得仁,又何怨”(《論語·述而》)思維。藉由“下學”而可上達天命,與天合德,豈可責怨於天?天命之性,可以自我求之,故沒有理由責怨於天。怨天者,必是不肯下“下學而上達”功夫的無志者。
人生或有不得志而窮困之時,但求諸己而上達天命,正道以行,合於人間正義,豈有怨尤?“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論語·顏淵》)我與天命合一,代天行命,內省不疚,故能不怨不憂。
“下學而上達”的人生工夫意旨,又體現為道的“費而隱”(《中庸》)上。“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知行之能為,人人可能,關鍵在於求諸己而付諸努力,而不可責怨於天。
人生之追求,愚可以與知,不肖而可以能行,修為其極雖聖人亦有所不知、不能。人生修為和能為,雖是“造端乎夫婦”,然可極致於“察乎天地”。有“上下察”,就是“下學而上達”。人人皆可“下學而上達”,豈可有“怨天”之情?
在《荀子》的思想中,天雖為自然之天,而非人的性命賦予之天,但其“不怨天”的價值內涵,與孔子的思想具有相合的思維,皆在揭示人生當求諸己而發揮自身主體作用的價值意旨。
(二)知命者,盡己職而不怨於天。
知命者,之所以“不怨天”,就在於明於天人之分,“知其所為,知其所不為”(《荀子·天論》),亦即是履行“能參”的人類職責。天有天的能為自然,人有人的能為本分。“能參”的價值意蘊,是與天地化育有並列之功為。
既然人有其特定的職為、職責,就不要與自然之天爭職,而要盡人事、行本分。“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應之以治則吉,應之以亂則兇。”(《荀子·天論》)天有其時,地有其財,而人有其治。知命者盡其職,就在於求諸己而發揮“能參”的主體功能作用。
不與天爭職,就要行曲治,養曲適,做到生育之而不傷。既然是“彊本而節用,則天不能貧;養備而動時,則天不能病;修道而不貳,則天不能禍”,則人生很多事情不可責怨於天。
對於孔孟之道而言,不怨天而求諸己,就在於篤行“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孟子·離婁上》)的修為。藉由反身以求,修養自身,而達致令人親、使人治和讓人敬的賢能品格和良好形象。人若能為己立命,就可存心養性以事天,豈可浪費心力而怨天尤人。
(三)怨天者,就在於心中無有志。
“怨天”者,之所以“無志”,就在於不能明於天人之分,不敢承擔人職之本分,盡己的人事之當為。人生有志,就在於求諸己而為仁弘道、建功立業,盡人性的主體能為之本分。
有道修為的君子,之所以要立志而有志,就在於“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荀子·天論》)。“不慕其在天者”,不訴諸天運的自然,方能“敬其在己者”。“敬其在己者”,便是求其在我者,做到“志意修,德行厚,知慮明,生於今而志乎古”,盡人事之當然本分。
一個人要擔負自己當盡的本分、職能,就要思人而措天。“大天而思之,孰與物畜而裁之?從天而頌之,孰與制天命而用之?”反之,若是“錯人而思天”,則必失萬物之情,而不能輔助自然。明確人當盡之職責,擔負起人應盡之職能,就在於立志以行本分和盡人事所當為。
與此思維相通,孔孟思想也強調人要求諸己而盡己之修為,立志做好分內之事,“居易以俟命”(《中庸》)。君子之為類似射之行為,失諸正鵠則要反求諸身,看看自己射箭的準星和力道如何。下苦功夫掌握技巧,準而有力,必然能夠射中。
人生的立身處世,為仁由己,弘道在人,豈可責怨於外而推卸自身的責任。立志而志堅,必能自強不息,日進不輟,積德而成善,修業而立功。人若無志,存有僥倖之心,一旦遇到挫折必是怨天尤人。
二、自知者,不尤於人
“自知者不怨人”而“怨人者窮”的價值意旨,就在於揭示“失之己,反之人,豈不迂乎哉”(《荀子·榮辱》)的思想真諦。自知而知人能為之本分,就當求諸己,而不責怨於人。事情之過失的責任,往往就在於自身。一味地責求於人,便是推卸責任,或是不敢勇於擔責,或是不懷好意敷衍塞責。
(一)自知者,不責怨於人。
人生的智慧,莫過於“知者自知”(《荀子·子道》)。自知者,知己性命本分而盡人事之職責,自能確知自己該擔之責任,履行分內的擔當和義務,而不會隨意地責怨於人。
自知己之職分,盡己之能為,盡心竭力而心無旁騖,固能在做人上無憾,在做事上無愧,達致一生無悔。盡了自己該為的本分,承擔了自己該擔的責任,有何心思、雜念去責怨於人。
自知者知勇於擔責,方能令人願意與己共度難關;自知者知不一味責怨於人,方能令人樂意與己和衷共濟;自知者,知愛人、敬人方能令人愛己、敬己,與己同心同德。
在揭示“自知者不怨人”的意旨上,可以用不同修為之知加以詮釋。士者之知,“知者使人知己”(《荀子·子道》),是以知而求立功名於世。使人知己,是求在外之為,必不能皆如人願。士君子的“知者知人”,乃在盡己本分而弘道,實為求諸己的堅定。
與以上不同,明君子的“知者自知”,是求諸己的自覺自證者。自知者,知己性命本分而盡人事之職責,自會藉由知人、愛人和用人以盡己之性。盡己之性,立人達人,必能為人所知。求在己者,不必求諸外,而人必知己。
(二)正己者,不責備於人。
在求諸己和求諸人上,不僅體現著君子與小人的趨舍之別,而且反映著是否有自知之明。“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論語·衛靈公》)求諸己,必有自知之明,知修身為本;求諸人,必然陷入舍本逐末之惑,無以反省自身。
自知者,知做事之本在於做人,明曉做人方是做事的根本。一旦有了修身正己的明智修為,就能發揮人格感染力和道德影響力,達致不令而人自正的管理效驗。“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論語·子路》)正人先要正己,己正則人自正。
自知者,知正人之本在於正己,求人之正不如求諸己而先正己。“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中庸》)正己而非強加於人,不求全責備於人,故能使人無怨。知求諸己而不責怨於人,便是“自知者不怨人”的價值意旨所在。
“自知者不怨人”的價值真諦,就在於求諸己而敬慎其所為:既不為“可非之行”(《文子·符言》),又不隨意憎於“人之非己”;既修行於“足譽之德”,又不刻意求於“人之譽己”。盡其在己之修為,而不必在乎外在的非譽。
自知者,知一切事為和問題的根本在於自身,故能責諸己,從改造和重塑自身的內因入手。既知問題和過咎“有諸己”,就能不非於人;既知修為或素養“無諸己”,就能不責人所立。在製法上言,能自知而求諸己,“先以自為檢式” (《文子·上義》),就能禁勝於身而令必行於人。
(三)怨人者,必導致窮殆。
君子之所以“不怨人”,就緣於“怨人者窮”的不良後果。怨人者,之所以陷入“窮”之境地,就緣於心中無志,不能強大自身而得道多助。一個心無志向之人,必是怨天尤人而不能反躬自省,無以自我完善、自我提升,奮發作為而成功。
人生無志,或是人生職為上的昏昧而不自覺,或是人進步發展上的怠惰和散漫。不能盡人職為而行本分,不能積德成善而神明自得,豈非自窮於人生?徒責怨於人,推諉責任而不能責諸己,就不能自強不息,及早遷善改過,畜道以待時。
在孔孟的思想中,怨天尤人,必然是自暴自棄者。“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為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孟子·離婁上》)責怨於人,則人進善言必不能聽,故為自暴;責怨於人,則不能反求諸己而有為,故為自棄。
“怨人”之窮,乃求全責備於人,或將主觀意志強加於人,必然失道寡助,不得人心。反之,修道則不失於人。“修恭遜、敬愛、辭讓、除怨、無爭以相逆也,則不失於人矣。”(《管子·小稱》)愛人者人愛之,敬人者人敬之,寬宏謙讓者得人心。不爭於人,則人必不爭於己,彼此相安無事。
三、求諸己,盡己之性
“不怨天,不尤人”的人生信仰,實是確立求諸己而自強不息的人生信念和意志。對於人的一生來說,只有不怨天尤人,方能反求諸己,責己而怨己,發揮主觀能動性,盡己之能為,達致仁至義盡而得人心。
(一)責己而怨己,則遠怨寡尤。
在人之常情,遇到苦難和挫折往往是怨天尤人。抱怨上天的不公平,埋怨人生的不公正。執著於怨天尤人,就會放棄反思自省的責任,進而找不回奮進的信心和勇氣。
真正的明智者,乃是直面困難和挫折的反求諸己者:自己努力找到戰勝困難和挫折的辦法和修為,著力打通贏得光明和未來的路徑。人生面對失誤和過失,也是如此,改過不吝而重塑自我。
一個人若能立足求諸己的主體精神,就必能於“多聞闕疑,慎言其餘”(《論語·為政》)中達致“寡尤”,於“多見闕殆,慎行其餘”中達致“寡悔”。“言寡尤,行寡悔”,則福祿內在其中。“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論語·衛靈公》)遠怨之道,就在厚責己而不怨人。
對於人生修為而言,若能誠心於內而不求於外,堅持積德行善而自強不息,必然獲得福報。“盡小者大,積微者箸,德至者色澤洽,行盡者聲問遠”(《荀子·大略》)。有志而盡心竭力,則必盡小而成大,積微而成箸。德至則心廣體胖,行盡則名聲遠揚。
從人生責怨上言,責人不如責己,怨人不若怨己。“怨人不如怨己,勉求諸人,不如求諸己”(《文子·上德》)。責己則敢於承擔,怨己則勇於擔當。求諸己,則一心向善,雖有過而人無怨。不能求諸己而隨波逐流,必然患得患失,無有安寧。
(二)儘性以事天,則功成名遂。
在人生修為上,若能不怨天尤人而反求諸身,就可藉由存心養性以盡人事,依靠窮理盡性以致其志。人生立德、立功和立名的功業、聲譽,無非是求諸己而盡心盡力、拼搏進取的結果。
在《老子》的思想中,求諸己而有所作為,是“修之於身”以至於“修之於天下”的德真而能德溥,實現博大之真的人格理想和“以道蒞天下”的王道境界。
在《孟子》的思想中,求諸己而主動作為,便能盡心知性以知天,存心養性以事天,進而做到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以立命,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不怨天尤人而反求諸身,既可修身養性,又可功成名遂,內聖而外王。或是獨善其身,或是兼善天下。
在《大學》的思想中,求諸己而積極努力,便是藉由格物、致知、誠意和正心的修身功夫,達致齊家、治國和平天下的功業。在《中庸》的思想中,是以至誠之性參贊天地之化育,實現“與天地參”的人生境界。
在《荀子》的思想中,求諸己而明確自身的責任擔當,就能發揮“天有其時,地有其財,人有其治”的“能參”作用。在《管子》的思想中,求諸己而有所作為,就在“法天合德,象地無親”中覆載化育,使天下人莫不各得其所。
不怨天尤人而反求諸身,就能“不求無益之物,不蓄難得之貨,節華麗之飾,退利進之路”(《申鑑·時事》),而讓民俗清正;就可“簡小忌,去淫祀,絕奇怪”,而使妖偽息禁;就會“致精誠,求諸己,正大事”,而以神明應宜;就將“去浮華,舉功實,絕末伎,同本務”,而讓事業發達。
(三)得己而得民,則可王天下。
在治國、為政上,人能不怨天尤人而反求諸身,就能自得而得人,以道治國則得道,以仁為政則無敵於天下。“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孟子·公孫丑下》)自得其道者,則是“得道者多助”。以天下之多助攻親戚所畔之寡助,故能有“有不戰,戰必勝”的無敵。
能成霸王者,必得勝以強,而非得人心、用人力則不能。 “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者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文子·符言》)。以柔弱之道德自得者,方能得人心、用人力。
反本而修諸己,便是不怨天尤人,而有所作為。為政者,只有反求諸己,方能使“戒心形於內”而讓“容貌動於外”,使“道德定於上”而讓百姓化於下,實現王天下的價值目標。
在得民心的反身自修上,“知得諸己,知得諸民,從其理也。知失諸民,退而修諸己,反其本也。”(《管子·君臣下》)求諸己而“從其理”,就在立德行,盡己之誠。求諸己而“反其本”,就在責諸己,改過遷善。
在政治上善於責諸己,便在克己而節制情慾,去奢而務於本事。“夫明王不美宮室,非喜小也;不聽鐘鼓,非惡樂也,為其傷於本事,而妨於教也。”(《管子·禁藏》)責諸己而使邪妄之念“禁藏於胸脅之內”,防患未然,方能避禍於千里之外。
中華文明五千年,歷經滄桑而綿延不絕,已充分證明中華傳統文化的頑強生命力,和迎接各種挑戰的開拓能力。這一文化內涵,既本自“學·思·觀”的探求真理而來,又呈現著“學·思·觀”的理性自覺和開放思維。讓我們齊心協力地一道投入“文化自信”的時代洪流之中,為民族偉大復興貢獻冷靜的思考,清醒的應對,果敢的鬥爭,無愧的付出。堅信“文化自信”,踐行“文化自信”,中華民族一定能夠實現偉大復興。
歡迎評論交流探討。文中圖片來自網路,感謝版權原作者。如有侵權,聯絡刪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