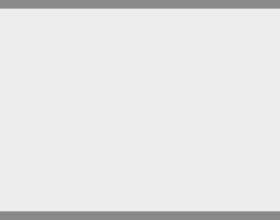外婆同情地抱住他的頭,溫柔地說:“人家拋棄你很正常啊,你醜。你忘不掉人家很正常啊,她美。哭吧哭吧外婆疼你,外婆倒黴。”
老太太回答:“你看到雲沒有?那些都是天空的翅膀啊。”
童年就像童話,這是他們在童話裡第一次相遇。那麼熱的夏天,少年的後背被女孩的悲傷燙出一個洞,一直貫穿到心臟。
他們以為自己是野比康夫,而程霜是上天派來的溫柔靜香。沒想到程霜的角色,原來是胖虎。
劉十三被欺負得最慘,卻想保護兇巴巴的程霜。每當她笑的時候,就讓他想起夏天灌木叢裡的螢火蟲,忽明忽暗,飛不遠,也飛不久,日出前會變成一顆顆露珠,死在人們不會注視的葉子上。因為有一天,他終於知道,程霜和螢火蟲一樣,現在是亮的,但說不定下一秒,就是暗的。
程霜聲音很低很低地說:“所以你不要喜歡我,因為我死了你就會變成寡婦,被人家罵。”劉十三沒有回應,因為背上一陣溼答答。那麼熱的夏天,少年的後背被女孩的悲傷燙出一個洞,一直貫穿到心臟,無數個季節的風穿越這條通道,有一隻螢火蟲在風裡飛舞,忽明忽暗。
再習慣等待,等不來依舊難過。那種難過,書上說叫作失望。直到長大後,他才明白,還有更大的難過,叫作絕望。
劉十三開啟程霜給他的信紙,幾行很短的字。
喂!
我開學了。
要是我能活下去,
就做你女朋友。
夠義氣吧?
這世上大部分抒情,都會被認作無病呻吟。能理解你得了什麼病,基本就是知己。
王鶯鶯的枕頭下,一毛不拔的外孫昨夜偷偷放了五百塊。
劉十三的行李箱夾袋,沒錢買柴油的外婆昨夜偷偷放了五百塊。
曾經班級組織活動,為自己的室友寫評語。劉十三原本寫的是:“矯情,古怪,要不是相處久了有點感情,我早就搬了。”不小心窺視到智哥給他的點評,寫的是:“英俊,聰慧,繁華人世間一道靚麗的風景線。”劉十三良心受到重擊,夜不能寐,等智哥抱著吉他睡著,偷偷爬起來重新給他寫下評語:“細膩,溫柔,恍如江南走來的白衣少年。”
直到失去愛情,劉十三也沒發現,他一直描繪的未來,其實是過去。
他一無所知,無法描繪所有人創造的未來世界裡,如何創造一個家。
他孜孜不倦地承諾和分享,只是把紮根他每個細胞的小鎮生涯,換了本日曆,成為他反覆的描繪。
劉十三淚流滿面。為什麼做不到。為什麼離筆記本上的每行字越來越遠。為什麼不快樂。為什麼冬至下這場雪。為什麼重要的人會離開。
這不是外婆的拖拉機,他快衝兩步就能翻身上去。這不是童年的風,他踩著女式腳踏車就能追到翻飛的葉子。但這是他竭盡全力的速度,在雲邊鎮,他可以趕上澡堂最後一鍋熱水,全鎮最早一籠蒸餃,只要他整夜讀書,還可以趕上山間最先亮起的一朵雲。
冬日的陽光並不溫暖,平穩又均勻,但陽光里程霜的笑臉那麼熱烈,她說:“我就不死,怎麼樣,很了不起吧?”
劉十三把自己這種狀態稱為矯情。生活中常常會出現不合時宜的矯情,比如小時候大家春遊,你頭痛,但你不說,嘟著嘴,別人笑得越開心,你越委屈。事實上沒人得罪你,也沒人打算欺負你,單純只是沒有關注你而已。委屈到達一個臨界點,當事人哇地哭出來,身邊人莫名其妙,明明一塊兒踏青野炊點篝火,大自然如此美好哭什麼,難道觸景生情,哭的是一歲一枯榮?
轟轟烈烈這四個字,一聽就知道是團伙作案。
想念在霧氣中游蕩,往事也是。全部扭曲,飄忽,呈現空曠的畫面。
回程計程車上,一直靜默的劉十三終於感覺到疼痛,大呼小叫起來:“掉頭!掉頭!送我去醫院!我需要臨終關懷!”
程霜說:“臨終是誰,他為什麼要關懷你!沒想到你不但做第三者,自己還有第三者。”
智哥解釋說:“劉十三是說他快要死了。”
程霜說:“才這麼點小傷,怎麼會死。”
智哥解釋說:“太丟臉了,羞憤到死。”
劉十三不屈不撓,繼續喊:“你們不是人!見死不救!我要包紮!”
程霜問:“你哪兒破了?”
劉十三說:“我牙齦流血。”
智哥說:“我也牙齦流血,每天早上刷牙都紅通通的,我媽以為我用的是草莓牙膏。”
程霜說:“草莓牙膏甜甜的,我只敢偷偷用。”
劉十三求助無望,只好展開自救,摸摸全身,掏出一塊電子錶。
劉十三對電子錶說:“廢物,長得跟創可貼一樣,但你有什麼功能?錶帶還是塑膠的,擦嘴能擦出血。”
電子錶嘀嘀叫,劉十三困惑地說:“它為什麼會響?”
程霜說:“鬧鈴吧。”
智哥怒罵劉十三:“大白天你定鬧鐘,不怕晦氣嗎?吵到別人睡覺怎麼辦?”
劉十三傻笑:“我是怕補考遲到,定了提前一小時。”
話說完一片死寂,程霜好奇地問:“什麼補考?”
智哥笑出了聲:“他今天下午要補考。”
劉十三顫抖地問司機:“師傅,你能飛嗎?”
監考老師衝了出去,而劉十三就像走在迷霧裡的人,那加油聲是條隱隱約約的繩索。他順著這條繩索跌跌撞撞振作起身,不管它會不會斷,一心一意要看清楚山崖上的考卷。他心想,走過去,走過去,走過去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