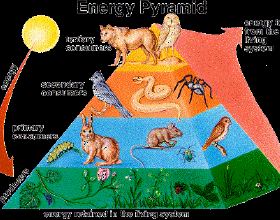當我還是個孩子的時候,我曾經住在一個孤獨的白色農舍裡,穿過我們所有領域中最富裕的地方,鋪設通往大城市的火車軌道。
火車每天每小時都在疾馳而過,轟隆隆地穿過荒野,震動森林地面,所以即使是最遠的鹿也能感覺到它的刺痛。
晚上,我常常冒險走出後門,整齊地踩著我們最美麗的花朵,躺在火車軌道上,凝視著星空,像碎鑽一樣在我身上閃爍。
當我感覺到他們來了,最終光線照亮了我悲傷的身體時,我會跨過金屬欄杆,走到鐵軌旁邊的田野上,距離足夠遠,可以看到人們,觀察他們的臉,然後想知道他們在不敬虔的巫師時刻要去哪裡。
在我家的田野對面,躺著一個小鎮,住著一家人。人們似乎從未停止翻新自己的房屋和院子,他們將衣物掛在卡通色彩繽紛的繩子上,以及舉辦派對和唱歌。我喜歡去那個小鎮。
如果你沿著擁有鎮上最大房子的柏油路,自豪地走過那些呆呆的辮子女孩和雀斑男孩,你就會到達本尼迪克特的房子。
本尼迪克特的房子也是白色的,我們有一個共同點,在它之外,碎石小路延伸到最美麗的松樹林和楓樹林中,搖曳進入山丘、空地和清澈的溪流,在樹木過濾的陽光下閃閃發光。只要我能步行到他家,我們就會出去。
他又高又瘦,總是穿著看起來一樣的衣服——黑色夾克,全部繫好紐扣,黑色緊身牛仔褲。他金色的頭髮被修剪得緊緊的,露出深陷的眼眸和凹陷的臉頰。
我媽媽似乎從不喜歡他,但從不公開反對我們的友誼。然而,在一個深夜,當我穿過佈滿圖片的走廊再次見到我的午夜情人、軌道和天空時,她對我工作疲倦的父親說得沮喪的話。她說,那個男孩長著一張我的奮鬥的臉,在我和本尼迪克特在一起的大部分時間裡,我都不知道她的意思。
他和我在一起很特別。據我所知,他從來沒有和任何人說過話。我也好不到哪裡去,我唯一的其他朋友是我的近親表兄弟,每當我的家人舉行重要聚會時他們都會過來。